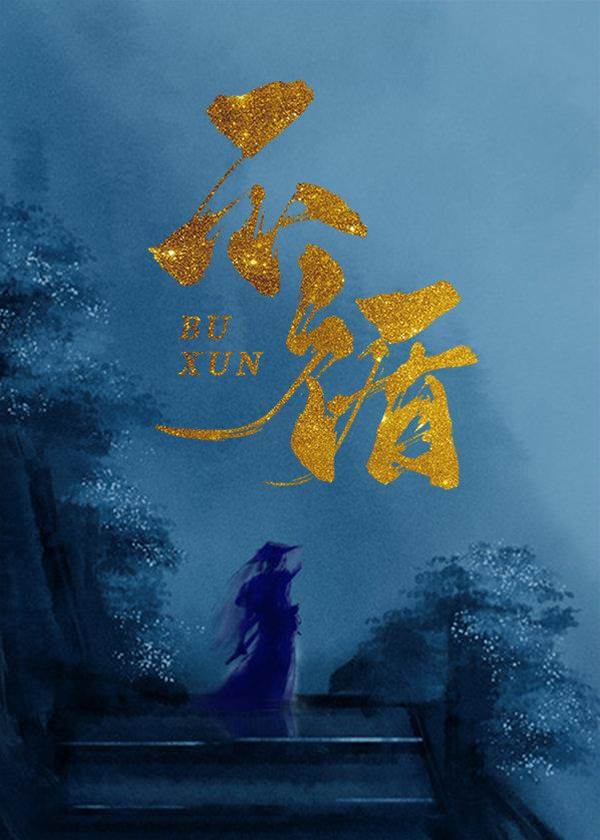《國色生香》 第4章 004
前世宋嘉寧給郭驍當了七年寵妾,但那七年,始終住在郊外的莊子上,郭驍沒解釋過原因,也沒問,總之,京城那些達貴人們,除了郭驍,便只在臨死前,草草與端慧公主、新帝打了一次照面。
而這個同船的黑男人……
宋嘉寧不控制地往郭驍的至親上聯想,因為兩人實在是太像了,如與母親,外人一看就知道是娘倆。算算年齡,郭驍今年十六,宋嘉寧不清楚衛國公的,但想來應該也就是三十五六的歲數。
地,宋嘉寧再次朝黑男人瞄去。
春明,船夫將烏篷竹簾卷起來了,黑男人臨窗而坐,正眺窗外之景。湖風涼爽,迎面吹來,男人側臉冷峻棱角分明,修長脖頸中間結明顯,結旁邊,有道細長的傷痕,年頭已久,不細看可能分辨不出來。
宋嘉寧的心,撲通撲通跳,年齡對上了,而那傷痕,衛國公是武將,難道真的是?
可堂堂衛國公,不在京城待著,怎麼來了江南?
宋嘉寧絞盡腦回憶前世,可惜嫁給梁紹前只是個普通的宅子,對場上的事沒興趣也沒有途徑知曉,等進了京城,又終日住在幽靜的莊子上,邊的丫鬟嬤嬤都得了郭驍提醒,只陪打趣解悶,不該聊的絕對不會多。
或許,衛國公在江南當過差?
宋嘉寧想的出神,忘了收回視線,那邊郭伯言久經沙場,五何其敏銳,察覺有人看他,他無聲偏轉視線,最先看的是對面頭戴帷帽的人,確定窺視不是來自帷帽之下,他才注意到人旁邊呆坐的小。
八九歲的娃,穿著桃紅褙子,臉頰白里,一雙黑白分明的杏眼水汪汪的漂亮。郭伯言有一個兒兩個侄,在他的記憶中,三個姑娘從小到大都很瘦,瘦得纖細優雅,孩子們喜歡,郭伯言卻總覺得不妥,他希自己的兒吃胖一點,胖了他才心安,不然總擔心孩子們吃不飽。
就像這個娃,臉蛋乎乎的,又不是特別胖,看著就讓人寬心。
剛上船時郭伯言就注意到娃看他了,小孩子好奇陌生人,他沒在意,現在這丫頭又在看他,看得那麼神,憨憨傻傻地,郭伯言不由納罕,肅容問道:“為何看我?”
船一直都很安靜,只聞湖波漾聲,他突然開口,威嚴清冷的聲音立即驚醒了宋嘉寧。為何看他,當然不能說實話,可一時半會兒,宋嘉寧也找不到合適的借口,骨子里又敬畏那位疑似衛國公的男人,出于本能,宋嘉寧著肩膀往母親后躲。
林氏都有點怕黑男人,兒害怕很理解,一邊盡量擋住兒,一邊低聲賠罪:“小頑劣,不敬之還請人海涵。”
貌的人聲音未必好聽,可林氏嗓音清潤細,突然在這四面敞亮的湖中小船中散播出來,便如秀麗江南春景中的一聲黃鶯輕啼,說不出來的婉轉空靈,恰逢烏篷船行到湖中央,風更大了,吹得林氏面前的帽紗翹起一角,出人白皙致的下,如牡丹綻開的第一片花瓣,姿人。
郭伯言頭滾了下,其實單看婦人邊娃的容貌,他便知道,此必是絕。
微微頷首,郭伯言繼續賞景。
林氏擔心兒再看,牽著宋嘉寧手站了起來:“咱們去外面看魚。”
宋嘉寧乖乖點頭。
娘倆一起往外走,宋嘉寧還小,顯不出段,林氏迎風而行,擺翩飛,不盈一握的纖腰頓顯無疑,那麼纖細弱,人忍不住擔心下一刻就會被風吹到湖里去。船里兩個男人都被的曼妙影吸引,尤其是郭伯言,口似有一團火了起來。
浮生得半日閑,他這個巡再有半年便要回京,今日突來游興出來走走,未料偶遇佳人。生在權貴之家,郭伯言年期間便見過不人,但只憑一抹纖影、一聲“人”便讓他心難耐的,這婦人還是第一個。
可惜,已為人婦。
郭伯言再心,也不會染指他人之妻。
船靠岸了,林氏扶著兒肩膀站在船尾,等郭伯言主仆上岸了,娘倆才不不慢地下船。臨行前,秋月低聲與船夫理論,船夫彎腰賠笑:“我的姑,那兩位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小的哪敢吭聲啊?”
秋月哼道:“那你退錢。”
船夫舍不得,哀求地看向林氏。
林氏笑笑,喚秋月一聲,這就去賞花了,故意選了與郭伯言相反的方向。
們來得早,島上人還不多,林氏牽著兒沿著主路走,盡量不往偏僻的地方去。
“娘,你看,那朵一半紅一半白,好漂亮。”宋嘉寧想方設法哄母親出門,就是希母親多看看外面的景,想一些父親,故上了島,宋嘉寧便一心尋找別致景給母親。
“娘給安安摘一朵。”桃花如霞,林氏確實賞心悅目,兒腦袋,親自過去摘花。一共十來步的路,宋嘉寧、秋月站在路邊等,林氏在樹下站定,回頭看看,對上兒桃花似的小臉,笑笑,仰頭摘花。
花枝偏高,林氏不得不踮腳,可就在努力折花枝的時候,路邊突然傳來一靜,好像有猛虎跳出!林氏大驚,一扭頭,驚見一蒙面男人手持棒以雷霆之勢連續敲在秋月與兒頭上,眼看兒小小的子倒下去,林氏心神俱裂,當即便朝兒撲去:“安安……”
這一刻,忘了自己也有危險,只想確認兒的安危。
蒙面男卻丟了長撲過來,一手抱住林氏纖腰,一手捂住林氏,火急火燎地往桃花深走。林氏拼命掙扎,奈何一個常年幽居的年輕婦人,折花枝都費力,又怎掰得開男人那雙手,無論手打還是腳踢,都沒有用。
蒙面男正是得了親姐姐消息尾隨而至的胡壯,他惦記林氏惦記了三年多,如今終于盼到機會,胡壯憋了三年的火登時燒到頂點,燒得他只想先要了林氏,其他什麼都不管不顧了,計劃是否周,路邊宋嘉寧兩人被人發現了怎麼辦,他都不管,只想將林氏按在地上先痛快一回!
時間迫,沒走多遠,胡壯便捂著林氏將在地上,林氏力掙扎,但這掙扎只刺激地胡壯火更熾,大手拽住林氏領口猛地一扯,林氏半邊雪白肩頭就出來了。林氏嚇得忘了反應,胡壯盯著衫里面的雪青肚兜,眼睛都饞紅了!
林氏帷帽早已落在半路,看出男人眼里的,臉慘白,一邊搖頭掙扎一邊哭,混間意外扯掉了胡壯臉上的黑巾。胡壯常去宋家,林氏自然認得他,恐懼中立即騰起憤怒,掙得也更用力,口中嗚嗚出聲。
“好嫂子,你就給了我吧,我宋大哥死了三年了,你真的不想?”胡壯一手捂著林氏,一手急不可耐地解帶,結實的將林氏得死死的,無法挪分毫,說著還試圖親林氏脖子。林氏拼命躲閃,未料一扭頭,竟瞥見一道高大影,風馳電掣般朝這邊而來!
林氏哭聲更高。
胡壯子都一半了,剛要扯林氏的,背上突然傳來一大力,他驚駭后,郭伯言一拳打在他臉上,曾經率領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的男人,全力打出的一拳甚至帶著虎嘯,打得胡壯當場昏死過去,被郭伯言隨手甩到一旁。
解決了混賬,郭伯言低頭。
林氏上的褙子已經爛了,單薄雪白的雙肩都在外面,如碧綠草地中的兩朵玉蘭。抱埋首蜷一團,一頭凌青擋住臉龐,只有絕后怕的哭聲嗚嗚地傳了出來,邊哭邊試圖拉攏破碎的裳遮住肩膀。
一個楚楚可憐的人,既讓人想要保護,又最容易激起男人的。
郭伯言靜默不,幽深目一寸寸在林氏上游移,發下出的淚臉,徒勞遮擋的人肩,蜷起來的蓮花一樣的子,以及悲切無助的哭聲,無一不在挑戰他的理智。他聽見了,丈夫死了三年,是一個寡婦。
后傳來腳步聲,是他的長隨魏進,郭伯言迅速下長袍,俯替林氏裹上。
這個作,說明他沒有心,至現在沒有。
林氏看到一希,閉著眼睛嗚咽道謝:“人救命之恩,我必當重謝……”
“如何謝?”郭伯言扶坐起,他單膝蹲在面前,黑眸犀利地看著眼,雙手握肩頭。
男人掌心火熱,過衫清晰地傳了過來,再男人肆無忌憚的審視,林氏心中一驚。余中見男人手下一手抱著兒一手抱著秋月走了過來,林氏急了,哭著求恩人:“我家有薄產,只要恩人開口,我悉數奉上,求您讓我先看看我兒……”
郭伯言并未松手,只看了一眼魏進。
魏進放下一大一小,低聲回稟道:“被打昏了,應該沒有大礙。”
林氏稍微松了口氣,眼淚卻越來越多,為后怕,也為前途未卜,惶然之際,忽聞恩人道:“那個收拾了,不可留下任何蛛馬跡。”
林氏心跳一滯,收拾是什麼意思,他要收拾哪個?
眼去看,就見魏進三兩步走到胡壯邊,大手提起胡壯,悄然朝島嶼深而去。
林氏渾抖,不在乎胡壯的生死,但,此人竟能視人命為草芥,必是兇殘狠辣之輩……
“在想什麼?”將的各種緒盡收眼底,郭伯言低聲問,低沉的話語帶著三分愉悅。
林氏沒聽出來,只害怕,男人的手還握著肩膀,心思不言而喻,而他當著的面展示兇狠,真不是另一種威脅嗎?
百轉千回,林氏垂眸,抖著道:“我有五百兩家私,想盡數獻與恩人。”
郭伯言笑了,笑得很晦,靠近,他抬起致小巧的下。抗拒,郭伯言用力扣住,盯著恐慌的淚眼道:“本國公不缺錢,只缺一房小妾。”
林氏聞言,如墜深淵。
猜你喜歡
-
完結185 章

重生寵婚:大佬命定甜妻
蘇喬上輩子眼盲心瞎,被渣男和賤妹騙得團團轉,放著那樣的好老公都不要。一朝重生,蘇喬的主要任務就是抱緊老公的粗大腿,手撕仇人,打臉白蓮!老公的大腿真粗啊,就是抱久了,她腿軟……「老公,對不起,以後我不會再犯傻了。」「蘇喬,你以為你以退為進,就能離婚嗎?收起你那些小心思,這輩子都別想離開。」
32.1萬字8 45289 -
完結596 章

重生七零:炮灰知青只想當鹹魚
谷麥芽被家裡人害死後重生到了七十年代,成了一名不受父母重視的小可憐,被安排下鄉當知青。 可後來她才發現,自己竟然是穿書了,成了軍嫂重生文中女主的極品妯娌、對照組! 谷麥芽怒了:想讓我當對照組、成為女主成功路上的墊腳石,我就先把女主的官配給拆了,給大伯哥安排個真心實意的對象! 顧愛國:媳婦,虐渣虐極品放著我來,我用極品打敗極品!
122萬字8 31078 -
完結922 章

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礦山裝備、電力裝備、海工裝備……一個泱泱大國,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用汗水和智慧,鑄就大國重工
252.3萬字8 5516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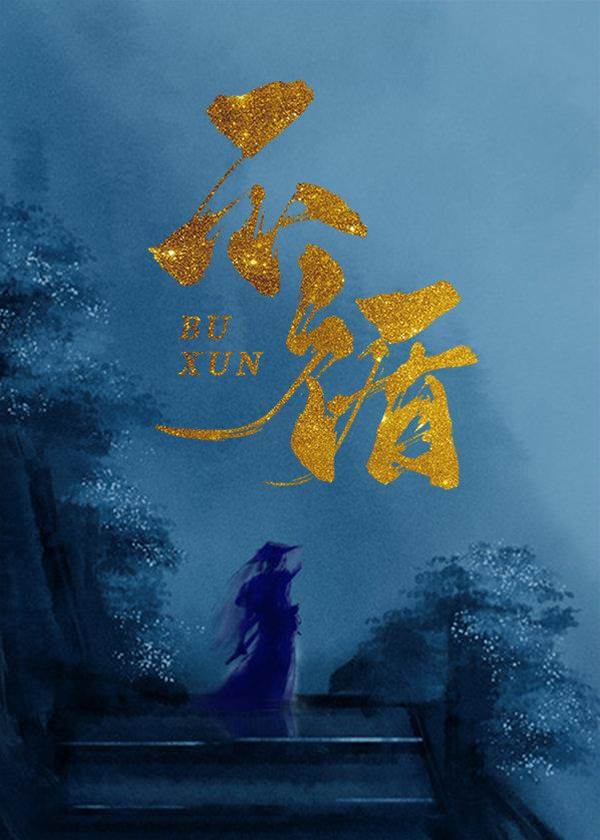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508 -
完結423 章

欲扶腰
南漁當上太后那年剛滿二十。面對稚子尚小,國事衰微,她急需抱一只霸道粗壯的大腿撐腰。朝野弄臣蕭弈權向她勾了手指,“小太后,你瞧我如何?”南漁仰著艷絕無雙的小臉,跪在男人靴下:“只要我乖,你什麼都可給我嗎?”后來,她真的很乖,乖到將上一世受的屈辱全部還清,乖到一腳將蕭弈權踹下城樓!彼時,早已被磨礪成舔狗的男人,滿身血污,卻仍討好的親吻她腳尖:“漁兒,別鬧。”-----我欲扶搖直上青云里,他卻只貪欲中腰。 ...
70.1萬字8 92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