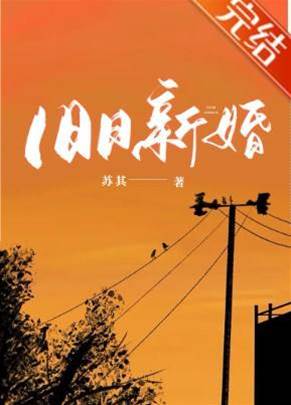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繁簡》 第26章
倪簡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說出這樣的話。
酸味十足。
沒等陸繁從那話里品出什麼味來,就先低頭了臉,不想再跟他繼續說下去了。
轉走了。
陸繁頓了一瞬,跟上去。
倪簡走到路口,轉彎,進了一家便利店。
陸繁過去時,正在貨架前挑東西,選了薄荷糖,順手拿了三盒岡本丟進購籃里,轉頭看到陸繁時面無表,自然得就像買了三盒口香糖。
結賬時,倪簡手掏錢包,陸繁先遞了錢過去,收銀員很自然地接過去給他找零。
倪簡看了他一眼,什麼話也沒說。
陸繁拎著購袋走在前面,倪簡在后頭慢慢跟著,兩人各懷心思,一路無言。
回去后,倪簡說:“我要睡會兒,你自便。”說完就進了房間。
陸繁要出口的話生生咽回中。
倪簡一覺睡醒已經是下午了。
睡眼惺忪地走出臥室,發現陸繁居然還沒走。
他坐在沙發上,手里捧著一本書。
倪簡站在房門口歪頭瞥了兩眼,看到書的封面,認出那是房東留在茶幾下面的推理小說,翻過兩頁,很俗套的節,看了開頭就能猜到結尾的那種,很沒意思。
但陸繁似乎看得很神。
倪簡半天沒作,默默在門口站著,突然不舍得打破這樣的畫面。
恍惚間,像回到了小學一年級。在陸繁的屋里做作業,他靠在椅子上看書,一大片夕從小窗里灑進來,蓋在他們上。
寫完作業時,他會放下書,把糖罐子打開,給兩顆花生糖。
那個味道,已經多年沒嘗過,但依然清晰。
這樣的記憶,如今想起來,恍如隔世。
倪簡不知道自己的記原來有這麼好。
陸繁家剛搬走的時候,倪簡時常想他,想他的好,想他媽媽的好,想他給買的零食,也想他房間里溫暖的夕。
但后來那些年,離開這里,在北京,在國,在不同的地方漂著,沒怎麼想過他,畢竟只是年記憶里的一個小鄰居,再好,也算不上多麼刻骨銘心。
頻繁地想起過去,是從再見到他后才開始的。
現在的陸繁跟小時候分明很不一樣,卻總是從他上看到那個小年。
說起來,真是詭異。
倪簡不知道站了多久。背著手,靠在門框上,魂被什麼勾走了似的。
陸繁合上書,一轉頭就看到了。
頭發很,散在肩上,頭頂還有一小縷立起來的,有點稽。
穿的睡偏大,松松垮垮地罩在上,襯得整個人纖細瘦小,無端地顯幾分罕見的脆弱。
他們視線合,互相看了一會,誰也沒說話。
陸繁把書放下,站起,朝走過去。
倪簡這樣厚臉皮的人毫不會因為默默看人家而到尷尬,就站在那里,平靜地看他走來。
陸繁到了邊,仔細看了看,確定臉還好,問:“睡好了吧?”
倪簡點了點頭。
陸繁說:“那行。”
倪簡抬了抬眼皮,以為他要說“那行,我就先走了”,沒想到陸繁的話頭打了個轉,拋出一句,“我們談談。”
倪簡愣了愣。
上次他提出“談談”還是在尋南村那天,不過當時沒跟他談,反把他調侃了。
那天的事想起來不怎麼好。
倪簡的心down下來了。
但現在這一刻,他的語氣似乎更慎重,像經過長久的思考,做下了某種決定一般。
以倪簡的壞心眼,應該再調戲他一次才對。
但沒有。
不知為什麼,他這般認真的模樣,讓壞的一時口拙。
鬼使神差地點了點頭。
陸繁突然手牽起,往沙發邊走。他的作十分自然,沒有一尷尬。
倪簡倒是有些發怔,的手不,保持著被他握進掌心的樣子,一路跟隨,到沙發上坐下。
陸繁寬厚的手掌松開了。
他收回手,坐到旁邊。
倪簡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里涼了一下。
把手回來,用自己的另一只手包住。
不行,沒他的手暖和、舒服,力道也不對。
倪簡皺了眉,反復自己的手。
陸繁沒注意的小作,他在看的眼睛。
默了片刻,他開了口,低沉的嗓音徐緩地喊:“倪簡。”
他很正式地喊的名字,除非是被惹怒的時候。
倪簡雖聽不到聲音,但著他的和他此刻的表,能覺到他的語氣應該是嚴肅認真的。
猜他這樣子,是有很重要的話要說了。
預料不到他要說什麼,竟莫名有點張。
沒反應,陸繁也不等應聲。
他的目自始至終都是平靜的,又或者說是堅定的。不論什麼反應,他都要把話說下去。
陸繁微抿了下,再啟口時,聲音放低,語速更緩慢。
他的一啟一翕都十分清晰。他要讓看清楚他接下來說的每一個字。
他說:“你離開太久,有些事,可能需要重新了解。”停了下,說,“我是說,我的事。”
“你的……什麼事?”倪簡著他,無知無覺地掐了手心。
陸繁眸微微轉深,淡淡說:“倪簡,你看清楚了,我不再是小時候那個陸繁,我今年29歲,高中肄業,在做消防員,合同制,也就是臨時工,我每個月工資兩千七,前年還清債,現在有四萬存款。我很清楚,我這樣的人跟你不是一路的。”他嚨微,“這些年,你走得很遠,也走得很好,再也不是當年的小簡,這些我也清楚,倪簡,我……”
“你閉!”
未說完的話突然被厲聲打斷,陸繁一怔。
倪簡沒給他一秒的時間,驟然撲上去:“你他媽給我閉!”
這作來得猝不及防,陸繁來不及反應,就被揪著領子到沙發上。
倪簡像瘋了似的,雙目發紅,惡狠狠地盯著他。
“倪簡……”陸繁喊了一聲,但倪簡像沒聽到一樣。
氣勢凌人,咬著微紅的聲說:“你要說什麼?你他媽接下來準備說什麼呢?讓我猜猜……啊,我知道了,不就是那一套嗎?是要說你只是個普通人,你沒錢沒勢,你卑賤無名,招不起我,咱倆不是一條道上的,所以你要請求我放過你,所以以后我走我的道,你過你的獨木橋,你就不跟我玩了,我就得滾了,是吧,嗯?”
伴著最后一個音,手上猛一用勁,將他得更狠。
“是不是啊,你說是不是?”
反復問著,一雙眼睛紅得嚇人,冷冷凝著他,像是騰了霧,又像是浸了水。
好像了。
全繃著,在發抖,攥著他領的手青筋明顯。
這個模樣的,令陸繁震撼。
他懵然地覷著,忘了掙扎反抗,也忘了接下來要說什麼。
倪簡像個被判了死刑的絕癥病人,再也偽裝不了淡然無尤的姿態。
要瘋了。
一次兩次,一個兩個,把當垃圾,當病毒,只想丟掉,丟到天邊去。
他也終于忍不住了是麼。
他也要丟掉。
在全沸騰,從里到外都被燒灼著。
媽的,不行了。
疼得不行了,心腔里那塊尤甚。
問不下去了,張著大口呼吸,覺吸不進去氣,眼睛里灼燙,仿佛所有的氣力都沖進了眼里,撞得眼球發脹、發疼。
有水滴掉下來。
一顆、兩顆、三顆……
不知道那是什麼,茫然地眨著眼睛看。
卻是模糊的。
看不清那落下的東西,也看不清陸繁的臉。
而陸繁整個人都呆了。
的眼淚砸在他的脖子上,好幾顆接連掉下來,跟熱湯一樣,快要把他的皮燙穿了。
他張了張,嚨發啞,嗓子里梗著什麼,半天找不回自己的聲音。
仍攥著他的領子,像攥著多麼重要的東西,死也不松手。
分明在哭,卻一聲音也沒有發出。
死死咬著,鮮紅的溢出來,和著的淚一起落下來。
“倪簡……”不知對峙了多久,陸繁終于找回聲音,但已經啞得不像話。
倪簡眨掉眼里的水,抬起一只手抹掉上的:“你閉,你閉。”
陸繁不會閉。
他認了。
如果這個樣子都不是因為在意他,那他認了。
“你錯了。”他說,“倪簡,你錯了。”
他手臂抬起,勾下的脖頸,上。
在里嘗到甜腥味。
三秒后,他退開,手抹干凈的淚。
倪簡的眼前清晰了。
陸繁看著,無聲地了瓣。
——你看清楚,我們的確不是一路的。
——但我不打算放過你。
猜你喜歡
-
連載1471 章
盛少,情深不晚
年輕幼稚的周沫被爸爸算計,稀裡糊塗睡了高冷男神盛南平,陰差陽錯生了兒子。 盛南平恨透周沫 三年後,為了救兒子,他必須和周沫再生一個孩子。 周沫是有些怕盛南平的,婚後,她發現盛南平更可怕。 “你,你要乾什麼?” “乾該乾的事兒,當年你費儘心機爬上我的床,為的不就是今天?” “……” 傳聞,京都財神爺盛南平是禁慾係男神,周沫表示,騙人滴! 終於熬到協議到期,周沫爆發:“我要離婚!我要翻身!” 但盛南平是什麼人,他能把你寵上天,也能殺你不眨眼......
357.7萬字8 15379 -
完結1203 章

五年後,龍鳳雙寶攜她炸了大佬集團
夏梵音被繼妹陷害懷孕,被迫假死逃出國。 五年後,她帶著萌寶們回國複仇,竟意外收穫了個模範老公。 安城裡的人都知道紀三爺性情殘暴冷血,可卻日日苦纏全城知名的“狐貍精”。 夏梵音掙紮:“三爺,麻煩你自重!” 紀爵寒抱起龍鳳胎:“孩子都生了,你說什麼自重?”
214萬字8.18 86977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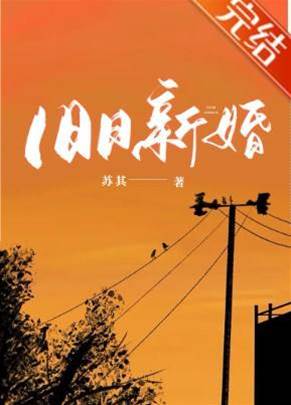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274 -
連載959 章

賀總夫人又來蹭氣運了
姜糖天生缺錢命,被師父哄下山找有緣人。 本以為是個騙局,沒想到一下山就遇到了個金大腿,站他旁邊功德就蹭蹭漲,拉一下手功德翻倍,能花的錢也越來越多,姜糖立馬決定,賴上他不走了! 眾人發現,冷漠無情的賀三爺身邊忽然出現了一個軟乎乎的小姑娘,會算命畫符看風水,最重要的是,總是對賀三爺動手動腳,誰不知道賀三爺不近女色啊,正當眾人等著她手被折斷的時候,卻見賀三爺溫柔地牽住她的手。 “嫁給我,讓你蹭一輩子氣運。”
174.2萬字8.18 12962 -
連載317 章

避孕失敗!沈小姐帶崽獨美,厲總慌了
十年深愛,四年婚姻,沈瀟瀟畫地為牢,將自己困死其中,哪怕他恨她,她也甘之如飴。直到一場綁架案中,他在白月光和懷孕的她之間選擇放棄她,間接害得父親離世。她終於心死,起訴離婚,遠走國外。三年後再見,她攜夫帶子歸國。厲行淵將她困在身下,“沈瀟瀟,誰準你嫁給別人的?”沈瀟瀟嬌笑,“厲先生,一個合格的前夫應該像死了一樣,嗯?”男人眼眶猩紅,嗓音顫抖,“瀟瀟,我錯了,求你,你再看看我……”
53.8萬字8.18 501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