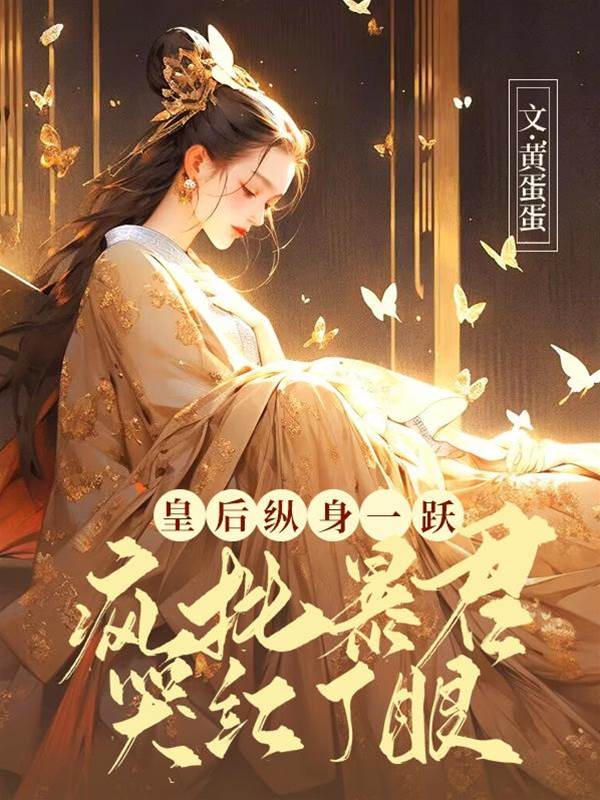《鳳囚凰》 第22章 三日鎖心丹
書閣的第一印象:大。
非常的大,七八間寬大的屋子,全都擺滿了書架,架子上也放得滿滿的,幾乎不見什麼空餘。
書閣的第二印象:。
這是楚玉細看之後發現的,書架上有放著紙書,有錦帛卷軸,也有竹冊。一捆捆竹簡卷軸以淡青的綢書包著,整整齊齊的摞放在書架上,乾淨無塵,空氣間漫溢著淡淡的書香與檀香混合的味道,可見容止平日裡對書閣的打理十分用心。
但楚玉說,並不是說容止丟書籍,而是這些書籍的擺放,幾乎沒有什麼規律,竹簡與紙書混放在一起,雖然各自拜訪得整齊,但是整看起來,卻是有些了。
而這些書也沒有按照容分類,各種類型的雜放在一起,非常不便尋找。
書閣的第三印象:雜。
楚玉隨意的翻了一些書,發現這書閣之中,所收藏之繁雜,超出的想像,山河,地理,政治,詩文,民間故事,異聞雜錄,幾乎什麼都有。
容止靜靜的站在書閣門口,看著楚玉在書架邊不斷的來回走,拿起一本本書草草翻閱,也沒有上前手幫忙,他只是在原地默默的看著,烏黑的深不見底的眼瞳裡,好似有疊雲一般莫測的緒漫漫舒捲著。
他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做,只出神似的看了許久,才慢慢的出聲,憑記憶指點楚玉應該在哪裡找要的詩文書冊,自己也幫忙挑選詩集。
“左側書架第二排第三格第七冊。”按照容止的指點,楚玉準確無誤的找出他所說的書籍,心中對於他的記憶力表示一百二十萬分的佩服,如此雜的排布,還能一不差的記得哪本書放在哪個位置,這人腦簡直堪比電腦。
懷裡抱著二十多本書,楚玉覺雙臂痠麻發痛,纔回頭想要招呼容止幫忙,卻見容止手上捧著十本書,樣子有些吃力的道:“公主,我拿不了,你幫忙分擔些吧。”說著,他走過來,給在楚玉雪上加霜的又疊了十本。
楚玉無語的瞪視著他,後者神倒是十分坦然,好像這是理所應當的事一樣,想起自己這些天從未見過容止拿起比一冊竹簡更重的東西,也許大概真的是質弱弱不勝,便咬牙忍下,充當了一回大力水手。
當楚玉抱著書慢慢的往外走時,作勢繼續翻找詩集的容止停下了作,從楚玉看不見的角度,深深看著。
滿是書卷芬芳的空氣裡,那容貌是欺騙世人的清雅,雖然因爲手上重負有些難過,可是抑之下的神依然明快如山間松風,目中又有幾分颯然之意。
恍惚間,容止好像看到了另外一個影子,模模糊糊的,與楚玉清麗的面龐分離又重合。
他不知不覺的手上心口,直到楚玉走出書屋,影完全消失,才從迷夢一般的幻境中甦醒:他方纔在看著的人,究竟是誰?
狂翻了兩天的書,楚玉看得頭昏腦脹,覺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前世上大學時,每到臨考試前,大家便都拼命的學習,努力的記憶書中要點,靠著這種考前突擊的做法,竟然一路平安,大學四年都沒有落到補考的境地。
對於這種突擊式的學習,楚玉是輕車路早已習慣,但是兩天來一直看著的容止卻十分不解,終於忍不住在兩天後問出來:“公主,你這麼辛苦看書,是要做什麼麼?”
楚玉放下書本,酸的眼睛,道:“沒法子,我人邀約,要去參加詩會,總要做些準備。”
容止失笑道:“竟然是這樣,公主是想要自己做出詩來麼?”這可有些不太容易。
楚玉想想道:“這倒未必,只是詩會上若只有我一人不作詩,未免有些出格。”
容止抿一下脣,聲道:“倘若公主在爲這個煩惱,大可不必如此辛苦,只消在參加詩會時帶上一個人便可。”
“誰?你?”楚玉微微瞇起眼,覺得頗爲有趣,難道參加詩會也能帶槍手?
容止搖搖頭,道:“我算什麼?我說的那人,是桓遠。只要帶上他,保管沒有人會留心公主你是否有作詩。”
他頓一頓道,“不過桓遠份不便示人,公主應該掌控得嚴一些。”他說著走到書架的盡頭,手按在牆面上,掌心一轉,便有一個暗格彈了出來。從暗格中取出兩隻瓷瓶,一隻瓶上有斑駁的青藍蓮紋,一隻瓶晶瑩玉白。
楚玉有點張又有點好奇的睜大眼,盯著兩隻瓷瓶:那該不會是傳說中的毒藥吧?
容止仔細端詳了一下兩隻瓷瓶,最後將帶蓮紋的握在手心,玉白的那隻放回去:“這藥名爲三日鎖心丹,服下一粒,大約有三日左右的時間子乏力,只能堪堪行走,跑卻是不支,更遑論武,如此一來便不必擔憂桓遠藉機逃走。”
“這個,會不會對有損害?”
“自然是有一些的,三日之後,桓遠需要臥牀調養半月,才能恢復如初。”容止很隨意的說著,好像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手中藥瓶朝楚玉遞了過來。
楚玉盯著他,手卻不去接:“桓遠是不是曾經得罪過你?”假如沒有,何以要慫恿對桓遠施加這麼損的藥?
忽然想起一件事,既然容止在苑的權力如此之大,那麼那些記載各男寵資料的卷軸,是不是他也曾經手過呢?
假如是這個緣故,卷軸上不見容止的記載,也是理所應當的事。
還記得,府上曾經有幾個男寵,據說因爲不守規矩被置了,那是不是容止乾的?
容止聞言一愣,他擡眼向楚玉,漆黑的眼瞳裡,如雲一般翻卷著微妙的緒,他平素看來總是高雅又深沉,這一番錯愕,帶著幾近微微的哀慟之,好像嚴的面乍然破裂,出了一角絕的臉容。
他的神素來平和高雅,這不同尋常的剎那波,反而令他生出一種別樣的驚魂魄的詭豔,楚玉剎那間幾乎失了神,片刻後才收斂心志,卻還是被他看得心虛。雖然明知道自己沒什麼可心虛的,可是被這樣一雙眼睛著,還是忍不住心虛……不僅心虛,還還心跳了好幾拍。
“公主既然捨不得讓桓遠苦,那麼便讓越捷飛留神將他看一些,此人假如放到了外面,一定會反過來爲對付公主的利。”容止微微一笑,方纔異樣的眼神好似水月鏡花的幻影一般,就那麼不著痕跡的抹去,他將藥瓶放回原,“容止還有要事,先行離去了。”他甚至連最簡單的禮節也省略了,頭也不回的匆匆離開。
楚玉就算再遲鈍,也曉得容止好像是生氣了,而生氣的原因恰好是。可是想不通那傢伙爲什麼生氣,只是不想傷人而已,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那傢伙究竟在計較什麼?有什麼問題坦白說出來不行嗎?給擺什麼臉?
古人真是莫名其妙!
猜你喜歡
-
完結1224 章
全星際都是我的美食粉絲
21世紀美食博主江秋秋穿越到了星際時代,兩袖清風,一窮二白。為了餬口,聯邦美食直播專區一個叫江啾啾的美食主播橫空出世,吸引了無數土豪大佬和億萬聯邦粉絲!#震驚!美食區某主播粉絲排行榜簡直就是聯邦中央臺新聞釋出會!!!#榜一是帝國之刃墨司上將!榜二是內閣首席瓊斯閣下!榜三到榜二十集齊了聯邦18位征戰將軍!眾人:!!!???*江秋秋原本隻想做做飯餬口,冇想到一不小心就出了個名,入了個伍,拯救了個軍團,撿了個一個丈夫。某日,一則短視頻引爆聯邦網絡,視頻裡,聯邦最熱網紅江啾啾指揮著高大英俊氣勢懾人的帝國之刃墨司上將那雙引爆蟲族女王的手,拿著菜刀切蘿蔔!並表示:她終於找到了一個為她做飯的男人。無數人為這絕美愛情嚶嚶嚶嚶嚶嚶嚶!-【嬌軟美食博主x為嬌軟美食博主洗手作羹湯的上將大人】
133.1萬字8 37919 -
完結155 章

戰損美人征服全星際
年僅20歲的星際戰神沈言在戰斗中犧牲,昏迷中聽到了一個奇怪的聲音。【歡迎進入ABO的世界。】【你是個嬌弱的omega炮灰、沈家真少爺,但假少爺沈安才是主角受。要逆轉命運,你必須——】沈言:?沒想到剛醒來就吐了一大口血。【系統:忘了提醒你,你…
56.8萬字8 18801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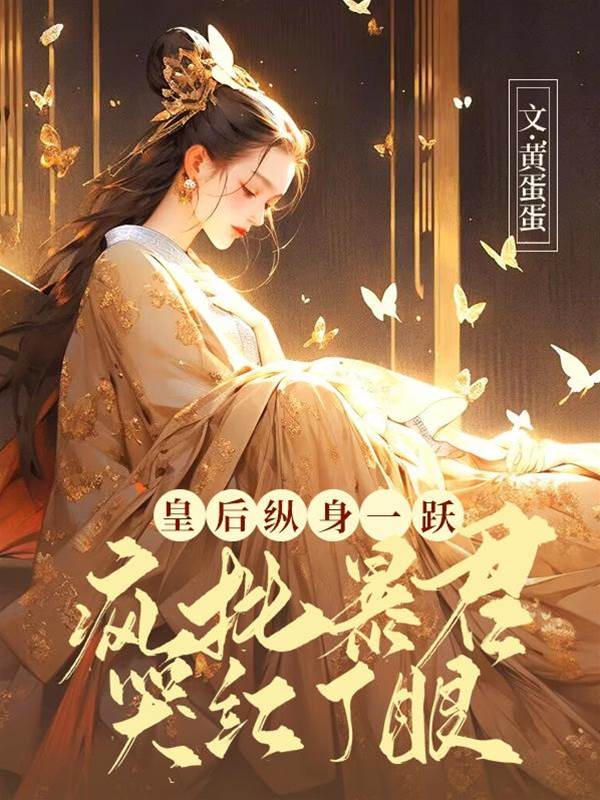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1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