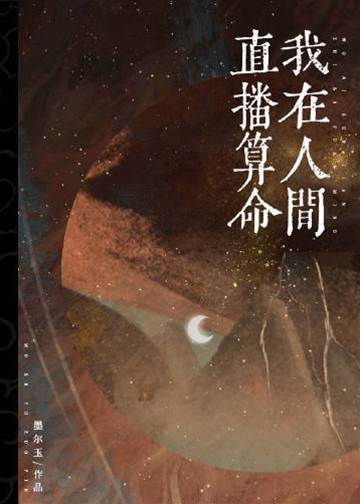《被獻祭后她成了白月光》 第2章 真相2
漫天飄雪停留在空中。
神殿高聳的正門緩緩打開,一道傾長的白影逆而立。
他周圍的雪花瞬間蒸騰,化了一陣陣縹緲的霧氣將來人環繞,看不清面貌。
天嬰知道,是他。
當年洗三清殿殺退鳩占鵲巢的眾妖之時漫天雨,他也是這般將無數珠子停在了空中。
他踏過尸山海,手刃萬千亡魂,角都從不曾沾染過一點污漬。
天嬰知道他潔癖,卻不想連這純白的雪片他都不允近。
在無妄川邊一個個大雪夜,還傻傻地開著窗,趴在窗沿眺,希他能夠踏雪而來,讓自己一頭扎進他懷中取暖。
現在想來這是多蠢多天真。
早就死了,早死在了無妄川邊,死在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等待里,只留下一行尸走的軀殼。
但是,這軀殼在看到他的瞬間,卻也本能的沒出息的想向他奔赴而去。
然而,向前一步,發現前方是他為自己準備的祭壇。
收回了邁出去的,那顆早已死去的心像詐尸還魂一般開始痛,撕裂,讓痛不生。
紅著眼睛看著對方,話到嚨口,口痛得發不出一點聲音,痛得抓住口的服。
手中的燈掉在了地上,驚得里面的火蝶瘋狂撲騰著翅膀,驚起一陣陣火花。
而對方的人影也只是漠然站在原,靜默地看著自己。
容遠從來不妥協,向來從不示弱。
即便自己站在祭壇之上,之地高于他,他卻依然是高高在上的模樣。
兩人相,永遠都是打破安靜,永遠都是找話題,即便此時此刻他也是如此,任自己和他對峙。
最終,妥協的還是,終于用嘶啞的聲音,緩緩喊出了兩個字:“大人。”
天嬰聲線極其細,即便沙啞,卻也有幾分纏綿的味道。
遠的男子淡淡地應了一聲,“嗯。”
他聲音如他的琴聲,清冽低沉,迷人心,讓人沉淪,實則高遠冷酷,沒有。
然而此刻,這一問一答像人的耳語,就像下一刻,兩人就會放下隔閡,如膠似漆。
只有燈罩中的火蝶好似知到這暴風雨前的危險,拼命地撞著燈壁。
這兩只火蝶是容遠給的,能在黑夜中照亮,能在寒夜中取暖,陪天嬰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無妄川的冬夜。
容遠送的東西,總是視若珍寶,這對火蝶也不例外。
即便知道它們不愿意呆在這小小的燈罩中,卻從來不準備放了它們。
此時此刻,蹲了下來,看著他們悠悠道:“對不起。”
打開燈罩的門,在發現缺口的一瞬間,火蝶奪門而出。
天嬰站起來,仰頭看著它們融化了一片片停在空中的雪花,朝天際飛舞而去。
今早,天嬰從海中的小仙們口中聽到了一條流言:
孤神暴斃前將能夠復活他的力量灑落大地,神們踏遍千山萬水也尋他不得。
原來天神竟然將這力量藏在了最不起眼的草種之中,每一年生發芽,每一年凋零飄落,生生不息,尋找適合它的容。
而天嬰,就是那合適的容。
天嬰無意中吃到了那棵草,也因此一夜妖,化了人形。
作為草種容的天嬰需要百年時間讓著力量在自己生發芽,然后在將其獻祭給孤神,喚醒孤神。
“所以你當年救我,養我在邊,只是因為我是草種容,是獻給孤神的祭品,對嗎?”
天嬰凝視著遠方被霧氣繚繞看不清容的男子。
“是。”
他答得毫沒有毫遲疑。
天嬰以為他至會遲疑一下,至問一下自己是從哪里聽來的流言,又至會流毫的愧疚,而不想,他答得決絕又坦然。
即便早有準備的天嬰一下子覺得天旋地轉,大腦嗡嗡作響。
天嬰咬著,直到到了腥甜。
他的狠辣決絕,連妖都自愧不如。
他是披著謫仙皮囊的惡魔。
詐尸還魂般跳的心臟劇痛后,好像已經疲憊至極,跳得越來越慢。
“你過我嗎?”再一次問了這個俗不可耐的問題。
“你覺得呢?”他反問。
曾經他也這樣反問過,而那時天嬰傻傻地答:“我覺得。”
那時候他會輕笑一聲,“真傻。”
這次天嬰卻道:“我在問你,我要你答。”
兩人相,第一次強勢。
而這次,容遠沉默了。
這片刻的時間,那對火蝶早已經飛得無影無蹤。
大殿一片寂靜,真如時間停滯了一般,天嬰只聽見微弱的心跳聲。
冰冷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沒有。”
在這兩個字在大殿中回響之時,天嬰那微弱的心跳,停止了。
以為聽到這句話會嗷嗷大哭。
然而眼眶干,最后一滴淚都流不出來。
天嬰還是兔子時,聽見隔壁家的書生說那些聊齋故事,書生救了妖,妖會以相許,說到最后書生還會搖頭換腦酸溜溜地念叨:
[問世間為何,只人生死相許。]
那時候墻角的天嬰啃著爛菜葉,心中卻又偉大的理想:
如果有一天化了人,也要試試這丟了命都要的是什麼滋味。
然后化了人,像話本子中一樣,遇見了容遠,落了紅塵。
話本一樣的開頭,卻是猜不到的結局。
他救了,卻只是為了要的命。
卻得瘋魔,得無可自拔。
欠他一條命,他欠一世。
最終,看著祭壇下熊熊的烈火一字一句道:“救命之恩,現在還你,你欠我的——”
說罷,縱深一躍,展開雙臂跳了為準備的火祭壇,沒有再看容遠一眼。
“——不要你還了。”
問世間為何?
我用百年時間只得出三個字:
——不值得——
天空中停止的雪,瘋狂飄落。
是仙界十萬年來最大的一場雪。
——————————
天嬰覺得很痛,痛不生,烈火焚燒著的發,灼燒的脾肺。
而然就在火苗將的心一寸寸吞噬之后,突然不痛了。
然后沖破了火海,和萬千的火花在旋轉中升騰。
那種覺就像化繭蝶,就像一場涅槃重生。
但是天嬰很清楚,不是凰,不會涅槃,只是死了,這些火花或許正是燒得支離破碎的靈魂。
飄了宛如永恒的無涯的黑暗之中。
的傷痛也好像也在這片虛無之中慢慢消失。
在那里漫無目的地漂浮流浪。
突然,開始有了知覺,開始到不適,這種不適將從黑暗中喚醒。
還沒有睜開眼,但是覺得自己全涼颼颼的,全不適。
這樣的覺悉又陌生,了睫,緩緩睜開了眼。
發現自己蜷在地上,手上腳上都被綁著最低級的縛妖索,上只穿了一件僅可掩的麻短。
猜你喜歡
-
完結1191 章

前方高能
這裡有最危險的任務,有最豐厚的報酬。 下一秒可能是生命的終結、可能是不能回頭的深淵,也有可能最後成為神,站在眾生的頂端!
353.7萬字8 9782 -
完結1756 章

醫流武神
一代魔君,逆天重生為復血海深仇,重回都市,掀起血雨腥風當其鋒芒展露的剎那,美女院長,萌呆蘿莉,清純校花,冷艷總裁紛至遝來
554萬字8 22216 -
完結4359 章

九天造化訣
地球末世的少將軍楊心雷,在最后改造龍骨鳳血的時候失敗,意外穿越到了迷川大陸,成為趙家整天被人欺負的入贅女婿。掌控天級功法九天造化訣,魚躍龍門,潛龍翻身!往常欺負老子挺爽的?現在一個個踩在腳下!老婆對自己不理不睬?老子還不一定看得上你呢!魔種…
399.9萬字9.13 9590621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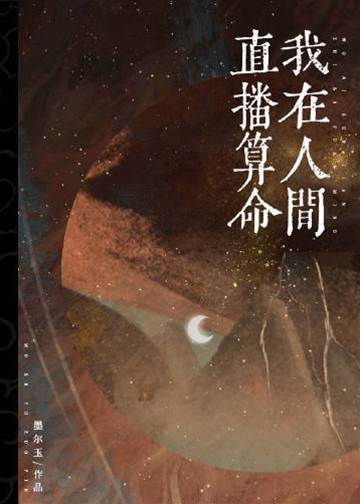
我在人間直播算命[玄學]
安如故畢業回村,繼承了一個道觀。道觀古樸又肅穆,卻游客寥寥,一點香火錢也沒有。聽說網上做直播賺錢,她于是也開始做直播。但她的直播不是唱歌跳舞,而是在直播間給人算命。…
134.6萬字8 82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