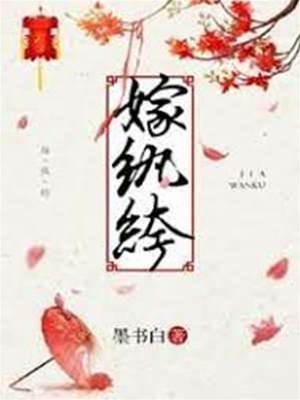《權傾裙下》 第16章 第16章 除夕
書房中,趙嫣給孤星看那支護腕造型的袖裏菖。
「卑職已檢查過了,此的確是袖箭,外並無問題。只是……」
孤星將袖裏菖重新奉還,方在趙嫣疑的目中繼續道,「只是此小巧,應是給子防用的。」
見趙嫣擰眉,孤星垂首,忙補上一句:「若是半大年,也可使用。」
護腕上的鏤花菖細華麗,的確是子喜的風格。何況年生長極快,骨量一天一個變化,有幾個會去定製這等用不了幾個月的兇防?
是嘲諷東宮太子男生相,還是懷疑……
趙嫣不敢繼續揣測,看著面前這件都覺得扎眼起來。
抓起袖裏菖丟出門外,然而手揚在半空中頓了頓,又慢慢收了回來。
如今頂著趙衍的份,須得忘記自己的原名與喜好。而趙衍是個寬厚到近乎傻氣的人,斷不會因為一支疑似人使用的袖箭而心存芥,流慌。
趙嫣索以不變應萬變。倒想看看聞人藺那張人畜無害的皮囊下,到底存了怎樣的心思。
僅是須臾便沉靜下來,趙嫣恢復了東宮太子應有的溫和敦厚,握著那暗藏殺機的袖裏菖道:「對了,孤的那兩個故,可有下落了?」
冬節過後,趙嫣便暗中命孤星去明德館,找尋與故太子有過書信往來的王裕與程寄行。
有很多事想問這兩人。如今大半月過去了,按理說應該有結果了才對。
孤星也是為回稟此事而來。
沉默半晌,他如實稟告道:「回稟太子殿下,那位姓程的貢生七月中突發急癥,猝死於寢舍。他鄉下的寡母認領了程生的,並未提出什麼質疑,沒幾日便下葬了。」
趙嫣訝異,忙問:「什麼病死的?」
孤星道:「似是通宵挑燈讀卷,發心疾。」
趙嫣莫名聽得心尖發涼。
一個月明德館暴斃兩名貢生,與趙衍有集的沈驚鳴與程寄行皆先後而亡,世上真有如此巧合之事嗎?
想了想,問:「查過程寄行的病史麼,確定死於心疾突發?」
孤星明白主子的意思,點頭道:「卑職自稱為程生同鄉,向其同窗打探過此事。可奇怪的是,同窗皆言程生素日康健,騎一流,連風寒小病都極有過。翻看明德館今年來的儒生出勤冊子,程生亦是滿勤。」
「這說明,這一年來他從未告過病假。」
趙嫣瞭然,這實在不像是一個患有心疾之人該有的表現。
「王裕呢?」
趙嫣將希寄托在這最後一人上。
「程生病故不久,此人便謝師雲遊了,至今未有音訊。」
孤星抱拳道,「殿下放心,卑職正在全力追查。」
不太對勁。
多儒生學子視科考為登天之梯,盼魚躍龍門,這個王裕已是貢生份,離最終殿試僅有一步之遙,為何偏偏在此時選擇辭師遠遊?
心中疑竇漸濃,趙嫣覺得自己有必要再與柳姬談談。
剛行至承恩殿門口,便聽到裏頭傳來一陣稀里嘩啦的傾倒聲。
流螢呈來的新鮮糕點,剛要勸,趙嫣便止住的話茬道:「母后只說不許出門,沒說不許我去看吧?」
說罷親自接過糕點托盤,推門進去。
一隻靴將才邁進殿中,便踩到了一本仰躺在地磚上的舊書,遠還橫七豎八躺了不紙筆書卷,幾乎沒有落腳之。
柳姬支棱著歪在窗邊坐床上,正百無聊賴地擲棋子玩。
一枚白子蹦到了趙嫣靴下,順勢拾起,將它補在了棋盤上的斷點。
柳姬挑眉,朝看了過來。
「呵!這還沒到清明節呢,殿下怎的就想起來看我啦?」
大人一開口便夾槍帶棒的,字字不提委屈,但字字都暗諷足殿中的無聊至極。
「想讓母後放下戒心,總得需要時日。再說了,我這不一直在等你想明白,給我答覆麼。」
趙嫣被逗笑了,將裝著各緻糕點的托盤置於案幾上,隨即規矩坐在對面,「聽流螢說你吃甜食,便讓膳房多做了些。」
柳姬皺了皺鼻子,半晌,沒忍住挑了一塊豆糕塞中,哼哧道:「我沒什麼好答覆你的。既然已確定趙衍不在了,真相如何又有何重要?」
「若真這麼想,你就不會冒險回宮了。」
趙嫣也不廢話,取出那張曾與趙衍書信往來的名單,「這三個人,你認識嗎?」
柳姬的目從紙箋上一掠而過,不假思索:「不認識。」
「沈驚鳴和程寄行死了,王裕下落不明。」
趙嫣道,「死在太子出事前一個月。」
聽到這話,柳姬那雙玩世不恭的琉璃眼才微不可察地一,很快又若無其事地捻起一塊新的糖糕來。
柳姬撒謊了,幾乎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守口如瓶。
趙嫣心知肚明,適時退讓,從袖中取出另一張字箋平在柳姬面前——
是在沈驚鳴贈予太子的那本《古今注》中發現的字條。
「那我換個問題,這個『拂燈』是何意?」
這一次,柳姬的目在力紙背的紙箋上停留了許久,神幾番變化。
回道:「撲棱蛾子。」
「什麼?」
趙嫣一滯,隨即慢慢擰起眉頭,「我並非在與你開玩笑。」
「我也並非在與你開玩笑,你沒仔細讀過那本《古今注》吧?」
柳姬已是不耐,咽下糕點道,「『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①拂燈,便是飛蟲,俗稱撲棱蛾子。」
趙嫣愣住了。
沒想到自己視作重要線索的,費盡心思去追察的紙箋,竟只是沈驚鳴隨手謄寫的飛蟲別稱。
柳姬捧著糕點,眼睜睜瞥見趙嫣緩緩垂下眼簾,眼中的彩明顯黯了下去。
記憶浮現腦海,面前的影變得模糊斑駁,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與之形似的年。
曾幾何時,柳姬與趙衍也曾於此執子對弈,嬉笑調侃。
「趙衍,你怎麼跟個木頭人似的,邊一個伺候的人也沒有?」
大剌剌盤坐著,喋喋抱怨,「害得我整日只能對著你這張小白臉,好生無聊。」
趙衍將外袍鬆鬆照在單薄的肩頭,溫聲道:「人沒有,不過孤有個孿生妹妹,甚是漂亮可人。」
「有多可人?」柳姬兩眼放。
趙衍手抵著下頜沉思良久,方慢吞吞道:「嗯……和孤一樣。」
柳姬作勢要打,趙衍卻愉快地聳肩低笑起來,笑著笑著,又咳得天昏地暗。
柳姬終是不忍,懸在半空的掌終是輕輕落下,改為給他背順氣。
「既是這般疼,為何不護在邊?」問。
趙衍氣吁吁地搖頭。
「孤弱無能,常惹生氣厭惡。何況東宮並不安全,孤不想……將拖泥淖中。」
「厭惡你?那你還這般掛念著。」
趙衍只是搖首笑笑:「我知道嫣兒說那些都是氣話,因為一心虛,便喜歡氣勢洶洶地反問回來。譬如『誰稀罕你的東西』『誰擔心你了』……說完氣話又會一個人悄悄躲起來後悔,心的模樣倒與你有幾分相似。」
他眼中全是兄長的寬厚溫,應允道:「下次有機會,定然引薦你們認識。」
柳姬沒有等到他的「引薦」,倒是記住了趙衍裏那個一心虛便下意識反問的小姑娘。
可憐的小公主與一樣,都被剝奪了原本的份和姓名,頂替別人坐在了搖搖墜的東宮危椅上。
「那麼你呢?你為何在意太子的死因?」
柳姬不自覺放輕了聲音,「我聽趙衍說過,你似乎很討厭他。」
那極低的「討厭」二字,如同細針刺痛趙嫣心中最脆弱之。
蜷起了手指,上等的料在指間起了褶皺。
「是,我討厭他。」
低聲道,「討厭他背負那麼多人的喜與希冀,而我再如何努力也從不被認可。討厭他明明脆弱得連自己的命都無法掌控,卻還總想著去照顧別人……」
僅是一瞬,低垂的眼簾重新抬起,眸澄澈堅定。
「可那又怎樣?他是我脈相連的兄長,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在乎我的人!」
低的嗓音如珠玉落盤,擲地有聲。
柳姬微張瓣,久久不語。
趙嫣以為今日又是無功而返,不由輕嘆一口氣,起離去。
「王裕在滄州有田產。」
後驀地傳來柳姬低沉的嗓音。
趙嫣詫異回首,見柳姬拍了拍指尖的碎屑起。
「我知道的並不比殿下多,既然目標一致,與殿下合作也行。」
柳姬環顧承恩殿,拋出了自己的條件,「我要行自由。日日足屋中,我已是待到厭煩了。」
如雲開見日,柳暗花明。
趙嫣攏袖一笑,輕而鄭重道:「當然。」
轉眼便是一年歲末,除夕在滿城煙火的熱鬧中如期而至。
梁州牧帶著數以百車賞賜搜刮而來的珍寶滿載而歸,厲兵秣馬。而朝廷揚湯止沸,圍城之急解了不到半月,宮中已是歌舞昇平。
除夕家宴,皇帝並未出席。
趙嫣與那幾個妃子及未出嫁的公主不,索尋了個借口提前回了東宮。
沐浴洗去一的疲乏,趙嫣只在發尾鬆鬆地綁了一條君子髮帶,裹著厚重的狐裘出來,便見一襲緋的柳姬提著一小壇羅浮春②迎面而來。
「殿下怎的這個時辰回來了?」
解除足后便恢復了以往的隨,來去自由。此時未施黛,五竟比塗脂抹時更為英氣清晰。
一提起家宴上所聞,趙嫣便心覺煩悶。
「那神教國師又藉著占卜天機的名義,慫恿父皇大興春社祭祀,以求蒼天庇佑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懨懨道,「勞民傷財不說,春社祭祀正巧在上元節。這下我連花燈也沒得看了。」
無需端著名為「太子」的偽裝時,總以「我」自稱,彷彿晝夜之中也只有這會兒能做回自己。
柳姬瞇了瞇眼,食中二指勾著酒罈晃了晃:「陪我喝酒去?羅浮春,甜的。」
趙嫣嗅了嗅空氣淡淡的甜香,宴會上本就沒幾口的肚子開始咕嚕響起來,眼波一轉,頷首笑道:「悄悄的,別讓流螢知曉。」
柳姬親昵地去勾的肩,手臂抬起來方反應過來,面前這個俏的年已然不是當初的趙衍了。
便不著痕跡放下,別過頭哼道:「你倒是不怕我在酒里下毒。」
「我這張臉,你捨得下手?」
趙嫣不聲地揶揄回去,又問,「滄州那邊,王裕可有下落?」
「暫未。」
兩人有一搭沒一搭聊著,與巡邏的宮侍看來,就是一對恩的小人。
積雪自屋檐墜落,遠中升起紅黃藍紫的束,在黑藍的夜幕中炸開朵朵荼蘼。
直到煙火完全綻開了,震耳的砰砰聲才相繼傳來。趙嫣停下腳步,朝著廊廡盡頭去。
流螢獨自坐在石階的影中,仰頭著天上的皎皎明月出神,上落著彩斑駁的煙火餘。
除夕夜放恩,其他近服侍的宮人都去偏房吃年夜飯了,趙嫣好不容易才說流螢休息兩個時辰,卻不料一個人坐在此,剪影蕭索而孤寂。
趙嫣想了想,朝流螢走去。
「流螢姊姊在看什麼呢?」
聽到後靜,流螢忙按了按眼睛回頭。
煙火升空而起,璀璨的芒下,的眼角泛著微微的紅。
那一瞬,趙嫣忽然明白了什麼。
將狐裘下擺墊了墊,坐在流螢邊。
流螢惶然起,聲道:「石階寒冷,殿下萬不可坐於此。」
柳姬皺眉將流螢按回去,也跟著坐在了流螢側。「太子殿下」與「寵妾」一左一右,將沉穩斂的掌事宮夾在中間。
這下流螢不了了,只好綳著子坐下。
「你也很想他吧?」
趙嫣托著下頜,向那被積雪與枯枝切割得破碎的明月。
流螢沒說話,素來古井無波的眼中流出近乎哀傷的神。
柳姬去而復返,不知從哪裏順來了三隻酒杯,拔開酒罈木塞一人斟了一杯。
趙嫣先取了一杯酒,流螢遲疑了片刻,也取了一杯捧在手心。
「敬故人。」趙嫣舉杯提議。
「敬故人。」柳姬附和。
三隻酒杯於月下叮的一撞,然後不約而同傾於階前,告泉下孤魂。
三線酒水自左而右-傾灑,趙嫣也紅了眼眶。
月下煙火正盛,三人依偎在這靜謐無人的角落,看同一皎月,品同一壇清酒,亦是緬懷同一個溫過他們歲月的年。
夜風拂過,滿城燈火隨之搖曳,燦若星河。
煙火尚在繼續,肅王府大門閉,隔絕了外邊的熱鬧。
書閣只燃了一對鶴首銅燈,聞人藺坐在離炭火最近的椅中,正用的硃砂筆勾畫冊子中的名字。
右副將蔡田帶來了外邊的消息,知曉主子到了那寒骨毒發作的日子,正是心不佳之時,便越發放輕聲音恭敬道:「皇上定了上元節郊祀,儲君亦會隨行。」
見主子不語,蔡田繼續回稟道:「探子來報,似是有人在暗中查探明德館那幾個儒生的消息。」
聞人藺勾畫的硃筆慢了下來。
蔡田繼而道:「近來城中混進了不江湖浪士,屬下追查之下發覺,這批人與雍王世子的幕僚多有接。郊祀將近,他們恐會有作。」
郊祀?
一旁立侍的張滄瞬間激靈,「那豈非是沖著儲君之位來的?那群狗賊,就知道與咱王爺的搶食!」
蔡田抱拳垂首,白眼翻到後腦勺。
他這個同僚什麼都好,就是太碎,腦子不甚聰明。
張不聰明毫沒領悟到蔡田的暗示,拳掌道:「王爺,這回咱們還要不要出手?」
炭盆的火映在聞人藺臉上,不見毫暖意。
他看著蒼白指尖沾染的那一點硃砂,眼睫垂下翳,像是在思索要不要救一隻來歷神的野貓。
良久,手中硃筆終是落下,毫不留地劃去最後一個名字。
「本王早說過,東宮擋的不止本王一人的道,多活幾日活幾日,又有何區別。」
熱鬧的除夕夜中,他置之事外的嗓音顯得格外冰冷。
給那支袖裏菖,已是他最大的善意。
至於最終是死是活……
與他何干呢?
猜你喜歡
-
完結758 章

慕紅裳
個性活潑的女大學生謝家琪抹黑下樓扔個垃圾,不小心跌下了樓,再睜開眼,她發現自己變成了右相府的嫡小姐謝淑柔;榮康郡王正妃顧儀蘭絕望自裁,一睜眼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四歲,一切都可以重頭再來。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與安國公家的小姑娘穆紅裳沒關係,紅裳怎樣都想不明白,她的人生怎地就從此天翻地覆……
123.8萬字8 6395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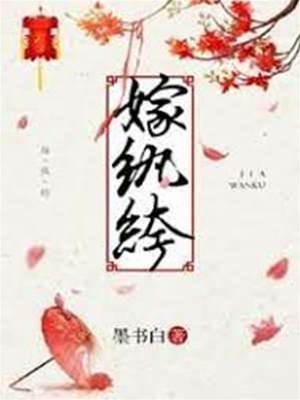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734 -
完結283 章

代嫁太子妃
簡介: 一朝穿越,她成了出身名門的官家小姐,青梅繞竹馬,卻是三人成行……陰差陽錯,定親時她的心上人卻成了未來姐夫,姐姐對幾番起落的夫家不屑一顧。她滿懷期待代姐出嫁,不但沒得到他的憐惜,反而使自己陷入一次更甚一次的屈辱之中。他肆意的把她踩在腳下,做歌姬,當舞姬,毀容,甚至親手把她送上別人的床榻……
23.2萬字8 10878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1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