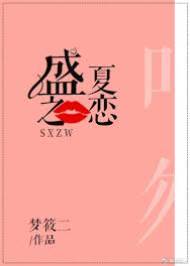《我和你差之微毫的世界》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眨眼,學期已經結束。
A市也已經是大雪凜冽的寒冬,前幾日開始下了一場小雪,晴了沒多久,鵝大雪直撲而下。
連帶著氣溫驟降,聞歌保暖一個沒跟住……就往醫院去吊水了。
今年的寒假要比往年更短些,學校剛放假時,街道上就已經喜氣洋洋地扎起了紅燈籠,大幅迎新春的橫幅。
商場更是反復循環著往年一直流行的迎財神,恭賀新年等金曲。
嗯……就連醫院注區,都人滿為患,趕場。
一年之中,最忙的時候,莫過于春節前后的這一個月了。
聞歌掩著袖子打了個哈欠,靠在椅背上看著不遠的電視機,正在播放著時下最歡迎的偶像劇。
奈何周圍的環境太嘈雜,鬧哄哄的,連電視的聲音都聽不見。
看了半天的啞劇,有些困。
但一個人又不敢這麼放心地睡著,只能勉強地撐著眼皮子。
等掛完水,步行回去。
這家醫院離家很近,走十分鐘左右就能到家。
再者,下這麼大的雪,路面上又是掃之不盡的厚厚積雪,本沒法騎車過來。
聞歌撐著傘,一路東看看西看看,十分鐘能到的路愣是走了十五分鐘。
回到家的時候,家里還沒有人,桌上著一張整百的爺爺,上面著張便簽:“聞歌,今晚我不回家,記得去樓下買點吃的。”
聞歌撐著暈沉沉的腦袋在客廳坐了一會,這才下樓買吃的。
大雪皚皚的冬日,天時短得眨眼即逝,天沉,才五點的景,街道上已經亮起了路燈。
那半灰半黑的夜空低得仿佛手可及,整個街道上的燈就像是一個個暈開的點,朦朧得像是話世界。
聞歌撐著傘,步子笨重。
隨意走進了一家面館,點了大排面加蛋的外賣后,就站在柜臺邊上等。
“聞歌?”
聽見人有,聞歌回過頭,一眼就掃到了站起來的白君奕。
即使是這麼冷的天,他穿得依然很淡薄,里面只有一件黑的,還是低領的,外面一件灰的羽絨服,一條牛仔,一雙馬丁靴。
鎖骨那一出大片皮來,看得聞歌忍不住替他牙齒打。
正好的外賣好了,聞歌拎著自己的大排面走過去。
和白君奕一起的是班長,憨厚的一個小胖子,卻壯壯實實的,關鍵是人耐寒都穿得比白君奕要多。
白君奕掃了眼手里拎著的面碗,問道:“你一個人吃啊?”
聞歌還沒來得及否認,就被白君奕拽住胳膊拉到旁的位置坐下:“一個人回家吃有什麼意思啊,一起一起,吃完我送你回去。”
明明就比高半個頭,看上去看瘦,怎麼力氣那麼大?
聞歌冒還伴著發燒,腦子有些發暈,被他這麼一拉,眼前黑了黑,也懶得再挪步,接過他遞來的筷子就開始吃面。
等吃過面,白君奕還真就認真地要送回去。
聞歌擺不了,就自己打了傘自顧自在前面走,走了半截路,回頭看了眼……
白君奕的頭上,肩膀上已經落了一層薄雪。
他的臉雪白,一雙眼睛亮得驚人,倒不像以往故意耍帥的樣子,很沉靜地跟在后三步遠的距離。
見轉頭看過來,也只是揚揚,沒說話。
聞歌一時有些不準他想干嘛,但想了想,還是朝他招招手:“我的傘可以先借給你一半。”
明顯是不太樂意的,表有些別扭,就這麼看著他。
白君奕頓時樂了,幾步上前鉆進傘里。
其實傘有些小,他半邊子都在外面,不過和聞歌一起走在傘下,覺呼吸到的空氣都不似剛才那麼清冽。
仿佛帶了溫度,暖暖的。
聞歌才沒那麼多心思去會什麼暖暖的溫度,下來之前吃了藥,現在困得不行,整個人都倦倦的,瞌睡得不行。
快走到小區門口時,的腳步一指,轉看著白君奕:“我家就在前面,你別跟過來了。”
白君奕愣了一下,抿看了一眼,義正言辭:“男孩子送孩子回家,是紳士風度,你懂不懂啊。”
“你要是有這玩意也不會欺負我一個學期了。”
聞歌翻了個白眼,跟趕蒼蠅一樣趕他:“老師還說過,這麼晚回家的小孩不安全。”
“我就也在附近。”
白君奕指了指相反方向的那一尖尖的塔樓:“就那邊的小區,跟你家很近。”
其實我真的沒興趣知道……
聞歌沉默。
白君奕不傻,自然看出來不想搭理自己。
很不客氣地像在學校時那樣輕怕一下的腦袋,看嘶了一聲齜牙咧地看著自己,笑著就跑遠了。
稚!
聞歌哼了一聲,看著他一下子跑沒影了,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捂著有些不上氣的心口半晌,深呼吸,這才邁開腳步往小區里走去。
剛邁進小區的大門,就聽見后傳來短促又連續地車輛鳴笛聲。
聞歌起初沒有搭理,被吵得煩了,狠狠地轉回頭去,一眼看見駕駛座上的溫遠時……腦子頓時空了。
三分鐘后。
聞歌被他揪到公寓樓下。
他個子高,聞歌打傘就要舉著手,起初還能堅持,沒一會,手彎就酸地跟浸了檸檬一樣。
苦著臉,眼地看著他:“小叔,你撐下傘好不好,手好酸……”
溫遠的臉沉得都能滴出水來,已經這樣盯了良久,要不是聞歌了解他,這會也要被他這種眼神給嚇出一冷汗來。
“素質太差。”
他搖搖頭,很不滿意,手卻過來,從手里接過傘。
接時,到涼得似冰一般的手指,眉心一攏,問道:“在外面待了多久了,手這麼冰?”
聞歌又有一陣子沒見到他了,這會見到他又怕又驚喜,只希他剛才什麼都沒看見……不然有的一通訓。
可沒忘記,溫遠說過讓不要和白君奕走得太近。
不過怕歸怕,聞歌在溫遠的面前已經越來越肆無忌憚,出已經左手被扎了兩次的手背湊到他跟前:“才不是在外面待久了,我冒去掛水了,掛了一下午,手怎麼也暖不起來。”
溫遠彎腰看了眼手背上的針孔,的皮細,針孔并看不太仔細,只看清了那發青的皮和清晰的管。
下意識地想出手去用手心捂暖的手,剛抬起又覺得不太妥當,就隨意地垂在側:“那趕上去吧。”
“可小叔你剛才還說有話跟我說……”聞歌回手,放到邊呵了一口氣,剛到一暖意又被迎面撲來的冷意取代。
“有喜歡的男孩子了?”
他突然問道。
聞歌卻是一驚,嚇得差點下都要掉了。
“啊”了一聲,支支吾吾了半天,臉卻可疑的紅了……
“那、那是白君奕。
我……我沒有喜歡的男孩子。”
說完這句,聞歌連他的眼神都不敢對視,低著頭,雙手十指叉地玩著自己的大拇指。
可那表現,分明像是被說中了心事。
溫遠的眉頭一擰,連表都凝重了幾分:“現在的喜歡都只是好而已,過完年也就十五歲哪能分辨什麼是喜歡?”
他的語氣重了些,帶著幾分冷意,訓斥的意味頗濃。
聞歌的倔勁也上來了,下意識地就回道:“那在古時候,十五歲的及笄已經可以結婚嫁人了!”
話落,不止愣了,連溫遠都怔了一下。
那臉……徹底黑了。
“現在我說話沒用了是不是?”
那語氣得低低的,似乎是從嗓子深傳來的,涼得幾結冰。
聞歌一個哆嗦,后悔不已……那麼快干嘛!
埋著腦袋,盯著腳面上沾上的一層冰凌,都快要哭了。
不接話,溫遠也不說話,氣氛頓時詭異地沉進了沉默里。
就在聞歌醞釀著怎麼服個時,溫遠上前一步,把手里拿著的傘塞回的手里。
不可避免地,握住了的手腕,又到了的手指。
他皺著眉,目凝視著,并沒有責怪,卻讓人心虛得不敢直視。
聞歌咬了咬,正要道歉……
他把傘回給,沉著嗓子說了句“趕回去吧”,轉便走。
聞歌傻眼地看著他轉一走了之的姿態,頓時慌了,幾乎是下意識地,就手抓住了他的手,牢牢地攥。
“小叔……”
那一瞬間的,手上的溫度涼得他心驚。
剛回頭,就看見臉雪白的,是不健康的蒼白,那雙眼睛黑漆漆的,看上去也是無打采的樣子,就這麼看著他。
流出一恐慌,一張,一哀求。
溫遠眉頭一皺,轉過。
下一秒,聞歌就在他的面前,綿綿地栽倒。
———
聞歌在摔倒前后,其實都是有意識的,并不是徹底失去意識地昏過去,是……太困了。
然后悶悶的,有些不上氣來,剛才一急,就這樣了……
從醫院開了藥被溫遠送回家的一路上,聞歌都耷拉著腦袋。
徐麗青還沒回來,家里空的,只客廳留著一盞燈,燈孤寂。
溫遠拎著藥進來,看著冷清的屋子皺了皺眉頭:“最近一直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在家?”
聞歌點點頭,正要去廚房給他倒水,被他拉住,按坐在沙發上:“我不喝水。”
他的表明顯沉了沉,臉部廓都冷了不。
四下環顧了一周,他忽然說道:“收拾幾件服,跟我回溫家住幾天。”
聞歌呆呆地“啊”了一聲,隨即便是本能的排斥,搖搖頭,替徐麗青解釋道:“我不是一直一個人,就是最近阿姨比較忙,很晚才回家……”
“有什麼區別?”
溫遠打斷,皺著眉頭有些不悅:“需要我再重復一遍?”
他今天明顯的有些不耐。
聞歌被他這冷著的語氣嚇了一跳,眼眶頓時紅了,咳嗽了幾聲,好不容易停下來,開口說話時,聲音沙啞,還帶了幾分哽咽:“小叔,你今天好兇……”
溫遠看一副下一秒就要哭出來的表,語氣更兇了:“不準哭。”
聞歌驚愕地看著他,還未反應過來,他已經放表,幾乎無奈地朝出手來:“不收拾就不收拾,反正還留著你的服……”
話落,見還呆呆地坐在那里,靜靜地看了一會,終于有些忍不住,微翹了角低低地笑出聲來:“看來,我們需要好好談一談。”
聞歌這才回過神來,看著他出的那只修長白皙的骨節分明的手,遲疑了一下,握住他。
我在牽住你手的時候,你也要學著握住我的。
這句他說的話,聞歌始終記得。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4488 -
連載1084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3萬字8.18 22690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678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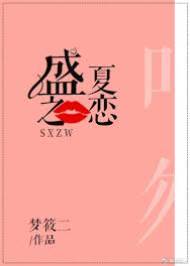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1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