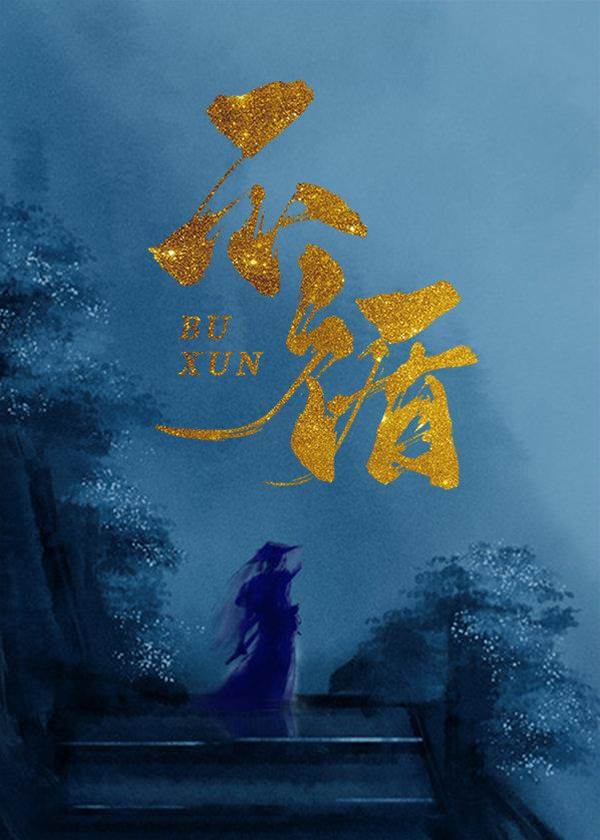《燼歡》 第14章 涂藥
惡念像夏日郊外的野草,見了風便瘋長。
就像昨晚他的妻,最的地方暴在他的利齒之下。
不能掙扎,亦推不開,只能用的十指捧住他的頭,低低地求他。
百般婉轉,楚楚可憐。
那種覺又來了。
無數枝丫藤蔓迅速鋪張開,仿佛要從他里鉆破,沖出來,將人眼前的人牢牢捆住。
瘋狂的念頭幾乎控制不住,陸縉握住的羅的指骨已經用力到泛白,往上拉的作實在太慢,太慢了……
他想,其實又能有什麼蔽作用呢?
再嚴實的也是用最細的棉絮和蠶的織的,尤其夏日,薄薄一層,脆弱不堪,在他這雙挽過弓,勒過馬的雙掌之下,稍微用力,便會徹底撕裂。
只能防的住君子,防不住小人。
君子守禮,不會做出撕人的舉來。
小人無禮,不會遵循約定俗的公序良俗。
陸縉從前是君子,即便有人在他面前主寬,他也不會奪看一眼。
而現在他想做個小人,妻妹穿的越嚴實,暴漲的念頭就越囂著想把的服撕開——
看看是不是同妻子一樣白。
看看里面究竟藏了什麼。
為什麼他明明沒見過,沒過,依舊能勾起他滿腔的邪念,讓他隔著已經能到了不可思議的。
著羅的手終于頓住,正要幾不可察地往下褪下一點,這時,頭頂忽地傳來一道聲音。
“姐夫。”
清清淺淺的,仿佛山林溪澗里流淌的清泉,清涼骨,甘甜潤澤。
只一聲,陸縉雜的思緒瞬間清明,渾瘋長的藤蔓也迅速回去。
“怎麼了?”
他眼底恢復平靜,一如尋常。
“天太熱了,不必束了。”江晚輕聲道,“就這樣便好。”
話雖這麼說,實際上,是因為被他握住的腳踝被抬高彎曲著看了太久的傷,有些酸麻。
他再不放手,那條便要痙-攣了。
陸縉低頭看了一眼,發覺被他握住的腳踝果然出了一層薄汗。
可能是他的汗,也可能是的。
陸縉下意識認為是他的,立即放了開。
“好。”
他了心思,起了,將雙手浸在盛滿冷水的銅盆里。
來來回回,反反復復。
江晚聽見了冷水聲,臉頰亦是微微燙,將起的擺放下。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自從圓房之后,一見到姐夫,好像就特別容易出汗。
剛剛只是被他短暫地握了一下,腳踝上便出了汗,應當是的汗吧。
實在太不矜持。
兩個人各懷心思,本就是梅雨天,屋里即便用了冰,依舊悶的人渾黏-膩,窗外是一片柳林,有不知名的蟬在,蟬聲如沸,的人愈發汗涔涔。
陸縉洗了三遍手,連指骨都被浸的寒涼了,眉宇間才淡下來。
了手,他吩咐康平替江晚去取一瓶紅花油。
余一瞥,看見江晚臉頰紅撲撲的,額發也汗的微的模樣,他又沉聲住康平:“再小廚房送一份冰飲子來。”
康平只略微琢磨,便知道公子這是替江小娘子的了,于是心地去問江晚:“今日小廚房冰鎮了好幾樣,有楊梅水,荔枝水,櫻桃酪,不知小娘子想要哪個?”
姐夫實在太心了。
江晚又微微出了汗,生怕他看出異常,也沒拒絕:“那便來一份櫻桃酪吧。”
“小娘子眼真好,這是當下最時興的,牛加櫻桃煎,再添一些冰塊,清涼爽口,小娘子正好嘗嘗鮮。”康平直夸口味刁鉆。
“怎麼只給我,姐夫不要嗎?”江晚靦腆的笑了一下,猶有不解。
“公子不吃甜食,尤其酪。”康平解釋道,“牛羊從不沾口,不但不飲,凡是用做的吃食公子也一概不,說是有腥氣。”
“是嗎?”江晚眼睫一眨,聲音低下去,“這口味倒是見。”
揪著手中的帕子,沒多追問。
耳卻微微燙……
陸縉幾乎是瞬間也被勾起了聯想。
他眉頭一皺,打斷康平:“話如此多,快去。”
“是。”
康平被訓的慌忙低頭,覺得公子這幾日火氣也忒大了點。
等他一去,屋子里只剩下陸縉和江晚兩個人,氣氛愈發有幾分微妙。
陸縉飲了一杯涼茶,周的熱意才沉下去。
茶碗一擱,他偶然看到了博古架上擱了一塊新送來的玉,忽然想起過幾日是他妹妹的生辰。
他之前吩咐人去采買一塊上好的暖玉,準備給陸宛當生辰禮,應當就是這塊。
然眼下再一看,這玉通剔,凈白瑩潤,陸縉又覺得這玉與陸宛那樣大大咧咧的子并不配,比起玉來,那丫頭恐怕更想要一匹小馬駒。
反而,與他這個子清清淡淡的妻妹更相配。
暖玉在他手中把玩了一遍,陸縉遞給了江晚,略帶了幾分歉意:
“前幾日是我記錯了,原來這玉未曾丟,是被擱到了博古架里。你既已找了這麼久,白白勞累也不好,這玉便贈與你,也算是賠禮。”
江晚甫一聽聞那玉沒丟,沉甸甸的心事總算擱下。
然打眼一看,一眼便看出這玉的極好,恐怕價值不菲,并不敢收。
只說:“原也不費什麼事,這玉既然沒丟自然是再好不過,姐夫不必客氣。”
“無妨,本就是暖玉,你們姑娘家佩著更好。”陸縉直接將玉放下。
江晚這些日子朝夕相,已經十分明白姐夫的子。
陸縉雖看起來溫和有禮,但骨子里卻是個極強勢的,只要他決定的事,旁人便沒什麼回絕的余地了。譬如圓房那晚,他給過機會,當時沒聽懂,亦是忽略了他們之間的差距,后來便生生躺了三日。
江晚不敢再拒絕,輕聲謝過。
其實,這麼多年,除了舅舅和為義兄的裴時序,很收旁人的東西。
舅舅對雖好,卻實在太忙,給的東西多揀貴的,并不十分花心思。
裴時序倒是肯花心思,但有時心思又太過細膩,且有些偏執,常常擔心這個不喜歡,那個不喜歡,于是便經常送一些墨守規甚至是重復的東西,收了十幾年,到后來已經沒什麼波瀾了。
陸縉是簪纓世家里教養出來,選東西的眼極好,譬如這塊玉,澤瑩潤,手更是極佳,雖是隨手送的,卻也想到了這是暖玉,十分合兒家。
既貴重,又不乏心思,的確十分周到。
江晚對這塊玉,其實有些喜歡。
只可惜,他們份差的太多,又是這樣的關系,為防人背后說口舌,即便是喜歡,日后也不打算佩在外面。
且并不差玉,從前也收了許多塊,至于這一塊,最多是裝在香囊里,帶著。
外面的雨還在下,淅淅瀝瀝的,天已經快黑了,不知什麼時候能停。
康平尚未送冰飲子來,藥油倒是先送到了。
大夫不必來了,陸縉便了一個使替將藥油進腳踝去。
那使年紀不大,從未幫人上藥,手底下沒個分寸,忽輕忽重的,弄得江晚時不時抓著椅子扶手低低的氣。
忍著痛,聲音也忽高忽低的,仿佛在刑。
聽在陸縉耳里,卻仿佛在另一種刑。
他想,他大概真是瘋了。
聽妻妹吃痛,卻不合時宜的想起了不該想的事。
多年的教養使然,只一瞬,陸縉很快下去,住了使:“你下去吧。”
使自知做的不好,答應了一聲便垂著頭下去。
江晚腳踝愈發紅腫了,沾著藥油,搭在杌子上,慘兮兮的。
兩人心照不宣,這回也不必多言,陸縉看了一眼的腳踝:“我來?”
“好。”江晚低低地答應,以為這回還是同剛才一樣。
但其實很不一樣。
畢竟剛剛陸縉只是看了一眼,這回他上了手。
他的手寬厚溫熱,一掌便將整個腳踝包住,比之方才的使不知多了幾倍的力道。
只了一下,江晚便急促地呼了一聲痛,蜷著想往回收。
然而卻被陸縉直接往前一扯,重重按在了他膝上。
“忍著。”
陸縉不留面。
江晚眼底登時便被出了淚。
陸縉手腕一頓,難得解釋了一句:“長痛不如短痛,這藥油需全部進去才有效,你是想瘸上一旬,還是想養個三兩日?”
“我想快些好。”江晚忍住眼淚,毫不猶豫。
“那就不許再。”陸縉命令道。
“嗯。”江晚答應下來,雙手又虛虛抓住陸縉的肩,試圖尋找一個借力的地方,“姐夫,我能不能扶著您……”
“扶好。”陸縉沒拒絕,方便將上半靠上去。
然后他便挖了一大勺藥油,重重地替進腳踝。
好疼。
江晚嘶了一聲,卻牢記他不許出聲的命令,又咬著,生生咽了回去。
一開始,當真覺得陸縉幫比使幫還疼,但慢慢的,江晚覺出一些不同來,姐夫的手力道十分均勻,準按在位上,且更加寬大,能照顧到每一寸的傷。
疼中又麻,麻中又熱,很快,江晚便覺得沒那麼疼了。
反倒有一種筋脈被活的酸爽。
趁著稍微好一些,江晚又低頭看了一眼,陸縉的大手完全包住了的腳踝。
江晚只看了一眼,莫名臉熱,連忙又扭回了頭,閉著眼抓了陸縉的肩。
陸縉只低著頭盯著紅腫的腳踝,專心致志,似乎也沒有多余的想法。
只是按著腳踝的手卻越來越快。
江晚額上已經出了汗,疼且麻,已經沒有思考的余地了。
藥油是不是倒多了?
江晚約覺得不對,又想,那是姐夫,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只愈發抓了陸縉的肩。
卻又不敢真的搭上去,便微微弓著背。
康平端著托盤進來時一眼便是這一幕。
瞳孔微睜,手腕一抖,手中的托盤倏地打翻在地。
“砰”的一聲。
陸縉和江晚被這靜驚的猛地頓住,一回頭,只看見不遠潑了一地的櫻桃酪……
猜你喜歡
-
連載771 章

心有瑤光楚君意
陸瑤重生後,有兩個心願,一是護陸家無虞,二是暗中相助上一世虧欠了的楚王。 一不小心竟成了楚王妃,洞房花燭夜,楚王問小嬌妻:“有多愛我?” 陸瑤諂媚:“活一天,愛一天。” 楚王搖頭:“愛一天,活一天。” 陸瑤:“……” 你家有皇位要繼承,你說什麼都對。 婚前的陸瑤,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未來的皇帝老子楚王。 婚前的楚王,奸臣邪佞說殺就殺,皇帝老爹說懟就懟。 婚後的楚王扒著門縫低喊:“瑤瑤開門,你是我的小心肝!” 眾大臣:臉呢? 楚王:本王要臉?不存在的!
114.1萬字8 7666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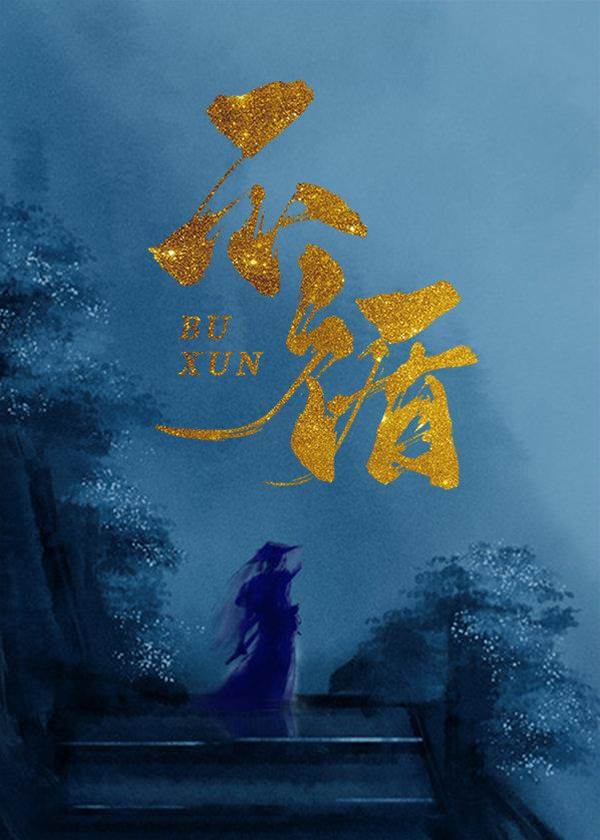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