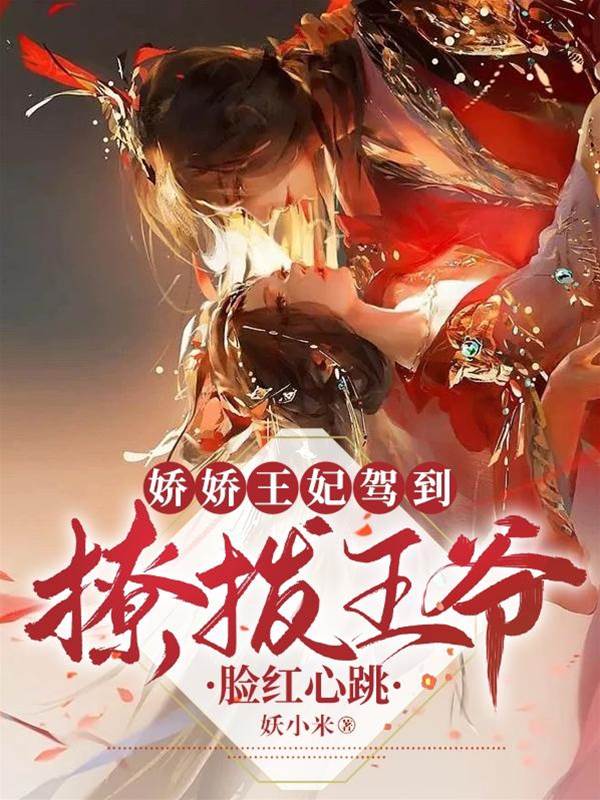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我妻薄情》 第 14 章 夜半驚
m.kelexsw.com
夕西下,香客們均已歸家。
程丹若收拾藥箱,和白芷一道上山。這幾日,們都借住在天心寺里,因為楊枝玉的方子,不收錢。
小院清凈,推門進去,不聞人聲。
白芷立即發怒:“郝媽媽又懶了,姑娘回來,熱水沒有,飯也沒有。”
程丹若嘆了口氣。
不可能獨自上山禮佛,黃夫人派了一個媽媽并一個車夫跟隨,算是照看。
可郝媽媽并不好,辦事推三阻四,耍一把好手。今天說要下山義診,就推說中暑,要在屋里休養,并照看院子。
現在呢,人影不見,連頓飯都不給拿。
“算了。”住尋人的白芷,“我去提飯,你熏熏屋子,天要暗了,不要讓蟲爬得到都是。”
白芷道:“姑娘也別太縱著這些老媽媽,們就是欺怕。”
“我不是縱著,是沒辦法。”程丹若說。積年的老仆連正經主子都敢折騰,何況一個寄人籬下的孤?
人家欺負的就是,而毫無辦法。
和黃夫人告狀,黃夫人最多明面上訓斥幾句,郝媽媽畢竟是的人。而這樣只會讓人背后說閑話,并惹來黃夫人的惡。
威利就更扯淡了。
威從何來?利從何來?
宅斗也要有底牌,除非打算一副藥把人弄死,不然,真的一張牌也沒有。
只能忍下算了。
主仆二人分頭行,一人打掃屋子,提熱水,一人去廚房領飯食。
天心寺的齋飯還不錯,程丹若分了一半的菜給白芷,自己回房去吃,自己則留在房間里,準備一段安靜的晚餐時間。
“阿嚏。”吃素時,突然打了個噴嚏。
程丹若裳,納悶是不是吹了風。
夾素火時,又是“阿嚏——”一下。
心中警鈴大作,立即起,提起水壺倒杯熱水,然后環顧一周,悄悄從袖中取出一袋板藍,倒進去飛快攪勻,一起喝下。
然后再用水沖一沖,洗掉板藍的氣味,若無其事地坐回去繼續吃。
接著,第三下。
“阿嚏。”
:“誰在背后說我壞話?”
是誰呢?
一院之隔,清凈而干凈的廂房中,晏鴻之正在和主持夢覺大師吃晚飯,謝玄英陪侍在側,替老師執壺。
兩人不免談到程丹若。
夢覺大師指著桌上的冰,道:“這就是程施主給予敝寺的方子,生津解暑,清涼降火,夏日食來適意得很。”
冰加了芝麻、花生、紅糖,比飲料更香甜可口。
晏鴻之吃了小半碗,才道:“此得來尋常,難得別出心裁,只不過,怕是人家姑娘的家傳方子,你怎好意思收?”
“收下才是慈悲。”夢覺大師簡單介紹程丹若的來歷,“程施主家在大同,寒之時,舉族俱沒,已無親族在世。”
寒之,指的就是五年前,瓦剌突破居庸關,侵大同一帶,大夏兵連連敗退,胡人屠城數座,死傷近十萬的慘劇。
當時事一出,舉國震驚。
更令人無語的是,胡人最后不是被擊退,而是自己戰線拉得太長,收獲又足,自己撤退的。
這下,連謝玄英都不有幾分惻然,父母雙亡,尚有宗族照顧,舉族俱沒,那是真的孤苦無依,世飄零了。
“程施主掛念父母,想為他們在這里點一盞長明燈,可惜無余財,便以膳方相抵。”夢覺大師不疾不徐道,“我若不收,如何能安心,唯有收下,才不負一番孝心。”
晏鴻之嘆息兩聲,頗為贊同,又慨:“去歲長江水患,不知多災民,好些個男子,手腳俱全,卻以乞討為生。而這位程姑娘世飄零,卻堅忍向善,寺下義診,普度眾生,多男兒竟不如。”
夢覺大師不道:“此事我有所耳聞,長江水災竟如此嚴重了?”
“可不是,近二三十年,每四五年便要遭災一次,比前朝可嚴峻得多。”晏鴻之不是只會空談經學的大儒,對實務頗為關心,“朝廷再不重視,必大禍。”
夢覺大師點點頭,兩人就歷朝的水災開始了新的話題。
此時此刻,他們并不清楚,長江的水災今后只會越來越嚴重,而這不管是明清還是大夏,都無法徹底解決源。
*
長江為什麼水患頻繁?
兩位當世大儒深探討的難題,假如去問程丹若,馬上就能答上來。
造水災的原因是圍湖墾田,而伐山砍木的背后,是人口日益增長帶來的必然矛盾。
大夏1370年建朝,比明朝晚了兩年,一百多年過去,已經到了麥哲倫環球旅行的年代。
封建社會已經走到最輝煌也是最危險的階段。
但這和一個父母雙亡的孤,有什麼干系呢?
和白芷各自用了晚飯,稍作梳洗后便早早睡下。
寺廟的禪房有一浸染到深的檀香,出世之地的氣息平息了心的紛雜思緒,很快夢。
不知道是不是卸下了照顧病人的心事,這一覺睡得甜又沉,好似一直一直都醒不過來,倦得厲害。
模模糊糊間,似乎有人在。
天亮了嗎?
程丹若竭力撐開眼皮,卻一點都沒有蘇醒的跡象。
不想,噢,看來我是真的冒了,睡前吃的那袋板藍一點用都沒有,該不會是病毒冒吧?
胡思想著,有人推了推:“姑娘,醒醒。”
程丹若終于醒來,支起沉甸甸的頭:“怎麼了?”
“廟里的小師傅來敲門,說有位香客被蛇咬了。”白芷輕聲細語地解釋,“好像有點嚴重,問姑娘能不能去看一看。”
似有顧慮,猶豫了下,勸道:“姑娘,是位男客,深更半夜的,不若我去回絕了吧。”
程丹若按按額角,想想道:“我還是去一趟吧。”
白芷道:“那我郝媽媽……”
“才生事,必是要編排我的。”程丹若穿上繡鞋,系好外衫,掬捧冷水潑到臉上,總算清醒了些,“無事,不睡到日上三竿不會起來,同說我們下山義診去了,必不會多問。”
提起藥箱:“走吧,被蛇咬傷可大可小,別誤了時候。”
外面還是漫天星辰,涼風吹過,程丹若打了個寒戰。
院門外,相的小和尚正焦急地等待著,見出來,連忙提燈照路:“程施主慈悲,請快隨我來。”
程丹若已經清醒,問:“是什麼蛇咬的,多久了,人在哪兒?”
小和尚才十歲不到,不然也不能半夜來敲門,口齒卻伶俐:“不知是什麼蛇,大約是一刻鐘前,晏施主已經被送回禪房了。”
程丹若奇怪:“怎麼,不是在屋中被咬,是在外頭?”
“今夜月甚好,晏施主到山上賞月去了。”小和尚認真回答。
程丹若啞然:“那病人況怎麼樣?”
小和尚臉皮繃,聲音也干的:“很不好。”
無語,卻不好問小孩子,只好加快腳步。
虧得目的地與所住的院子所隔不遠,不出一炷香即到。一進門,就看到歪在榻上的老人,燭燃燒,暈搖,立在床前的公子轉過頭,霎時間,珠玉生輝,昏暗的禪房頃刻明亮。
月白衫子,墨發如瀑,乍然看去,辨不清是男是,是仙是妖,只覺此景非人間該有,此人非紅塵之貌。
好若聊齋中古廟的艷遇。
“程姑娘。”謝玄英垂下眼眸,“深夜驚擾,事非得已,請你看看我的老師。”
程丹若回神上前,藥箱往地上一放:“傷口在哪里?”
老人滿臉慚愧地,竟然十分不好意思:“冒犯了。”
“卷起來,讓我看看傷。”救人如救火,程丹若暫時摒棄雜念,打開藥箱,吩咐幫忙。
謝玄英怔了下,手忙腳地幫忙卷腳。
小,有一紅腫的傷口,還在流。
程丹若自藥箱中取出小銅鏡,端近燭臺,借燭火的反,仔細觀察傷口:“知道是什麼蛇咬傷的嗎?”
晏鴻之倚靠在枕上,有氣無力地回答:“那毒蛇在背,我沒瞧清。”
“慢慢呼吸,不要張,我問什麼,你答什麼,好嗎?”程丹若的語氣輕又冷淡,無端予人安心,“有沒有覺得不上氣?”
晏鴻之忍著不失態:“尚可,只傷疼得厲害。”
“發熱還是發脹?”
“又熱又脹。”
“您別張。”程丹若取出一條雪白的棉布帶子,松松系在傷口上方,又掏出兩張干凈的棉布片,沾竹筒里的水,用鑷子夾住潤的紗布,輕地去傷口的臟污。
又問:“疼嗎?”
晏鴻之:“尚可、尚可。”
“傷還有斷牙,我現在要取出來,會有一些疼。”被蛇咬傷的最好辦法是馬上送醫院,及時注清。但現在麼,土方子加急救,看運氣吧。
程丹若拿起銅鑷子,在燭火上燒了會兒消毒,這才白芷掌燈照明,伏仔細挑揀斷掉的毒牙。
晏鴻之強忍著痛楚,悔得腸子都青了。
都怪老友,說半年前月下悟禪,忽見五彩月暈,心有所得,害得他半夜好奇,忍不住外出訪月。
然后,就被蛇咬了……
謝玄英氣惱又無奈。
他知道自家老師最是怕疼,只是不便在外人面前表現出來,有一回上山跌跤,在家接骨時,一個勁的師母。
“阿菁,痛煞我也!”他是這麼朝師母痛呼的。
師母心有不忍,親自下廚,煮了一碗極味的湯面條。
“老師,且忍一忍。”他終歸心,消了氣,認真問,“我小師傅去廚房,下一碗素面來可好?”
晏鴻之以白眼相對,的是面條嗎?
是老妻,老妻!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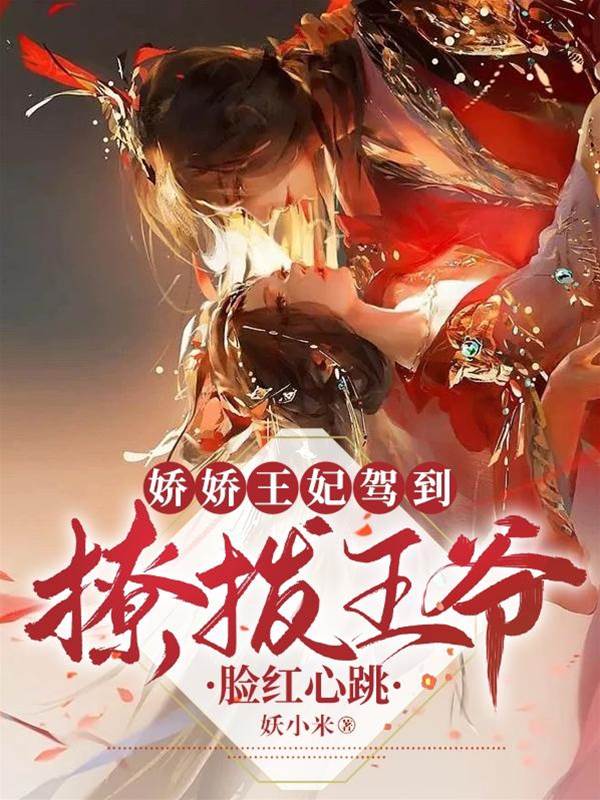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576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