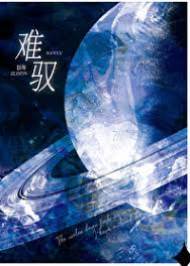《獨家偏愛:靳教授請輕輕吻》 第16章 下車
時寧想起很多事,和周治學過去的點滴,被周治學背叛、拋棄的絕,還有這些年和外婆相依為命的艱難。
為什麼,明明沒有對不起誰過,都要這麼欺負!
眼淚,無聲落下。
幾近絕的那一刻,耳邊都是嗡嗡嗡的。
直到忽然間,天大亮,熱風撲面。
一切痛苦掙扎都被了中止,渾抖著,只聽到劉總不敢置信的聲音。
“靳……靳總。”
靳宴?
劫后余生,時寧恍惚地睜開眼睛。
方才那令窒息到快要死去的惡心已經退去,不知自己是什麼況,只是車門開了,撐開眼皮,剛好有一點過樹葉隙落在眼上,燙花了的視線。
看不清車門外男人的面容,只聽他聲音沉沉。
“下車。”
靈魂驟然歸,時寧手腳發麻,卻還是撐著一口氣,將出了車外。
猛一落地,就不控制地往前栽去。
預料的疼痛沒有到來,和那次在餐廳里一樣,靳宴接住了。
不同的是,這次,正面跌在了他懷里。
淡淡的冷質香氣,不久前曾聞過,是他上獨特的香氛。
“還能走嗎?”靳宴低沉的聲音過腔傳遞到耳邊,如有實質。
“能……”艱難出一個字。
試圖穩住形邁步離開這里,卻怎麼也使不上力了。
腦中發暈之際,腳下一輕。
靳宴將打橫抱起。
前后不過一分鐘,就像是一場噩夢,腳下一踩空,驟然醒了。
醒來時,在他懷里。
遠吸煙的司機察覺到這邊的靜匆匆趕
到,一看靳宴抱著時寧離去,臉大變。
再次坐進車里,時寧看著搖搖墜的天花板,想要說一聲謝謝,眼前卻黑了下去。
只聽到靳宴吩咐司機。
“去醫院。”
……
“靳總,那位小姐醒了。”
鼻息間是淡淡的消毒水味,時寧睜開眼,就見護士轉頭去靳宴。
順著視線看去,靳宴站在窗邊。
穿白大褂的醫生上來查看了一番“沒什麼問題,多休息,等力恢復了就能出院。”
他對靳宴很是恭敬,并沒多留。
時寧躺在床上,對上不遠靳宴寂靜的眸子,思緒逐漸恢復。
想起來,他嘲諷心思活絡。
可千鈞一發之際,也是他救了。
扯了下干涸的,“……謝謝您。”
靳宴瓣微抿,態度不冷不熱地應了一聲。
護士進進出出,幫時寧扎針,又扶著在床頭坐好。
“有事按床頭的鈴就好。”
時寧點頭。
連護工都出去了,室安靜下來。
氣氛之尷尬,比上次他們在車里那回更甚。
靳宴沒打算多留,他拿上了外套,“有事自己護士。”
時寧見他要走,下意識住他。
“教授!”
男人看了一眼。
時寧想起他曾給自己的警告,下意識換了稱呼“……靳總。”
“還有事?”
他這樣刻意冷淡,仿佛是什麼臟東西,時寧頓覺如鯁在。
沒別的想法,只是不想被誤會。
“我沒有……”腳踏兩只船。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樑少的寶貝萌妻
【暖寵】他,宸凱集團總裁,內斂、高冷、身份尊貴,俊美無儔,年近三十二卻連個女人的手都沒牽過。代曼,上高中那年,她寄住在爸爸好友的兒子家中,因爲輩分關係,她稱呼樑駿馳一聲,“樑叔”。四年前和他的一次意外,讓她倉皇逃出國。四年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歸國後成了正值花樣年華。樑駿馳是她想拒絕卻拒絕不
14萬字5 38724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65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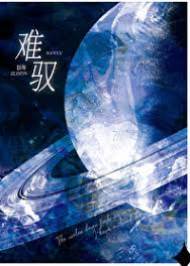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7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