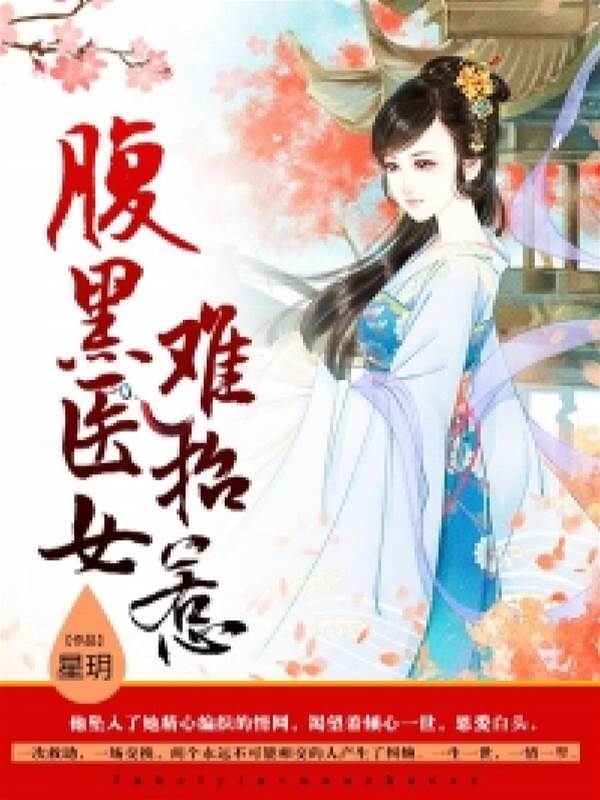《千山青黛》 第 10 章(承平被人用繩索縛了捆在馬...)
承平被人用繩索縛了捆在馬背上,正往這方向帶來。他怒容滿麵,力掙紮,口裏大罵著賊奴狗輩,卻被縛得,縱有神力也是掙不開,掙紮間抬頭見了裴蕭元,立刻大吼:“賊奴布下絆馬索,我不防落人手!你不必管我,我他們敢殺我否!”
裴蕭元明白了。
這些便是此人的同夥,或者說,是隨從,見他被擒,不敢貿然靠近,恰好承平聽到鹿哨聲趕來,暗設下絆馬索,他們得了手。
至於目的,顯而易見。
果然,那些人停在近前,當中一名頭領模樣的向他行了一禮,恭聲道:“裴郎君,得罪了王子,還海涵。隻要裴郎君肯放人,小人們立刻便走,不敢王子一汗。”
承平額頭青筋怒跳,正要再罵,被近旁一人用個口塞堵住了,麵孔登時漲得通紅。
裴蕭元瞥了眼藍人。
他傷得實在不輕,上兩傷口流不止,尋常人早已倒下,他卻仍能立著不倒,舉止還保持著這樣的風度,不見半分蹙偪之,不得不說,也算是個非常的狠人。
承平又衝著裴蕭元拚命搖頭,口裏發出嗚嗚之聲。
裴蕭元沒有半點猶豫,收劍歸鞘。
那些人目狂喜之,又似乎有點不敢相信,遲疑不決,道:“你先將人放來!”
話音剛落,藍人麵慍:“放肆!你們當裴郎君是什麽人?竟敢以己度人?”
頭領遭叱,麵惶,再無半分猶豫,立刻上去將承平放下馬背,一眾人跟著上來,兩人左右攙扶住藍青年,頭領拔出腰刀,一刀斬斷了貫穿他的箭桿,另個人從係在腰間蹀躞帶上的一隻皮囊裏取出傷藥,先草草止,縛住傷口,隨即將藍人護在中間抬著便走。整個過程極快,沒有半點雜音。
藍人至此顯然是再也支撐不住了,整個過程一直半睜半合著雙目,頭頸無力下垂,神萎靡,直到被送上了馬背,勉力坐直,這才回頭,沉沉了眼裴蕭元,隨即被那頭領幾人護在中間離去。
裴蕭元來到承平邊,拔出便刀,一刀挑斷縛住他的繩索。承平雙手得了自由,自己拔掉口塞,沉著臉,人從地上一躍而起,翻上馬。
“不必追了!”裴蕭元喊住他。
承平一語不發,麵孔漲得若要滴出來,足跟疾踢馬腹,催馬便走。
裴蕭元右掌攥住馬韁,一拽,生生地阻了那匹已蓄勢揚蹄的黃驃馬。
“這些人步伐穩健,理外傷手法練,配合無間,起來是久經沙場的敢死老兵。這種能活下來的人,出手隻講致命,更是狡如貍狐,不容易對付。況且你應當也瞧得出來,都是死士,對那人惟命是從。我們人不多,天將黑,追上去也不好得手。他若有不可告人之目的,這回失手,必然還有下回,到時慢慢比劃不遲,今日不必再節外生枝,去尋葉要!”
承平眺前方那已經走得隻剩下小點的人,片刻後,慢慢轉向裴蕭元,目濃重的慚,沒等他開口,裴蕭元又笑道:“不必說了,真不怪你,我也沒想到此人手下的反應如此迅捷,短時裏便想出這法子賺了你,換是我,也難躲開。你沒事便是大幸,且消消火,走吧,下何叔那邊可有發現。”
何晉也沒任何收獲。
這裏太過空曠,他走得比承平遠,此時才循著鹿哨之聲找來,還不知道片刻前發生的那一場意外。聽承平講來,驚怒不已,環顧四周。
“到底是什麽來頭!郎君你剛才可有問出來過?”
裴蕭元微微搖頭,“是個狠角,輕易不會開口。”
並且,對方顯然對他所知頗多,幾乎可以肯定,就是衝著他來的。為免惹出何晉更多的擔憂,這一點他沒提。
但即便如此,何晉還是關心則。
“郎君你出去總不帶人,往後一定要多跟著些,萬萬不可大意!”
裴蕭元頷首,將話題轉回到了尋人的事上,很快返道。
夕徹底地落了下去,暮四合,夜幕迅速降臨,又繼續前行找了些時候,四野俱黑。
早上出來得匆忙,沒想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也沒有做長久上路的打算,幾人隻白天在行經的驛點裏隨意吃了些食而已,早已腸轆轆。何晉提議先回去向郡守複命,而且還有一個可能,如果走的是另條道,那麽派出去的人說不定已經找到了,隻是他們還沒得到消息而已。
裴蕭元止馬於道,環顧著漆黑的四周。
今天也隻能如此了。
現在他最大的盼便是真能如何晉所言,等他回去,等著他的是已尋到的消息。否則,他無法想象一個子如何獨自上路行在如此荒曠的道上。即便在留裏特意強調過無須擔憂,他也不可能安心。
萬一有個什麽意外,那便是他的罪責,罪不可恕。
回程幾人放馬而行,趕回的時候,也已是下半夜了。還沒到郡守府,便從城守口中得知前半夜走另條道的人已有消息,結果和他們一樣,也沒見到人。
承平神沮喪無比,裴蕭元知道他的自責,強打起神,正想說明天繼續,聽到城守又說:“還有一事。白天令狐節度使來過。”
“知道什麽事嗎?”
“這個不知。不過,著好像不是公事,來了沒多功夫,郡守便送人出了城,倒像是路過。”
城守口裏的節度使是甘涼都督兼節度使令狐恭,轄製包括威遠在的甘涼之地。裴冀在此多年,始終沒再遷過,但他上麵那個都督節度使的位置,已是換了好幾任了。
此地對整個帝國的重要不言而喻,能坐這個位置的,將來極有可能拜相,自然不是一般之人。
如今這位令狐恭,說起來,也算是裴冀的晚進。
當年裴冀於變中力挽狂瀾名登頂之際,令狐恭還隻是他帳下的一名普通將軍。到了三年前對西蕃的戰事,當朝太子遙領行軍總管坐鎮後方,令狐恭已任行軍副總管,是實際的領戰之人,戰後他便因功升遷來到這裏,做了裴冀的上司。並且不止這樣,在那場戰事裏,因他行軍副總管的份,裴蕭元又了他的麾下,因而雙方可謂頗有淵源。
不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他與前幾任一樣,平常與裴冀絕私下往來,今天怎會忽然到來?
何晉困地了眼裴蕭元。
“走吧,回去便知。”
何晉送承平去了驛館整休,裴蕭元回到郡守府,青頭正守著門,東張西,見了他,拔奔出來相迎。
“郎君你可回來了!郡守你去下他那裏!”
房門大開著。裴蕭元匆匆趕去,見裴冀背對著門而立,微微仰麵,正在著牆上的一副懸像。
正是今早葉留下的那副繪像。
夜風湧,燈火搖曳閃爍,裴冀背影一不。
裴蕭元怕打擾,悄然停在門檻外。忽然聽到裴冀發問:“是沒有找到人嗎?”
他應是,隨即邁步,接著立刻解釋:“侄兒回來是想做些準備,明早再行上路。”
裴冀不再說話。
他沒提白天令狐恭來的事,裴蕭元也就沒問,停在他的畔,一道著麵前的這幅畫。
許久,他聽到裴冀低低地歎息了一聲。
“那天早上來見我,我不過隨口提了一句想日後為我畫個像,竟真就放在了心上,便是決意走了,也先替我作了相。如此尺寸的人像,畫師耗時十天半月已算快了,卻在數日間便畫了出來,還如此到,非草草敷衍。難怪那幾天閉門不出,當時該是如何不眠不休,耗損心力!”
裴蕭元沉默著,負疚如同一座大山,得他心頭沉甸甸的。
“這我又想起當年葉鍾離作那一幅天人京長卷的往事了。他也是閉關不出,全神一氣嗬。當時以我估計,要完永安殿的壁畫,至也需三四個月,他卻月餘便,以致於出來後竟當場嘔。他如今衰壞,也是那時落下的因。絮雨確實是名師出高徒,但想到因為我的一句話,要如此辛苦作畫,我更是心疼了。”
裴蕭元隻覺自己罪大惡極,再次道:“我明日……”
他一眼裴冀,改口,“伯父勿過於擔憂。我準備下,今晚立刻上路,再去尋!找不回來,侄兒不歸!”
裴冀轉臉瞥他一眼。
“倒也不必如此。”
“白天你走後,我過畫,再讀的信,反倒另有所悟。絮雨眼界之寬,心之堅,誌氣之高,莫說普通的子,便是這世上的許多男子,恐怕也難以其項背。伯父在想,也許先前確實是伯父誤會了。提解約,未必全然就是出於誤會,說不定確如當時所言,這一趟過來,原本就沒想著是來嫁你的。”
裴蕭元一頓,再次沉默。
裴冀的目落到他的臉上。
“我知你因此事,必定頗多疚。今早是我一時急,說你說得重了些,小阿史那已經向我解釋過了。罷了,你也不必過於自責。強行要回來,或許當真不是的所願。明天繼續找,若是能夠遇到,不必強留,送回去,或許反而更合的心意。”
“侄兒知曉了,謹遵伯父之命。”
裴蕭元恭謹地應下,頓了一頓,問道:“我聽說今日節度使來過?青頭說伯父要見我。”
裴冀微微頷首:“是。”
“敢問伯父,是為何事?”
他知道裴冀近年曾數次上,以年老為由力請致仕,但是不知何故,每一次的奏章都如泥牛海,一直不得消息。
難道這次終於有了回複,令狐恭來,就是傳達那個坐在紫宮裏的人的旨意?
裴冀著他,目卻漸漸出些複雜之,最後搖了搖頭。
“令狐恭今日來,為的不是伯父,而是為你。”
“朝廷召你金吾衛,告已從京中發送抵達,他親自送了過來。”
裴蕭元微微一怔。
“你沒想到吧?”
“不止是你,便是伯父,也頗為意外。”
白天令狐恭來,雖然沒有久坐,但在言談間,向裴冀了些這告背後的來由。
金吾衛的諸多職責當中,有一項是直接擔負天子儀從護衛,因而可謂是天子近臣中的近臣。當朝的不員乃至宰相尚、地方節度使這樣的大員,早年都曾有過金吾衛的任職經曆,故每年的補員,就了勳貴為自家子弟爭奪仕機會的戰場。
今年也和往年一樣,將從勳貴子弟和下麵上報的立有軍功的人裏擇選出眾人材遞補衛。自三年前起,裴蕭元因有戰功的緣故,名字也在遞補之列,但每一次,他都不在最後的名錄裏。今年負責初擬名單的金吾衛長史是個剛擢拔上去沒多久的,也不知怎的,或許不明,竟將他名字誤錄上冊,遞到了金吾大將軍韓克讓的手裏。韓克讓對下屬過於信任,也沒細,直接就將名冊遞送到了宮中。
因金吾衛屬皇帝的直屬衛率,不像一般的朝廷武,走完一係列的審查流程後由兵部下發告任命,而是金吾衛擬好名錄,司宮臺呈上,由聖人批。名錄送上去後,隔了幾天,司宮臺下發,一也未過,眾人這才發現,裴蕭元的名字赫然在列。
神虎大將軍裴固和他折戟沉沙的最後一戰北淵之戰都早已塵封,淡出了世人的記憶,更如同一個忌,朝堂裏絕不會有人當眾再度提及。此次卻因這個意外一夜之間再度浮出水麵,一時一石激起千層浪。當中反應最大的屬太子舅父,宰相柳策業。據說他立刻私下找司宮臺侍執事袁值去詢問詳,袁值稱聖人恰好在閉關修道,名冊是他隔簾放下的,三日後依舊還在簾外,聖人未曾過,隻發了一句話,金吾衛自定便可。
金吾大將軍韓克讓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謬。但就算名單有錯,已過批這一關,哪怕聖人未曾啟封親,也當視作照準,他何敢擅自再作變。柳策業便要他麵見聖人修正謬誤。罪將之子,何來的資格能金吾衛。不料這個舉卻惹出了另一個人的不滿,那人便是和柳策業同為宰相的王璋。王璋出來反對,稱裴固之罪,聖人當年便已不加追究了,這一點天下皆知,如今其子為國立下戰功,為何不能循製金吾衛?製度既立,便當遵行,否則,豈不寒了軍中無數將士的報國心腸。
這兩人為此爭執不下,吵了幾天後,終於還是驚聖人。聖人閉關依舊沒有麵,隻太子代為置。太子最後裁定,以國製為上,召裴固之子,如今遠在甘涼的七品雲騎尉裴蕭元金吾衛就職。
事雖就此落定,但從頭到尾,可以說是意外裏的大意外,荒唐之程度,也算是本朝開國百餘年來前所未有了。
“無論如何,若論功勞,令侄三年前便當擢升了,這回也是他的應得。聖人萬壽雖還未至,但京城防務想必是要提前布置的,金吾衛在其中更是負重責,老恩師比我想必更清楚。恰好我今日路過,便將告帶了過來,令侄早一日到手,便可早一日,免得耽誤大事。”
白天令狐恭說完這一番話,便起匆匆告辭。
裴冀將告的來曆講了,眉頭鎖。
“這一紙告,雖是無數勳貴子弟的夢寐所求,但於你,我未必就是好事。伯父已經想過了,你若無意回京,伯父便替你尋個由頭,辭了吧!”
他說完,卻見侄兒的視線落定在案頭的燭火上,目沉凝,方才似乎並未全神在聽自己說話。
“蕭元!”他又了一聲,“怎不說話?”
裴蕭元從火上收回了視線,向裴冀。
“能回,為何不回?”
他應話道。
猜你喜歡
-
完結1212 章
法醫嬌寵,撲倒傲嬌王爺
苏青染,21世纪最具潜力的主检法医,因为一次网购,被卖家免费送了次时光之旅:记得好评哦亲~ 不仅如此,这时光之旅还超值赠送了她一口棺材和里面躺着的王爷。 更不幸的是,她是躺在棺材里给那王爷配冥婚的——女人。 苏青染顿时小脚一跺,“退货,我要退货!” “看了本王的身子,还想退货?” 自此,苏青染便被一只腹黑狐狸缠上。 她验尸,他坐堂,她断案,他抓人,绝配! “今晚,王妃的小兜兜好生诱人,让本王看一看这里面是不是一样诱人?” 破案路上,某王爷打着断袖的幌子一言不合就袭胸。 “滚!” 宠文,1V1,黑吃黑,青酒出品,坑品保证。
165.5萬字8 39030 -
完結801 章
穿越后,我被竹馬拖累成了皇后
顧靜瑤很倒霉,遇到車禍穿越,成了武安侯府的四小姐上官靜。 穿越也就算了,穿成個傻子算怎麼回事啊?! 更加倒霉的是,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呢,她已經被自己無良的父母「嫁」 進了淮陽王府,夫君是淮陽王有名的呆兒子。 傻子配獃子,天設地造的一對兒。 新婚第一天,蕭景珩發現,媳婦兒不傻啊! 而上官靜則發現,這個小相公,分明機靈得很啊……
147.3萬字8 10797 -
完結1125 章
神醫毒妃颯爆全京城
前世,葉清幽傾盡所有助夫君上位,庶妹卻和夫君聯手斷送了將軍府上百口人命。 一朝重生,她手握絕世醫術,背靠神秘組織,發誓要讓背叛她的人付出代價。 渣男上門?她直接甩休書退婚!姨娘下毒?她直接讓她自食其果!庶妹蛇蝎心腸?她直接撕下她的臉皮踩在腳下。 她一心復仇,無意間發現七皇子蕭凌寒一直在背后幫自己? 葉清幽:又幫我打臉,又給我權勢,還多次救我出險境,你是不是想接近我,是不是想利用我,是不是想陷害我? 蕭凌寒:不是,你媽吩咐的。 葉清幽:…… 沒想到她還有一個身份成謎的大佬親媽!
151萬字8 16919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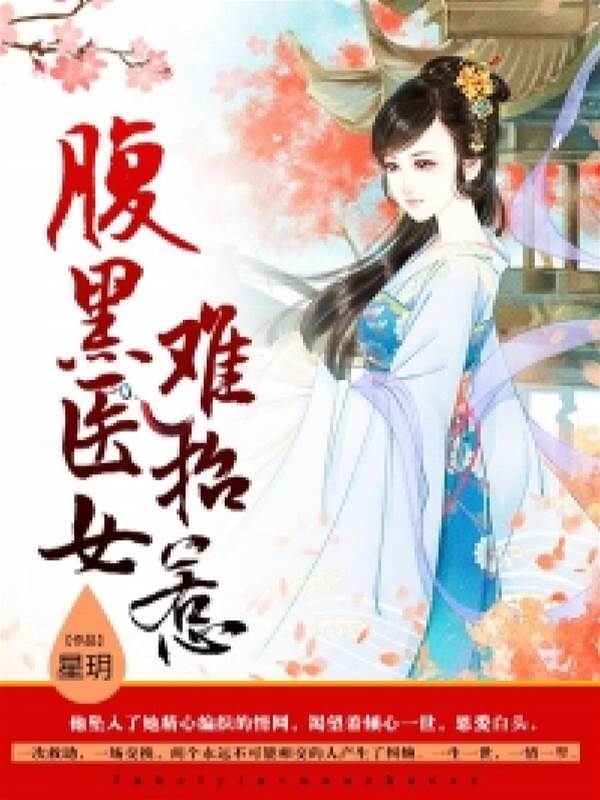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16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