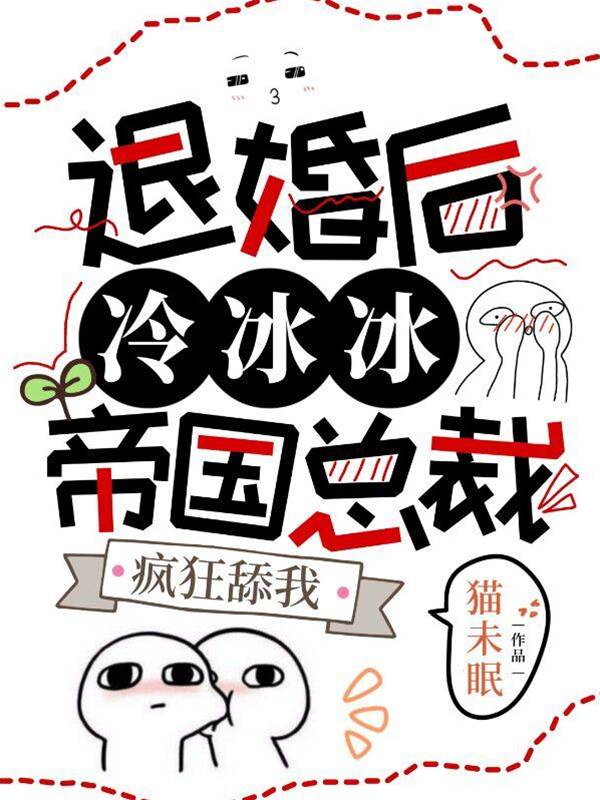《終身妥協》 第9章 晉江獨家首發
趙子真一聽朋友說的話,再看了看賀言郁的臉,心里暗道不好,壞事了。
他推囔那人:“你別瞎說,去去去,過去跟其他人玩牌,別來添。”
趕走那人,趙子真湊到賀言郁邊笑道:“郁哥,你別聽他胡說八道,說……說不定那紅繩就是單只,安棠隨便戴的,當不得真,當不得真哈。”
“戴了兩年半,一直以來都是右手。”
趙子真:“這……”
他著頭皮說:“可能就是戴習慣了。”
這話說得有些底氣不足。
賀言郁沒心思待下去,起走了。
趙子真張了張,想住他,旋即一想,這尊大佛走了,他也不用再提心吊膽。
安棠最近閑著無事,就一直待在別墅,坐在沙發上,上放著一盤致的五彩星星。
這是謝織錦送的生日禮,所以純手工折疊的殼膠小星星,統共有五百二十一顆,代表了的生日。
雖然禮并不貴,可都是滿滿的心意,況且折星星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耐心,所以安棠很喜歡這份禮。
把星星制風鈴,一串一串掛上,這樣待來年春風拂過,星星做的風鈴就可以隨風飄揚。
周嬸在包餛飩,看向坐在沙發上的安棠,遲疑道:“小棠啊,先生這幾天都沒回來,要不你給他打個電話吧。”
吵架冷戰的兩人,總得有一方先低頭退讓。
提起賀言郁,安棠的心極速變壞,這幾天沿著那晚回來的路,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沒有找到扔下的紅繩。
說不定早就被做清潔的環保工人掃走了。
想到這,安棠的心被大手狠狠攥著,開始急促呼吸,趁著手腳冰涼發麻的時候,趕從兜里拿出撕了標簽的藥瓶,倒出幾粒白藥片服下。
待緒平復下來,抱著致的盤子準備上樓,用最平淡的語氣說著最傷人的話:“我現在不想給賀言郁打電話,看到他就惡心。”
“小棠……”周嬸張了張,眼角余瞥見已經回來,此刻站在門口的男人。
他的臉很沉,渾更是冷冰冰的,那雙深邃凜冽的桃花眼就這樣盯著安棠上樓的背影。
顯然并不知道他已經回來了,所以剛剛說的都是發自肺腑的話。
很好。
賀言郁抬腳走上樓,周嬸怕兩人又吵得不可開,走上去替安棠說話:“先生,小棠剛剛不是那個意思,最近心不太好,你也多擔待一些。”
賀言郁沒有說話,來到二樓最里面的房間,擰開,走進去再關上。
安棠正在掛星星制的風鈴,聽到背后傳來靜,扭頭一看,竟是賀言郁。
“你來做什麼?”撇開視線,不去看賀言郁那張臉,腦子清醒的時候,分得清賀言郁是賀言郁,溫淮之是溫淮之,可即便如此,每當凝賀言郁那張臉的時候,還是控不住滿腔的意。
冷冰冰的語氣著實不太好,賀言郁冷笑,現在這況,搞得他倆的關系倒像反過來一樣。
說到底,還是他把縱容得無法無天,失了分寸,才讓沒有看清自己的份。
賀言郁走過去,拽住的手腕,迫使抬頭看自己。
幾天的沉默冷戰,讓他現在開始算總賬。
“看到我惡心?”賀言郁冷笑,“你當初對我死纏爛打的時候怎麼不覺得我惡心?安棠,你這張,可真會騙人!”
以前追著他死纏爛打,任憑他怎麼攆都攆不走,熾熱滾燙的意恨不得告訴所有人他是的摯。
這才跟他在一起多久,就開始不耐煩厭倦了?
呵。
賀言郁用指腹重重的摁了下安棠的,略帶薄繭的碾磨,讓覺得很疼。
“我騙你什麼了?如果不是你扔了我的紅繩,我會這麼生氣嗎?!”得虧安棠剛剛吃了控制緒的藥片,這會才不至于失控。
賀言郁看著那雙瑩瑩杏眸,瞳孔里倒映著他的影子,他以前極了這雙眼睛,從眼里,他可以看到熾熱真摯的與依賴,可現在,他看到討厭痛恨惡心。
紅繩代表姻緣,是幸福的見證。
如果是一對紅繩,那就男戴左,戴右。
賀言郁的腦子里又躥出這兩句話,他口燃燒著熊熊烈火,拽著安棠的手腕用力收,近乎咬牙切齒:“區區一紅繩就值得你這樣?安棠,你該不會背著我還有其他野男人吧!”
聞言,安棠的瞳孔驟然,不敢看賀言郁這張臉,撇開眼道:“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聽不懂還是做賊心虛?”看那副不敢直視自己的模樣,賀言郁一步步近,把到角落。
“我以前就說過,你的世界只能有我。”他擒住安棠的視線,手指勾起的一縷頭發纏著,修長的手指刮過的側臉一直延至耳邊。
指尖涼涼的,讓安棠想起暗地界里骯臟黏膩的毒蛇,吐著猩紅的信子準備將獵徹底咬死。
賀言郁的五指咻地埋安棠的發間,指腹挲的頭皮,迫使仰頭著自己。
只見他淡淡一笑,埋首在耳邊呢喃。
“既然你忘了,那我就好好幫你回憶。”
安棠被賀言郁拽著手腕離開房間,在下樓的時候使勁掙扎,“賀言郁,你給我放開!”
“小棠,先生,你們這是……”
周嬸的話還沒說完,兩人已經走了,看到這形,又止不住嘆氣。
安棠被賀言郁塞進車里,司機得到吩咐,開車先去了一個地方,安棠不知道對方究竟在搞什麼鬼,被造型師押著做造型,同時還換上一條漂亮的黑禮。
禮是肩的,后背近乎鏤空,擺并不長,約莫到大。
這套走的是火辣的設計。
安棠看著鏡中濃妝艷抹的自己,扭頭就想換服卸妝。
賀言郁攬著的腰,一言不合把人帶到酒會上,從他們進來的那刻起,就吸引不人的目。
大家好奇的打量安棠,畢竟他們只知道賀言郁家里有位金雀,寶貝得跟眼珠子似的,也從不把人帶到這種場合,所以眾人紛紛猜測這位火辣的人,肯定不是賀言郁家里那位,估計就是最近在外面新包養的小模。
酒會上雖然不缺青年才俊,但更多的是上了年紀且大腹便便的老總,像賀言郁這樣的人更是麟角。
他的指腹挲安棠的細腰,目掃了眼那些對安棠虎視眈眈的男人。
賀言郁在耳邊溫道:“知道我以前為什麼不帶你參加這種宴會嗎?紙醉金迷的地方,最容易上演權易,既然我養的玩意兒不聽話,那就該好好教訓,吃了苦頭,才知道自己錯了。”
他順勢從服務生的托盤里拿起一杯香檳,轉與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流。
有人的視線往安棠上游走,材窈窕的人穿著火辣的黑禮,瑩白的得仿佛能掐出水,尤其是那雙長,當真是件漂亮的藝品。
他的嚨有些干,笑著沖賀言郁舉了舉手中的酒杯,“賀總,您帶伴參加酒會,家里養的金雀不會吃醋嗎?”
賀言郁用酒杯輕輕和他了,語調懶散:“就是那只金雀。”
這話不輕不重,周圍的人都聽見了,紛紛詫異的看著安棠。
男人們的視線開始變得奇怪,油膩又惡心,而那些來參加酒會的伴,則個個面帶譏諷嘲笑。
原來被藏在漂亮別墅里的珍貴金雀,有一天也會被玩膩,然后淪落到這種地步。
跟們沒什麼區別嘛。
“賀總這是?”有人試探的問。
賀言郁的視線落到安棠上,那雙桃花眼天生多又薄涼。
他似笑非笑道:“只有我不要的玩意兒,才會拿出來資源共。”
安棠怔愣的看著他,腦子瞬間嗡嗡作響。
賀言郁撇開視線,走遠了。
這種行徑無疑告訴其他人,只是一件可以隨便玩弄的玩意兒,紙醉金迷場上的權易再正常不過了。
安棠活了二十四年,除了五歲那年出了點意外被人拐走,都是被寵著長大的。
以前有父母疼,后來的世界里又多了溫淮之,他陪走過暗的經歷,用溫與呵護,告訴哪怕世界再黑暗也是有的。
別人總是言無忌的罵小怪,發起病來只會大吼大像個神經病,可溫淮之會著嘟嘟的臉認真說。
你不是小怪,你是小星星。
當時小,只是呆呆的笑著,心里卻甜滋滋的。
真好,原來小怪也可以變小星星。
安棠抬手了眼角,將自己變得堅強起來,踩著高跟鞋,扭頭想離開酒會。
紙醉金迷場上的權易,那是他們的事,與又有什麼關系。
抬腳想離開,卻被幾個男人攔下。
他們打量商品的眼神讓安棠覺得惡心,其中有個人之前應該喝了不酒,眼下一開口就有酒氣傳來。
他塞了張房卡給安棠,笑得曖昧:“安小姐要是有什麼需求,盡管來找我。”
安棠抬眸,眼神不經意間看到不遠和別人談笑風生的賀言郁,他的視線跟撞在一起。
賀言郁瘋。
其實,也瘋。
就看誰先按捺不住,失了控。
輕輕了下頭發,舉手投足帶著嫵,指尖夾著房卡,似笑非笑:“知道了。”
安棠轉離開,沒注意到賀言郁的臉已經變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59 章

慕川向晚
千年難得一遇的寫作廢柴向晚,因為書撲成了狗,被逼相親。 “媽,不是身高一米九腹肌十六塊住八十八層別墅從八百米大床上醒來的國家級高富帥,一律不要。” “……你是準備嫁蜈蚣?” 后來向晚終于如愿以償。 他被國家級高富帥找上門來了,撲街的書也突然爆火—— 有人按她書中情節,一比一復制了一樁命案。 而她與國家級高富帥第一次碰撞,就把人家給夾傷了…… …… 愛情、親情、倫理、懸疑、你要的這里都有,色香味俱全。 【本文狂撒狗血,太過較真的勿來。】
178.1萬字8.09 16389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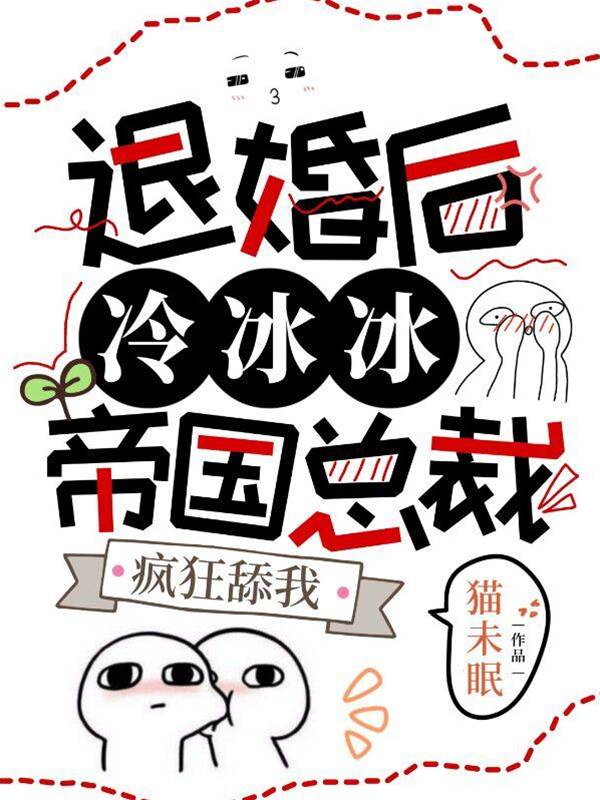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5631 -
完結132 章

小妻很乖,腹黑九爺輕點撩
【年齡差 甜虐交織 雙向奔赴 HE】【堅韌嬌軟小白兔VS痞野腹黑大灰狼】沈阮阮是嬌貴的乖乖女,她有個竹馬叫蔣清洋。蔣清洋從小就喜歡她,終於等到她上大學,但他卻被家裏送出了國,於是他撥通電話,說出此生最後悔的一句話:“舅舅,我求你一件事。幫我看顧好阮阮,別讓別人把她拐了去。”傅九爺嘴皮輕扯,懶散罵道:“瞧你這點出息。”蔣清洋知道小舅肯罵他就說明同意了,於是他鬆了口氣,隻是這口氣卻在他回國時泄了,他第一次對傅玖失態:“舅舅你怎麽能這樣呢!你不是答應我不讓別人拐她嗎?!”“不是別人啊。”傅玖嬌軟在懷,並沒有動怒,反而氣死人不償命道,“我是你舅舅。”閱讀指南:1、背景半架空,務究(感恩感恩)2、大甜小虐3、HE,HE,HE,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嘿嘿(o﹃o )
22.8萬字8.18 87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