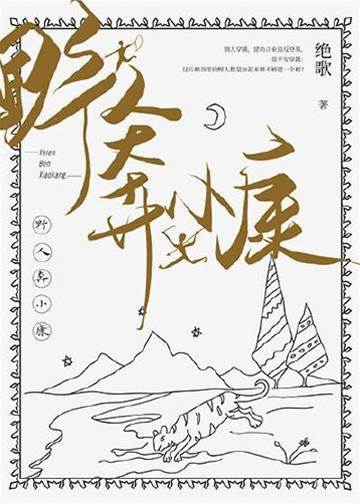《女配是大佬[快穿]》 第201章 為往圣繼絕學4
傅岑原以為,他孫去湘月書院走一遭,夫子的事就能夠順利解決。
結果衡玉回來后,把和容謙言說的話,又重復了一遍。
“我是饞他當我的老師嗎?不,我是饞他能讓我名正言順進湘月書院玩。”
傅岑瞪,“什麼饞?你堂堂鎮國公世,怎麼說話的?”
“還有,丹青先生的名聲我是聽說過的,他出世家大族,本是同輩中最出眾之人,可惜一直不太好,每次去參加科舉就要折騰掉半條命,考秋闈出來,這條命險些熬不過去。為了命著想便沒有繼續往下考,這才止步于舉人功名。”
“連這樣的名士你都看不上,你難道真要按照之前說的高標準去找老師?”
衡玉攤手,非和祖父倔上了,“祖父,我剛剛已經把理由告訴你了,他不是饞我的腦袋瓜子,他如果收我為徒,那肯定是饞我那一堆書。這兩者之間有著本質區別。”
傅岑沒明白,“有什麼本質區別,他收你為徒后,難道會不盡心盡力教導你嗎?”
都收徒了還敢不好好教導,當他鎮國公府是擺設嗎!
“就是有區別啊,祖父你不懂我。”
一旁的肖嬤嬤聽了半天,好像有些著衡玉的想法了。
衡玉年紀雖小,難道不知道所提出的要求,當世幾乎無一人能達到嗎?
知道。
但偏偏還要堅持。
——大概就是想折騰,不想那麼早就開始自己苦的讀書學習生涯吧。
當覺得折騰得夠了,才會安安心心開始學習。
肖嬤嬤笑瞇瞇盯著,那雙被歲月侵蝕依舊溫和慈祥的眼睛,帶著看一切的彩。
衡玉對上肖嬤嬤的視線,忍不住抬手蹭了蹭鼻尖。
好吧承認,就是想折騰了。
這一世這麼好的份,錦玉食信手來,需要承擔的責任又。
人生苦短,總要給自己找些樂子,也要給祖父多找些樂子。
自從父母與城池共存亡后,鎮國公府就日漸冷清。這麼大的府邸,還是鬧些折騰些為好。
可憐兮兮的傅岑完全沒注意到衡玉和肖嬤嬤的眼神流。
他深深吸了口氣,“這樣吧,看不上舉人當你的老師是吧,這江南一帶員極多,隨手一抓,最起碼都是三甲同進士出。鎮國公府每月都會收到不帖子,我有空就帶你去赴宴,總能給你找到合適的老師。”
攤上這麼個孫,他沒辦法了。
為今之計,先廣撒網,再重點捕撈。
為武將的倔脾氣一上來,傅岑他還真就不信了,江南員這麼多,沒有一款能把傅衡玉這小崽子折服的!
衡玉:“……?祖父,倒也不必如此。”
傅岑冷哂,“不是鐵了心要找老師嗎?小兔崽子,給你祖父我老實點,難道你打算非暴力不合作?”
“你舍得打我?”
傅岑板著長臉,“我是武將出,死人堆里爬過來的。打你一個不聽話的小崽子,我還能不舍得了?”
衡玉撇,不信祖父這話,卻還是很給面子的跑到肖嬤嬤邊,拽著肖嬤嬤的袖子,“嬤嬤,你看看我祖父,年紀這麼大了,連修養四個字都沒學會。”
“傅衡玉——”
“你給我過來——”
衡玉快步往廂房外溜,邊走邊喊:“春秋,天已晚,我們回院子歇息吧。”
——
不過,這件事就這麼定下來了。
衡玉在家待著無聊,對于參加宴會一事還是有些興致的。
素來不喜際,整日待在府里練武寫兵書的鎮國公傅岑,突然對參加宴會發強烈熱。
他命管家將近段時間的帖子都整理好送過來,展開一一研究。
說是要廣撒網,再重點捕撈,結果傅岑看著那些拜帖,自己就先不滿上了。
“我雖遠離京城,這些年可從來沒有遠離過場,這人做了那麼多齷齪之事,居然好意思給鎮國公府送上拜帖,不怕我去攪和了他的生辰禮?”
“還有這個,諂邪之輩!”
“荒謬,陛下怎麼把這人放到五品實缺上了!”
肖嬤嬤聽著聽著,似乎知道了玉兒的挑剔都是傳自誰。
說:“現在這麼挑剔,當初幫玉兒選啟蒙夫子時,沒見你像現在這麼謹慎!”
傅岑把拜帖全部扔回桌面,“我在場消息靈通,但文武之間爭斗嚴重,對這些文人的事那是一點兒也不了解。況且當初幫駒兒挑啟蒙夫子,不也就是隨便挑挑的,哪里像玉兒一樣這麼麻煩。”
他口中的“駒兒”,就是衡玉的父親傅駒。
衡玉正邁著過來給傅岑請安,一進門就聽到這句話。
原本說要找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師,只是衡玉的笑言。現在還真就和祖父杠上了。
肖嬤嬤瞥見走進來的衡玉,連忙道:“國公爺,你說兩句氣話。”
傅岑也瞧見衡玉了,不自在咳了咳,“我也沒說錯。”
衡玉快步走到祖父面前,目往拜帖上掃幾眼,“祖父,這些都不行啊。”
“你都沒看就知道不行?”
“這能給你遞拜帖的,也就江南一帶的員吧。除了江南總督幾人,還有多個的職在正三品以上的?而江南總督他們份高,不會隨便給你遞拜帖,以免有史彈劾你們結黨營私。所以,我覺得這些給你遞拜帖的都不太行。”
傅岑:“???”
連結黨營私都懂了,他這孫平常都在干些什麼?
衡玉一嘆,“果然,只能找我親親皇祖母和皇帝舅舅幫忙了。”
這一副嫌棄他辦事不利的模樣,是在挑釁他嗎?
他傅岑好歹是朝堂超品國公爺,居然被自己七歲的孫嫌棄了!
看著傅岑那郁悶憋氣的模樣,衡玉這才樂了。
——
帝都了九月,天氣漸漸轉涼。
青山灼灼,綠水緩緩,晚風慢慢。
水之畔,來往的行人和客船極多。
僻靜一些的角落,此時有兩位老者并肩走在水之畔。
走在前列的,是個穿青布的老者,他的發里摻雜有些許白發,眼角也帶著歲月的痕跡,但一氣度淵雅,整個人帶著一種通深淵的意境。
令人見之忘俗。
他淡笑道:“你不該過來給我送行。”
另一個老者穿著暗紫錦袍,氣質沒有他這麼出眾。
聽到陸欽的話,紫老者微微搖頭嘆息,“你被致仕,此去江南,也不知是否還有再見之期。”
說到這里,紫老者話音微頓。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他這好友今年剛過六十大壽,又不是很好,此一去……誰能說得上來會出現什麼變故呢。
紫老者將剛剛的話補完,“他們不敢來,擔心政見之爭會影響仕途,我終日在翰林院里編修書籍不問朝政,仕途早就走到了盡頭,沒什麼不敢的。”
陸欽搖頭微笑,“不是他們不敢,是我不愿他們前來送行。”
紫老者長嘆,“你啊你——”
“江南乃文教興盛之地,你孑然一,若是在那里待得無聊,不若進書院當個教書匠。”
“一介閣老進書院當教書匠,我想沒有哪個書院會不樂意。”
陸欽有些心,但想了想,還是輕嘆一聲,“罷了。”
“為何?”紫老者有些急了,“那些人把你走朝堂還不夠嗎?你當個教書匠教個學生,有誰敢反對。陛下一直念著你,他若是知道那些人你至此,定然也會生氣的。”
水之畔的晚風有些喧囂,陸欽寬大的袖袍翻飛,整個人有種羽化登仙之。
他微嘆口氣,“和他們無關,是我自己怕把良才玉教壞。子慎,我的思想和抱負都太過沉重超前,朝堂容不下我這種思想抱負。”
說這話時,他語氣平和,沒有任何的激憤與惱怒。
字子慎的翰林學士沈唯,卻自心底升起一不平和悲憤來。
三十多年前,那個在金鑾殿上對答自如、意氣風發的狀元郎,已經被一次次的失和貶謫詰難,打磨如今這般華斂、氣度溫和的模樣。
這朝堂!
這世道!
陸欽又一笑,寬好友,“現在的我有些累了,回到老家先好好休息一段時日,到時再另做打算吧。”
他抬眸眺碼頭方向,“時間已不早,我該上船了,子慎你也該打道回府。”
“好,你定要好好保重。”
“我知曉了,不必擔憂我。”
怎麼不擔憂呢?
他這好友孑然一,這一次回老家,只有兩名老仆和十幾箱書籍相伴,此外再無他。
朝堂上那些政敵,一次次攻擊他的政見,一次次攻擊他所做下的決策,唯獨無法攻擊他的為人。
這是一位,連敵對者都不得不稱頌人品的君子。
猜你喜歡
-
完結386 章

毒舌醫女穿越記
在古代,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是以,欠下賭債的父親要將自己賣了換取錢財,沈淩兒別無他法,隻能一死了之。誰知死人竟有復活日,沈寶善大喜:「既然沒死,趕緊嫁人去!」然而,這柔弱的身體中,已換了個接受現代教育長大的魂魄。什麼三從四德,愚孝夫綱,統統靠邊!憑著一手精湛醫術,金手指一開,沈淩兒脫胎換骨,在古代混得風生水起。誰知,穿越之初撿來的那個男人,竟越看越不簡單。毒舌女對戰腹黑男,誰勝誰敗,尚未可知吶。
101.3萬字8 22734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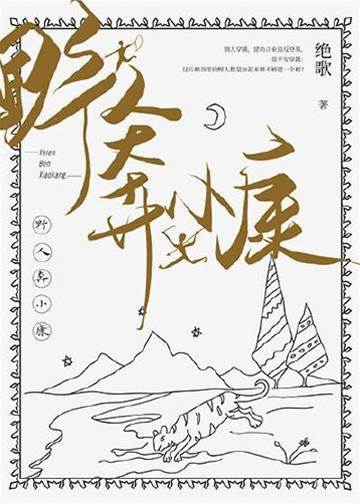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79 -
完結626 章

我,開局輔佐嬴政,成為六國公敵
張赫穿越大秦,獲得最強輔助系統,只要輔助嬴政,便能獲得十連抽。于是張赫踏上了出使六國的道路,咆哮六國朝堂,呵斥韓王,劍指趙王,忽悠楚王,挑撥齊王,設計燕王,陽謀魏王。在張赫的配合下,大秦的鐵騎踏破六國,一統中原。諸子百家痛恨的不是嬴政,六國貴族痛恨的不是嬴政,荊軻刺殺的也不是嬴政。嬴政:“張卿果然是忠誠,一己擔下了所有。”張赫拿出了地球儀:“大王請看……”
122.8萬字8 8511 -
完結293 章
這個將軍是我的
醫學博士洛久雲被坑爹金手指強制綁定,不得不靠占她名義上夫君的便宜來續命。 偷偷給他做個飯,狗狗祟祟盯著人家的手。 魏巡風:這個姦細一定是想放鬆我的警惕! 洛久云:悄悄拉過男人修長的手指,反覆觀看。 看著他矜貴又懵懂容顏,想,他可真好看。 面對時不時被佔便宜的洛久雲,某日魏大佬終於......後來,魏巡風:這女人,真香!
51.4萬字8 92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