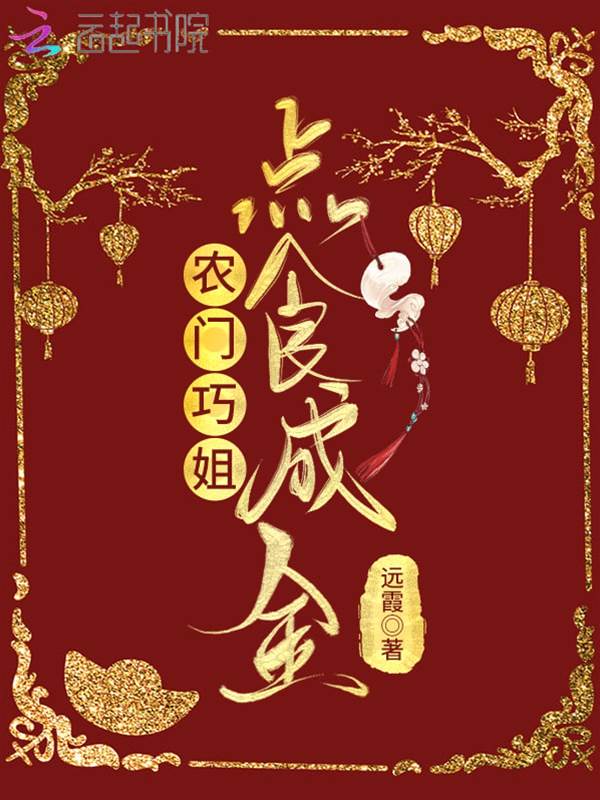《側妃上位記》 第69章 有礙(補更)
東宮,花園中。
軍站在假山前,徐盛如今悲傷過度,傅昀帶著人率先走近道。
道通地下,長長的階梯而下,最終連通一個房間,房間門是敞開,里面擺設皆為貴。
一柄黃梨木椅悠閑地擺在一旁,而另一側的件,卻和這方產生割裂。
一排排刀橫掛在木架上。
中間擺著一張榻,上方躺著一位人,輕淺闔眸,臉紅潤,發髻上帶著五金釵,赤紅的玉珠垂落,似只人臥榻小憩般。
進來的人,皆是呼吸稍滯。
躺在榻上的子,眾人皆認識,圣上盛寵多年的珍貴妃娘娘。
誰都不能否人,珍貴妃容貌即使在長安城也是堪絕,不點而赤,如凝脂,即使如今年近四十,卻不過比時多了分婦人的風。
有些人在這一刻,竟忽然有些理解太子為何要這般病態。
這般景,誰舍得逝去?
傅昀不過愣了一瞬,待視線到一旁的刀時,他眸子倏地涌上一子寒意。
他對著進來的宮人,冷聲說:
“帶著娘娘,去見皇上。”
珍貴妃的尸朝圣上面前一擺,方才還淡定理徐家子一事的圣上頓時怒火攻心,手中的杯盞狠狠砸在傅巰頭上,冷喝:“畜生!”
疼不在自己上時,都可淡定漠然,還覺旁人小題大做。
但事一旦發生在自己上,才會覺得作惡之人有多可惡。
圣上如今就是這副模樣,他看向傅巰的視線中,生平第一次添了分厭惡:“朕這麼多年的教導,皆讓你學到何了?”
“竟多了這種齷齪的心思!”
“連庶母都敢,你還有什麼不敢的!”
傅巰額頭稍偏,許久,他才堪堪正過頭,抬手了下額頭,修長的手指上一片殷紅。
傅巰輕飄飄地掃過那抹殷紅一眼,心中無所謂地輕嗤一聲。
圣上那杯盞,碎在他額頭上,直接出了跡。
可這時,圣上滿心皆是氣憤,哪還有方才的一分心疼。
好半晌,圣上才止住怒氣,道:
“將太子大理寺,待審!”
這決斷,在場的許多人不著痕跡地擰了擰眉。
大理寺?
誰不知大理寺寺卿沈青秋,是太子傅巰的人。
進了大理寺,不過是將太子傅巰從自己的地盤換到另一地盤上罷了。
傅昀心中一抹涼意閃過,他沉著臉上前一步:
“父皇——”
不待他再說,圣上就冷眼掃向他:
“朕已有決斷,此事不必再議!”
傅昀堪堪噤聲,抬頭看了一眼圣上,待看清他眼中的那抹怒意時,才退了一步。
他賭。
賭憑借圣上對珍貴妃娘娘的在意,不會輕易放過傅巰。
若不然……
傅昀垂頭,眸子中劃過一冰冷。
宮中靜甚大,有些路子的,早就派人打探消息。
賢王府。
莊宜穗躺在床榻上,清麗的臉上泛著一抹蒼白,板著臉,多了一分生和冷寒。
和往日那個端莊溫和的模樣,大相徑庭。
氿雅端著藥碗,走進來,覺到屋中的氣氛,了頭,待走近,才低頭小聲:“王妃,該喝藥了。”
莊宜穗睜開眼,盯著那碗中的藥,一子苦傳出,狠狠攥錦被,下一刻,倏地揮落藥碗。
“砰——”
滾熱的藥灑了氿雅一,氿雅臉頓時慘白,驚呼一聲,下一刻,待及王妃視線,立即噤聲,砰得跪了下來。
藥碗的碎片,落了一地。
地,忍著眼淚,說:“王妃,你別生氣,別氣壞了子。”
似聽到了什麼笑話般,莊宜穗輕嗤了聲:
“子?”
突兀地,兩行清淚就從眼角流下,發了瘋般,將靠枕什麼皆砸下床:“如今本妃還能顧及什麼子?”
崩潰地質問:“本妃這還能差到哪里去!”
氿雅被這副模樣嚇到,卻不敢,瑟瑟發抖地爬近床,將莊宜穗抱住,哭著說:“王妃!王妃!您別沖啊!”
“太醫說,太醫說……也許有轉機的!”
那日,莊宜穗落水,如今二月的天甚寒,水中冰冷,誰也不知落水多久。
只知曉,近乎去了半條命。
昨日,太醫來診脈,卻說了一句話:
“娘娘這次落水,寒過于嚴重,傷了本,日后恐……與子嗣有礙。”
太醫說得遲疑,而聽的人,卻仿佛愣住了一般。
莊宜穗直接傻掉,仿佛聽錯了一般,讓太醫又給重復了好幾遍,才不敢相信地回神。
當時險些瘋掉,只一理智尚存,讓冷聲封了太醫的口。
當時,的眸甚是駭人,見慣了后宮晦的太醫都生了一分寒意,竟真的點頭應了下來。
過了不知多久,莊宜穗才重拾理智,推開氿雅,斂著眸,埋聲說:“可查到那日害本妃是何人了?”
氿雅啞聲,極為緩慢地搖了搖頭。
那時宮中因側妃險些小產一片,誰也顧不上王妃,們在宮中本就沒有基,待主子清醒后,再想去查,本查無所查。
莊宜穗抹了一把眼淚,冷笑著說:
“哪還需要查。”
氿雅不解抬頭。
這次打擊,似莊宜穗清醒過來一般,眸中生了恨。
能在宮中有人脈,偏生還對了手腳,除了周韞,本不做旁想。
待許久后,深呼吸了一口氣,冷沉地說:
“重新端一碗藥來。”
氿雅點頭,就要退出去,倏地莊宜穗住:
“仔細著些,若本妃的事傳了出去……”
話音很輕,后面的話也未說完,可未盡之言,足以讓人猜到。
沒等氿雅出去,鳩芳就端著藥碗走了進來,在外間聽見靜,就立刻讓人重新端了碗藥過來。
一步步,沉穩地將藥端給莊宜穗,稍有些遲疑地低了低頭。
莊宜穗余瞥見神,冷淡地問:
“何事?說吧。”
鳩芳了手帕,才堪堪出聲:
“王妃,這事可要通知府上?”
幾乎話音剛落,莊宜穗就倏地甩了一掌,鳩芳疼得生生偏過頭去,莊宜穗用勁之大,直接偏移了半個子。
屋中稍寂靜,氿雅埋著頭,本不知說些什麼。
就聽莊宜穗著涼意的一句話:
“不要再讓本妃聽見這句話。”
子嗣有礙一事若傳回莊府,不用多想,都知曉,祖父和父親會做些什麼。
莊府大房如今只有一個嫡不錯。
可卻庶甚多,二房也有嫡,對于莊府來說,皆是一家人,利益皆相同。
必會安排送人府。
可對莊宜穗來說,這般一來,一旦進府的莊府子誕下子嗣,莊府的助力必定傾斜。
即使,抱了旁人子嗣又如何?
養母總歸是不如生母的,再如何,都有一層隔閡。
除非……去母留子。
可大房唯二的庶皆是單姨娘所生,單姨娘深得父親寵,兩個庶妹和也不是一條心,一旦進府,那只會是給自己添堵,而不是添助。
是以,子嗣有礙一事,能瞞多久,就要瞞多久。
再說,只是子嗣有礙,又未必一定不能生!
鳩芳本就是夫人派來伺候莊宜穗,對莊府的忠心要比莊宜穗要強,當即抬頭,咬牙遲疑:“可是——”
“本妃讓你閉!”
莊宜穗倏地打斷,眸子中的寒意,鳩芳背后生了一冷汗。
生生地噤了聲。
莊宜穗盯著,一字一句地說:
“若是府中知曉這事,你,就不必留在本妃邊伺候了。”
留在王府,會回到莊府,對鳩芳本無甚差別。
若鳩芳選,恐怕更愿意回到莊府去。
可偏生莊宜穗下一句話,鳩芳生生打斷了念想:“你在莊府的家人,也皆不必伺候了。”
鳩芳一家子皆是莊府的家生子,死契在莊府中,“不必伺候了”幾個字,莊宜穗說得輕松,可對鳩芳一家子來說,不亞于滅頂之災。
鳩芳垂頭,手心說:“奴婢記住了。”
莊宜穗喝著藥,不愿再看見:“退下吧。”
鳩芳躬,退了出去。
莊宜穗盯著的背影,眸子中似有涼意閃過,氿雅不小心瞥見,頓時又埋下頭。
可莊宜穗卻是又看向,不不慢地說:
“本妃邊留著的人,必須是對本妃忠心的。”
氿雅立刻跪地:“奴婢對主子素來忠心耿耿!”
莊宜穗偏開頭,手輕上小腹,闔眸,輕聲卻著一涼意:“本妃不想再看見。”
?是誰?
氿雅想到主子剛剛看向鳩芳的視線,心中陡然閃過一抹寒意,死死低頭,說:“奴婢知曉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620 章

神醫娘親她又美又颯
九千歲獨孤鶩因疾被迫娶退婚女鳳白泠,滿朝轟動。 皇子們紛紛前來「恭賀」 : 鳳白泠雖貌丑無能又家道中落,可她不懼你克妻不舉之名,還順帶讓你當了便宜爹, 可喜可賀。 獨孤鶩想想無才無貌無德的某女,冷冷一句:一年之後,必休妻。 一年後,獨孤鶩包下天下最大的酒樓,呼朋喚友,準備和離。 哪知酒樓老闆直接免費三天,說是要歡慶離婚, 正和各路豪強稱兄道弟的第一美女打了個酒嗝:「你們以為我圖他的身子,我是饞他的帝王氣運」 九千歲被休后, 第一月,滿城疫病橫行,醫佛現世,竟是鳳白泠。 第二月, 全國飢荒遍地,首富賑災,又是鳳白泠。 第三月,九朝聯軍圍城,萬獸禦敵,還是鳳白泠。 第某個月,九千歲追妻踏遍九州八荒:祖宗,求入贅。 兩小萌神齊聲:父王,你得排號!
284.6萬字8.18 32494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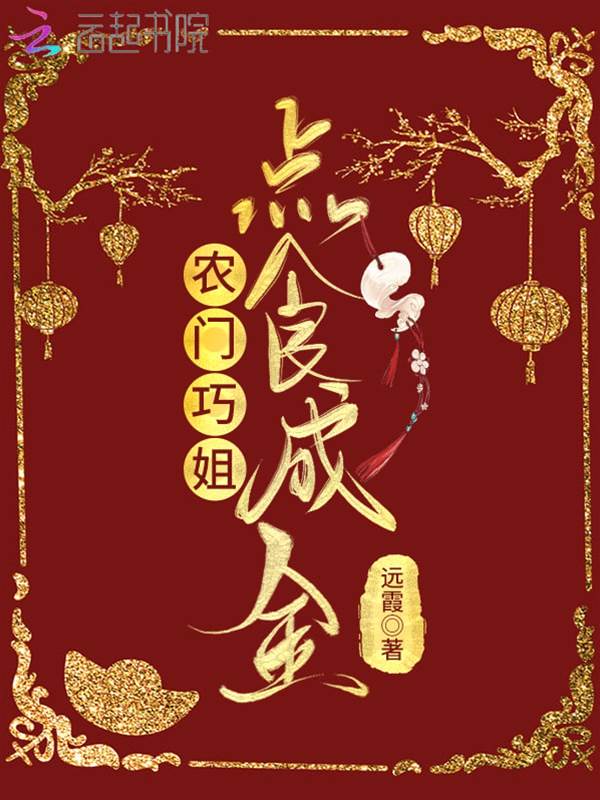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4370 -
完結506 章

爺快跪下,夫人又來退親了
中醫世家的天才女醫生一朝穿越,成了左相府最不受寵的庶女。 她小娘早逝,嫡母苛待,受盡長姐欺負不說,還要和下人丫鬟同吃同住。 路只有一條,晏梨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鬥嫡母踹長姐,只是這個便宜未婚夫卻怎麼甩都甩不掉。 “你不是說我的臉每一處長得都讓你倒胃口?” 某人雲淡風輕,「胃口是會變的」。 “ ”我臉皮比城牆還厚?” 某人面不改色,「其實我說的是我自己,你若不信,不如親自量量? “ ”寧願娶條狗也不娶我?” 某人再也繃不住,將晏梨壓在牆上,湊近她,“當時有眼不識娘子,別記仇了行不行? 晏梨笑著眯眼,一腳踢過去。 抱歉,得罪過她的人,都拿小本記著呢,有仇必報!
90.4萬字8 291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