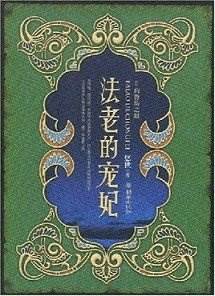《穿成男主的惡毒小媽》 第27章
衛諺心里不大痛快。
他這人一向沒什麼同心的, 但自從知道冤了沈遲意,心里便見的有些愧意,他人在自己院子, 一直心著給沈遲意解蠱的事兒,好容易有了線索, 他又聽說沈遲意醒了,便急忙趕了過來。
本來這事兒, 他派個下人來也使得, 他也不知自己怎麼得了, 就這麼上趕著過來, 沒想到在這里撞見老二,老二一手端著藥碗,一手持著絹子,眉眼溫地給著角,而是沈遲意雖然橫起手臂抗拒,但眼底卻有些用, 瞧見這一幕,他莫名就不痛快起來。
平常他稍微靠的近些,便一口一個小娘兒子的, 生怕旁人不知道做了他的便宜庶母似的, 怎麼一到老二這里,就百無忌了?難道老二就不算兒子了?
更讓他不悅的是, 沈遲意見他過來,本來還算能看的臉,徹底冷了下來,甚至冷哼了聲,轉過頭去, 一副看他一眼就被玷辱的表。
衛諺長這麼大,就沒被人無視到這個地步,心中不由生出一悶氣,重重往前了一步。
衛詢微怔,似乎沒想到衛諺竟也在這時候過來。
他見自家大哥表不善地走了過來,微微移步,不著痕跡地將沈遲意擋住,很快笑道:“這一路走的順當,我帶著人早到了一日,想到這次能安然回來,多虧了姐姐提醒,又聽聞姐姐中奇毒,我心里擔憂,所以便匆忙趕來探姐姐了。”
衛詢一未來得及下的鶴羽氅,顯得頗為磊落拔,回答的也是落落大方,半點瞧不出方才做了翻窗爬墻的舉。
衛諺對著親弟也沒個好臉,冷哼了聲:“你姐姐在縣主府里,這里有你哪門子的姐姐?”
衛詢手挲著下頷,看了沈遲意一眼,含笑道:“大哥還不知道吧?我和姐姐認識的比你早上許多,從認識那時候起,我就已經開始姐姐了,現在已經習慣,怎麼都改不了口,大哥不會介意吧?”
這兄弟倆說來也怪誕得很,他們雖然是相互信任,在大事上也絕不會拖彼此后,但在平時相上,當真算不得和睦,也完全沒有親近兄弟該有的樣子,也難怪府里府外都覺著兩人不睦,瑞王更是想用衛詢制衡長子。
他沖沈遲意眨了眨眼:“對吧,姐姐?”
沈遲意見著衛諺,徹底連說話的都沒有了,更不想摻和兄弟倆莫名其妙的較勁,聞言含糊地‘嗯’了聲。
再沒什麼比這話更拱火的了,衛諺瞇了瞇眼:“你既回來了,就先把手頭的事兒理干凈,別忙著往人房里鉆。”他流出嘲諷:“更何況這人,還是你我的庶母。”
衛諺說完這話,自己心頭的窒悶又加重了點,委實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衛詢面一滯,低頭抿了抿,沉默片刻才道:“大哥又是為何而來?”
衛諺淡淡道:“我有正事尋。”他又哼了聲,轉向周釗:“西戎之事耽擱不得,送老二回去。”
衛詢又瞧了沈遲意一眼,叮囑道:“姐姐有什麼事,立刻遣人去喊我一聲。”他說完才沖衛諺點了點頭,轉出了房門。
衛諺看向背對著自己的沈遲意,忍了又忍,還是沒忍住哼了聲:“你什麼時候多了個弟弟?”
沈遲意本不搭理他,信手玩弄床邊的流蘇,就是不肯瞧他一眼。
衛諺想到衛詢方才離那樣近,忍不住向前了幾步,徑直走到床邊,穩穩立在衛詢才站的位置上。
沈遲意這才有了反應,一拂袖便把藥碗摔到他腳邊,冷冷道:“離我遠點!”
不過現在全乏力,自以為很有氣勢的一句話,也說的有氣無力,聲調綿綿的,帶著低低的喑啞,就如同撒一般,讓更是氣不打一來。
衛諺似乎呆了呆,這些日子沈遲意要麼昏睡不醒,醒來也是迷迷瞪瞪的,還沒見他發這麼大脾氣。他治人一向有方,這些日子費心費力幫找尋解藥,也是為那日之事做些彌補,沒想到沈遲意卻不領。
他生出一種挫敗,心中頗是郁郁,忍不住又靠近了一步,皺眉打量:“你才轉醒,那麼大肝火做什麼?”他輕哼了聲:“又不是沒離得這麼近過。”
冷聲道:“怎麼?世子上回耍威風還沒耍夠?這回是要過來拔刀砍殺了我?”
衛諺被譏諷的微微擰眉,半晌才道:“上回遇刺之事,是我冤了你,你…”他卡了會兒,才道出一句:“我信你了,你確實幫了我和老二大忙。”
老天作證,他長這麼大就沒對誰說過話,當年瑞王揍他,子都斷了兩,他也是沒低一下頭,所以最后一句說的他臊得慌,耳都有些泛紅。
冷笑一聲:“那也是幸好二王子今日平安歸來,不然等著我的,怕是世子的一碗毒酒了。”
衛諺咕噥了聲:“我從不用毒酒…”
這話說的沈遲意臉又是一黑,衛諺這輩子沒跟人相的經驗,又張了張:“不會的…”他遲疑道:“當時是我一時急,事后知道此事與你無關,我豈會傷你?”
沈遲意又冷哼一聲,不說話了。
衛諺只得拋出一個無法拒絕的話題:“我來是想告訴你,抓到李鈺了。”
沈遲意神一,果然肅了神:“然后呢?”
衛諺沉道:“我正命人上刑,令他出解藥。”
沈遲意想到沈家軍械案,心頭一:“我想單獨見見他。”李鈺是樓的人,對沈家軍械案的應該知道不,實在想不明白,父親那樣忠于朝廷的人,為何會做出私藏軍械之事呢?只怕是有人在背后蓄意陷害,那陷害之人又是誰?
衛諺皺了下眉,似有些不樂:“你見他做什麼?”
沈遲意抿了抿:“李鈺畢竟曾經和我家關系親厚,我有些私事要問他。”
衛諺本想拒絕,瞧一臉冷意,微哼了聲:“給你半個時辰。”
沈遲意點頭應了,又一瞥衛諺:“夜深了,我這人冷自私,蛇蝎心腸,世子還是盡早回去吧,免得被我趁著夜深毒害了。”
“這時候該懼的是你不是我吧?”衛諺輕嗤:“你倒是跟我說說,這般深夜,你打算怎麼毒害我?”
沈遲意面一沉,又不說話了。
衛諺討了個沒趣,又哼了聲,轉走了。
……
衛諺雖說煩人,不過辦事倒頗為老道,他沒把李鈺關押到軍營里頭,而是關押到別院的地牢里,畢竟李鈺也是朝廷命,若死在他軍營里,不得要和朝廷一番扯皮,只有死在別,他才好把事推給山賊惡匪。
沈遲意經過一晚上的休整,上的力氣已經恢復了許多,裹上厚厚的大氅和兜帽,掩好面容,悄悄跟隨衛諺去了別院。
這別院甚至沒被記在衛諺名下,明面上是一個富商用來金屋藏的地方,往進走了之后才發現有乾坤,衛諺帶著進了一空屋:“等會我讓人把李鈺押出來,你們最好別談的太久。”
他不大放心地補了句:“若有什麼事,及時喊上一聲,我就在不遠。”
沈遲意打量屋環境,聞言輕輕頷首。
李鈺直接是被囚車押上來的,雙手被千金鎖鎖住,腳上也帶了厚重的鐐銬,上臉上跡斑斑,四肢也微微扭曲,似乎已經被人折斷了。
衛諺先問周釗了句:“解藥的事兒審問的如何?”
周釗還沒作答,李鈺仰頭哈哈大笑:“世子別白費功夫為著人求藥了,我給下蠱毒之后,本就沒想過為解毒,如何會留下解藥?我連解藥是什麼都不知道!”
周釗面有愧,衛諺面一冷,沈遲意心下微微一沉。
衛諺這時卻遞來一個安的眼神,好像有了后手似的,也沒再糾纏解藥之事。
他淡聲道:“你想問什麼便問吧。”說完便帶著周釗退了出去,自己在距離大門一丈來遠的地方看守著。
要不是李鈺手腳都被束縛,沈遲意還真不敢跟他待在一個屋里,整理了一下思緒,很快問道:“關于沈家軍械案的,你知道多?”
李鈺似乎毫不意外會問這個問題,冷嗤:“我憑什麼告訴你?”
沈遲意眼里掠過一道寒:“你自己不要命倒還罷了,可難道你親眷的命,你也不打算顧及了?”
作為一個國旗下長大的五好青年,李鈺哪怕抵死不說…只怕也不能對無辜的李氏族人做些什麼,不過在李鈺經酷刑之后,這點威脅足夠讓他信念崩塌。
李鈺臉果然變了變,惡狠狠地盯著。
沈遲意怡然無懼地和他對視,兩人互視片刻,李鈺深深地垂下頭:“我確實知道一些…”他閉了閉眼:“你湊近些,我告訴你。”
沈遲意腳下不:“就在這里說。”
李鈺臉又幽暗了幾分:“沈家…”
他才吐出兩個字,眼里劃過一冷,沈遲意心頭生出一危險的預,還未來得及呼救,只來得及踹翻腳邊的一個凳子,就見牢車的門居然自己打開了!
李鈺明明重傷,上也套著重重枷鎖,卻仍有余力,直接向沈遲意飛撲過來。
他微微張開,里一點寒芒閃爍,這人竟在里藏了一枚刀片!
李鈺恨毒了壞他計劃的沈遲意,雖然雙手雙腳被束,卻仍有把握擊殺一個孱弱子。
眼瞧著自己就要撲到沈遲意跟前,他指尖甚至快要及沈遲意發,李鈺眼底出幾分怨毒,舌尖的刀片正要從沈遲意脖頸間劃過,他突然心口一涼,一柄雪亮長劍居然貫穿了他的口!
李鈺不可思議地轉過頭,就見衛諺不知何時鬼魅一般出現在自己后,他神冷厲,無聲無息地把長劍往前遞了三寸。
李鈺口中噴出一鮮來,心中充滿怨毒不甘,他不知道哪里來的力氣,突然力向前,湊在沈遲意耳邊低聲道出一句:“沈家出事…最益的莫過于衛諺,你猜猜軍械…一案,和他有沒有關系?”
他說罷便絕了氣息,尸首伏在地上,在彈不得了。
但他臨死前的那番話,無疑在沈遲意心中掀起了驚濤駭浪。
沈家軍械案和衛諺有關?是衛諺籌謀設計的?
那為什麼朝廷還要把這樁案子移給衛諺?或者說…是衛諺暗中運作,這才讓朝廷把案子到他手里?
不!李鈺亦是歹毒之人,此事疑點重重,他的話不能全信。
沈遲意深吸了口氣,拼命住翻涌的心緒。
衛諺長劍歸鞘,盯著李鈺的尸首,面上還有些凜冽冷意,又見呆立不,蹙著眉道:“你怎麼了?”他眉頭擰得更:“傷到哪里了?”
說著一副想瞧傷的樣子。
沈遲意這才回過神來,往后退了一步:“我無礙。”
衛諺上下打量幾遍,確定真的無礙,這才微哼了聲:“李鈺被我刺死了,不要怕。”
沈遲意心緒煩,隨口敷衍:“我沒怕。”方才那個椅子是故意踢到的,眼瞧著李鈺沖過來,張是有的,還沒來得及害怕呢,衛諺便進來了。
衛諺不知道又哪里不痛快了,瞇起眼,重重強調:“方才我救了你,一劍刺死了李鈺,你真的不怕?”
這丫頭到底在想什麼?難道就沒注意到他英雄救時的瀟灑姿態嗎?
沈遲意不搭理他了,衛諺討了個沒趣,悻悻地把周釗進來理尸首,李鈺這次能突然牢而出,負責看押的人自然逃不了責任,他理完后續的一應事宜,這才又轉向沈遲意:“你上的蠱毒…不必太過擔憂,我既答應了為你解毒,便不會讓你出事。”
他沉默了下才道:“雖然李鈺已死,但我已經找到了能為你解毒的人。”
難怪他這麼輕易就殺了李鈺,理起后續來也不慌不忙,果然留有后手。
沈遲意就是再不爽他,這時也不由高看了他一眼,更何況這人方才還救了自己命,緩了緩神:“是誰?“衛諺閉了閉眼,似乎下定了某種決心,才道出那個名字:“羌族的一位巫醫,漢名夏洵。”他沉道:“羌族已徹底投效于我,夏洵此人…”他難得躊躇:“擅醫擅毒,對蠱毒也是造詣頗深,我之前去信給仔細描述了你的癥狀,有八的把握可以一試。”
沈遲意聽到夏洵這個名字,又勾出一段回憶來。
這個人在原書里沒有正面出現過,至截止到看的地方沒出現。不過衛諺卻提起過幾次,每每提起來都神奇特,還讓薛素因此吃了飛醋,好多讀者在評論區猜,夏洵是不是衛諺初或者白月什麼的…
衛諺甚猶豫,提到夏洵的短短幾句卻停頓三四回…果然有些不對勁啊。
沈遲意哪怕中著蠱毒,也按捺不住心中好奇:“世子是要把請來王府嗎?”那薛素和夏洵面,一個朱砂痣一個白月,豈不是很有趣兒?
衛諺搖頭:“不便前來,我也不會讓進蓉城。”他瞥了沈遲意一眼:“我會帶你去羌族,讓為你診治。”
解毒救命要,沈遲意下思緒,微微一笑:“我很期待見到那位夏姑娘。”
衛諺默了片刻,用一種奇特的眼神看著,轉走了。
沈遲意:“?”
……
衛諺和沈遲意都是有決斷之人,何況上的蠱毒也不允許他們耽擱時間。
從蓉城到羌族治理的地方約莫一日一夜的路程,兩人略休整一番,第二日一早便了。
沈遲意并不太多人知道自己中毒的事兒,猶豫道:“王府里…”
衛諺懶洋洋地瞟了一眼:“早布置好了,我讓你邊的丫鬟在病床上冒充你兩日,瞞過眾人,王爺那里我也使了法子拖延,讓他能在佛寺多待個五六日。”
這般妥帖有些顛覆沈遲意心里,衛諺魯莽武夫的形象,略有訝異,不過很快又把腦袋回了馬車。
衛諺并非心大意之人,只是懶得對人費心思,他費心這般布置,沈遲意連個好臉也沒給他一個,讓他又不痛快起來。
他用劍柄挑開車簾:“還在為那事兒生氣呢?”
沈遲意琢磨著李鈺臨死前的那句話,跟這事相比,之前兩人爭執反倒是小事了。
心緒煩,蹙眉看了他一眼,敷衍道:“沒有。”
“真沒生氣?”衛諺懶洋洋地撐著下:“那就給哥哥笑一個。”
沈遲意:“…”
猜你喜歡
-
完結3151 章

裝傻王爺俏醫妃
猝死在實驗室的柳拭眉,一朝穿越就失了身,被迫訂婚於傻二王爺。 未婚夫五歲智商,又乖又黏、又奶又兇。天天纏著她要親親、抱抱、舉高高,眼裡隻有她! 繼母繼妹暗害,他幫撕!父親不疼不愛,他幫懟!情敵上門挑釁,他幫盤! 可儘管她左手當世醫聖、右手一代毒師,唯獨,她家狗子這傻病,多少湯藥都不管用! 某日,她盯著二傻子剛剛倒進水溝裡的藥,這才醒悟:“原來你是裝的!” 靠著奧斯卡小金人的演技,這二狗子到底在她這裡占了多少便宜? 披得好好的小馬甲被撕了,他精緻絕倫的臉上笑容僵凝:“媳婦兒,你聽我解釋!”
386.5萬字7.72 1918324 -
完結1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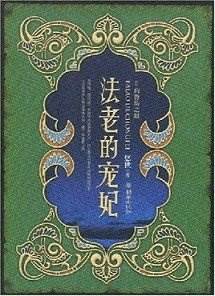
法老的寵妃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利」!? 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他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方向前進……
71.2萬字8 55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