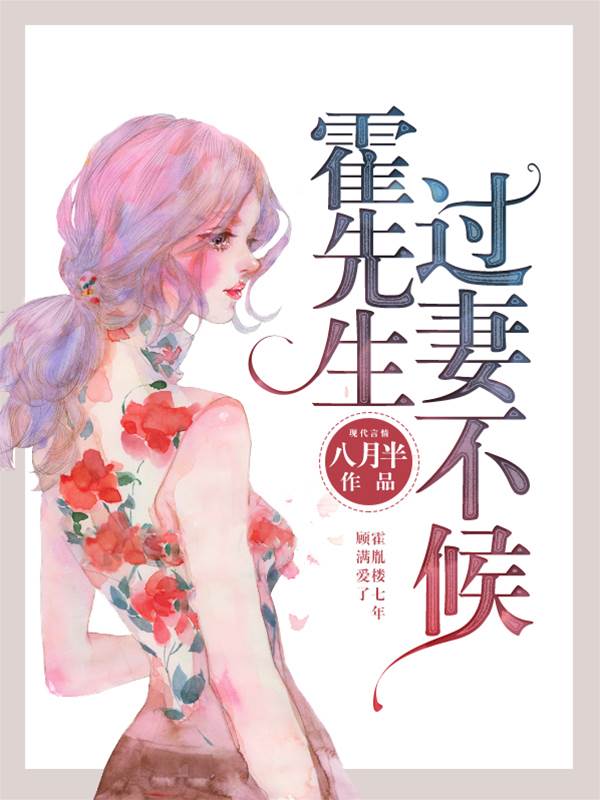《嫁給喬醫生》 第53章 隔河相望
差不多快到了。
飛行三小時,估還有半小時到達喀土穆,喬越掐準時間起去拿車鑰匙。
手放在門口時有那麼一瞬的猶豫,電筒掃過,圈下桌椅整齊。
仿佛又回到那些明的清晨,某人像乖學生一樣坐在這里筆疾書,然后抬頭沖他笑了下,出角淺淺梨渦。
“呵。”
黑暗里響起一聲輕笑,短促收尾。喬越拉開屜,車鑰匙不見了。
“喂,”列夫靠在門口,手里晃著一抹銀:“我拿了,走吧。”
看來早有準備。
“你說怪不怪,明明就了兩個人,可總覺一下子冷清了不……車你開還是我開?”
他把鑰匙拋出去,喬越揚手握住看也不看地扔回去:“你來。”
心不怎麼好,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車速。
而這輛老得不能再老的吉普車是唯一的代步工,上了80碼就渾作響,一百以上絕對首四離。
列夫干脆地開門發車:“上次找到信號的點在哪?”
“村東邊緣。”
喬越上車后就一言不發,向窗外,有些出神。
“舍不得?”
男人輕笑,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承認得大方:“是啊,舍不得。”
習慣真是種很可怕的力量。
“好在這次項目時間不長,等這里的人接手完畢,到時候……”人熊嘿嘿笑:“提前能走也說不定。”
手指無意識地碾。
提前走,回家好好過日子。這還真是個。力十足的條件。
喬越了下鼻尖:“工作量加倍?”
“怎麼,不愿意?”
男人勾起角:“有舍有得。”
人熊忍笑。
外面一片漆黑,吉普車行駛在遼闊的平原上,上空夜幕無邊,星野四垂。有種時間和空間都被空的錯覺。
有點迷失。
“就在這附近。”
列夫遲疑地停車,高大的俄羅斯男人把服起來扇風:“這里烏漆墨黑的,又沒個燈,也沒標牌,你怎麼知道是這?”
喬越指著星空:“東西南北。”
說了當沒說。
或許這邊是另一個基站覆蓋的范圍區,兩人出手機邊走邊找。
列夫興高采烈:“有了!有了有了!”
恭喜啊,幾個月了?
喬越看著自己信號網絡全無的提示界面,悶不做聲繼續找。心想著該死的全球通,偏偏這時候沒通全球。
人熊眉飛舞地開始撥號碼,電話一通喬越快速奪過。
男人漲紅了臉:“喂!”
聽筒里:“。”(俄語,你好。偏親昵。)
喬越愣了下:“你沒打給左微?”
紅人熊把手機搶過去,著脖子道:“我當然先打給我媽媽!”
喬醫生:“……”
列夫和家里聊得熱絡,喬醫生頻頻看時間,這一聊就快半小時。最后還用很稚氣的口吻對話筒里說著什麼,應該是在逗孩子。
歡樂的背景之外是喬越略冷的氣場。
他依舊沒找到信號。
喬醫生放下手機,以表面的沉寂來掩飾心的……發狂。
列夫逗著逗著忽覺脊背涼,像是有雙眼睛盯著自己。他下意識瞄了眼,喬越正盯著手機,瑩瑩屏幕反在廓分明的臉上,一臉認真的表。
不是他啊。
他繼續逗孩子,一口氣將幾個月不見的相思全部表達出來,最后才不舍地掛了。
人熊舒心后意識到什麼:“你怎麼不打?”
喬越盯著他沒說話,眼神卻讓人瘆的慌。
“啊!”他了聲,最后嘿嘿笑:“那再等等啊,我再給左微打一個。”
喬越手揣包里,繼而無奈輕笑。
也是,兩個都在一起。
沒想到電話一打就通了,列夫沒準備好有些張,結結語無倫次:“你左好微。”
左微:“……”
“微……你還好——”
電話那頭的左微啞著嗓子:“給喬越。”
“恩?”當著他的面找喬越?
人不耐煩:“我說電話給喬越,蘇夏沒跟我在一起!”
人熊被吼得有些懵:“蘇夏怎麼沒跟你一起?”
喬越抬頭的作僵了下:“什麼意思?”
列夫把電話給他,他慢慢舉起放在耳邊,聲音低的可怕:“蘇夏沒跟你在一起,怎麼回事?”
左微把前因后果說了,空曠靜謐的環境下聲音清楚地從聽筒中飄出。列夫打量喬越的臉,明明沒什麼表,卻著一子冷厲。
“那他們明天幾點去?”
“大概10點。”
“早上出發給這個手機打電話。”喬越一字一句:“我會在這里等著。”
喬越撥通蘇夏的電話,悉的無法連接,看來那邊的信號也沒了,一時有些煩躁。
列夫忍不住安:“空中救援隊的人不也在麼?再說明天直升機就來接,應該不會有問題。”
喬越沉默。
他有些后悔,后悔在蘇夏上飛機前說了句“乖乖聽話”,那家伙心,寧愿自己委屈也不想給人添麻煩的包子格。
現在喬越恨不得蘇夏變得死皮賴臉一點,科打諢要求上去,那種承載6人的退役軍用直升機未必帶不走。
他著河對面站了會,最后:“算了,走吧。明天再來。”
此時是當地時間9點32分,尚未決堤。
只有等明天。
只是睡的時候并不安穩,口像是了一塊石頭,呼吸中著氣短。
半夢半醒間覺有人在搖他。
“……阿越,阿越,醒醒。”
喬越的耳朵像是隔著一層霧。
“阿越,再不醒我就走了啊。”
像是久違的嗔,綿而沮喪。
他手,那道影卻漸行漸遠。遠去的人無聲地流淚,回頭時黑白分明的眼,讓他的心驀然收。
“為什麼到現在你都不肯看我一眼……”
喬越剛要追上去,影就散了。他猛地從床上翻起,呼吸急促。
平時不怎麼做夢的,竟然夢到了蘇夏,他不迷信,可這時候偏偏覺得有些邪門。
不知哪里出了問題。
23點25分左右,地面忽然輕微震,連帶著喬越他們這邊都驚醒了幾個。
“地震了?”
“沒覺啊。”
“弱的,等等啊,再震就跑……”
喬越第一個沖出房門,著寂靜的夜空,心底沉得厲害。
當地時間23點25分,南科爾多凡州阿卜耶伊附近(11.3°n,28.7°e)出現一決口。
萬頃白尼羅河水傾。瀉而下,村莊淹沒。而決口在水流沖擊下坍塌出更大的范圍,災況比想象中更嚴重。
當初劃定的安全區不再安全,然而蘇夏他們尚不知。
這會不人一臉茫然地站在門口,聽著遠滾滾浪聲,有些還拿出扇子一邊扇風一邊嘆:“今晚涼快啊,風都比以前大。”
蘇夏渾冷汗,伊思心很寬地安:“沒事的,沒事的,我們這里是安全區。”
別的沒聽懂,但是“沒事”這個詞蘇夏聽明白了。
真的沒事嗎?
“河離這里遠著呢。”
靜驚醒了孩子,床上的兩個小不點一聲蓋過一聲,卯足力氣比誰哭的嗓音大。伊思匆匆進屋哄,最后只剩下蘇夏一個人站在門口。
心跳的有些發慌,下意識捂著。不遠幾只土狗在路上跳著吼,甚至有的用牙咬主人的角,想把他們拖著走。
蘇夏看了會,轉掀簾子:“安置區在哪?”
人正在喂。,昏黃的煤油燈下,人的臉恬靜而慈祥。小嬰兒抱著的脯吮。吸,發出陣陣香甜的咕嘟聲。
沒有聽懂:“什麼?”
蘇夏換了個詞:“你老公,還有默罕默德,我們去找他們好不好?”
“為什麼?”
“你不擔心嗎?”蘇夏在煤油燈下比劃:“那里決堤了。”
懷中的小塔里察覺母親在,生怕有搶走“口糧”的用牙又磨又扯。
伊思疼得吸氣,不住擺手:“現在很晚,你看我有這麼多孩子,怎麼走?”
頭疼。勸不的頭疼,語言不通還要生生通的頭疼,意識不一樣還得互相融合的頭疼。
想著就更疼了。
外面有腳步聲和馬蹄聲,伊思偏頭聽了會,陷沉默。
“有人離開了。”
“恩?”
忽然有些慌,把塔里往床上一放開始團團轉:“看來是該走了。可是我有這麼多孩子,我還有這麼多東西,我的布也在外面,還有家里祖傳的織布機……”
蘇夏見滿屋走著念叨,忽然湊過來握著自己的手:“蘇,你得幫幫我。”
“你能不能說慢點……”蘇夏哭無淚。
這里的語言太復雜了,小單詞都是一串稀奇古怪的發音,說慢點一些常用的單詞能明白,可說快了真的就跟一只貓不停在嚨里咕嚕咕嚕一樣。
是真的一個字都沒聽懂。
“幫我帶幾個孩子,我們一起走。”
伊思把塔里包起來,綿綿的小嬰兒才睡著又被鬧醒,哭得氣勢洶洶。遞給蘇夏,見抱孩子的手法太生疏,干脆綁在前。
“走。”
這個詞聽懂了。伊思挨著讓孩子起床,一個個夢中被吵醒,大點的懵懵懂懂,小些的不依不饒。
蘇夏將晚上剩下的餅全部倒進背包里,從行李箱中了件外套系在腰間,再一手拎著一個孩子跟著往外。
這時候外面的人越來越多,左右手的小屁孩們見狀一個個都不配合地到扭,要麼蹲地上不肯走。
蘇夏氣得一人屁上小踢了下,搬起臉很嚴肅:“走。”
頓時老實了不。
伊思跑過去想去收拾晾著的布,蘇夏忙拉著往外,好不容易拉出門后對方又想著自己那個祖傳的織布機。
得得得。
后邊傳來急促的馬蹄音,條件好的開始用馬車。
這個時候準備撤離的人并不多,蘇夏看著只裝了一半的馬車眼睛一亮:“嘿,嘿!”
來人停下。
蘇夏把伊思往前推,意思是通通,讓們蹭個馬車。
可對方卻皺眉:“我只有一匹馬,帶不走這麼多人。”
“我們不重的,又都是孩子,您能不能試試?”伊思祈求,蘇夏忙拍了拍幾個小頭,給了個眼神暗示。
于是一排星星眼齊刷刷著馬車主。
對方心:“都上來吧。”
蘇夏跟著爬上馬車,上面擁得快要坐不穩,口的孩子被得哭,忙低頭親吻額頭語哄:“乖乖,不哭。”
小子在懷里地靠著,順帶委屈地噎了好幾下,最終抱著的胳膊不撒手。
心底一片。
馬兒試了幾次,終于慢慢邁開步子,滾滾車聲響,蘇夏著漸去漸遠的住松了口氣。
猜你喜歡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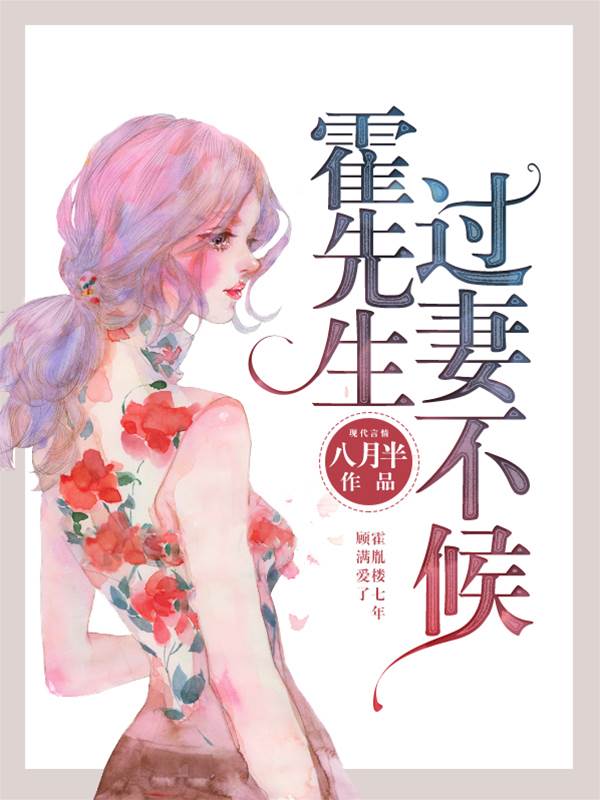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07 -
完結283 章

獨占偏寵
葉奚不拍吻戲,在圈內已不是秘密。一次頒獎典禮上,剛提名最佳女主角的葉奚突然被主持人cue到。“葉女神快三年沒拍過吻戲了,今天必須得給我們個交代。”面對現場追問,葉奚眼神溫涼:“以前被瘋狗咬過,怕傳染給男演員。”眾人聽後不禁莞爾。鏡頭一轉來到前排,主持人故作委屈地問:“秦導,你信嗎?”向來高冷寡言的男人,笑的漫不經心:“女神說什麼,那就是什麼吧。”*人美歌甜頂流女神VS才華橫溢深情導演。*本文又名《返場熱戀》,破鏡重圓梗,男女主互為初戀。*年齡差五歲。*男主導演界顏值天花板,不接受反駁。
52.6萬字8.18 6376 -
連載363 章

少帥既然不娶,我嫁人你哭什麼
楚伯承像美麗的劇毒,明明致命,卻又讓人忍不住去靠近。可他們的關系,卻不為世俗所容。姜止試圖壓抑感情,不成想一朝放縱,陷入他的牢籠。他步步緊逼,她節節敗退。一場禁
64.7萬字8.18 18542 -
完結507 章

離不掉!高冷佛子為我墜神壇
【追妻火葬場 雙潔 假白月光 虐男主 打臉發瘋爽文】“離婚吧。”傅樾川輕描淡寫道,阮棠手裏還拿著沒來得及給他看的孕檢通知單。整整四年,阮棠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一場車禍,阮棠撞到腦子,記憶停在18歲,停在還沒愛上傅樾川的時候。麵對男人冷酷的嘴臉,阮棠表示:愛誰誰,反正這個戀愛腦她不當!-傅樾川薄情寡性,矜貴倨傲,沒把任何人放在心裏。阮棠說不愛他時,他隻當她在作妖,總有一天會像從前那樣,哭著求他回頭。可他等啊等啊,卻等來了阮棠和一堆小鮮肉的花邊新聞。傅樾川終於慌了,將人堵在機場的衛生間裏,掐著她細腰,聲音顫抖。“寶寶,能不能……能不能不離婚?”
88.1萬字8.18 184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