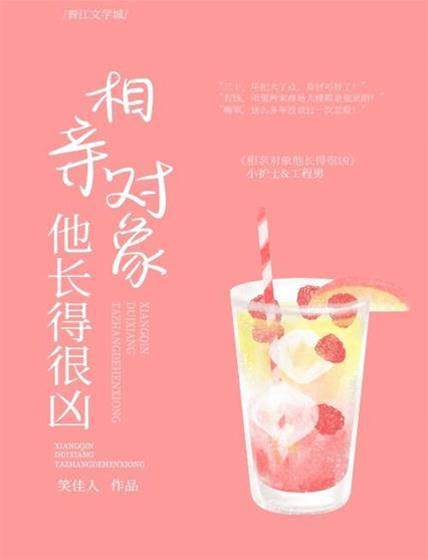《女配不想讓主角分手》 第六十七章
沈挽最終還是沒能控制得住謝無衍。
他艱難地站起, 渾燙得出奇,隨時可能撐破經脈,而亡。
然而, 他卻低低地笑了起來, 就如沈挽在封魔窟見到他的時候, 眼底一片赤紅,臉上的笑容除了猖狂之外,只能看見已經變得麻木的殺意。
謝無衍撕開周遭的藤蔓, 就好像不到疼痛一樣, 毫不在乎自己的已經被那些尖刺劃開深可見骨的傷痕。
制謝無衍已經耗費了沈挽大半的力氣, 跪坐在那一片藤蔓中間,抬頭看著他的背影。
“支撐著他活下來的,只有刻進骨子里的戰斗。只要他活著, 他就會不斷地殺人,直到自己傷口沒有辦法愈合, 軀徹底腐爛, 力竭而亡為止。”
“他為什麼不肯離開呢?非要活在這世上, 變一幅不人不鬼的樣子。”
“或許應該來問你——”
夏傾的聲音逐漸近了,如同魑魅一般, 不知何時出現在沈挽后, 呼吸想蛇形子一般, 舐著的脖頸:“你為什麼不愿意讓他離開呢?”
沈挽看著不遠的謝無衍。
沒意識到, 現在的謝無衍到底有多痛苦。
他的溫不再冰冷,強烈的生強迫著他全上下每一個部位都變武,就連皮下流淌著的都變得滾燙,
就像一個沒有意識,幻化人形態的武。
“承認吧, 其實自私一點也沒什麼不好。”
蔓藤悄無聲息地生長著,一寸寸束縛著沈挽的腰,仿佛要將整個人包裹一個不風的蠶蛹。
夏傾:“你可以和我一起留在這里,和他一起,池潼關會變一座死城,世界上再也沒有人來打擾你們。”
周圍的風聲逐漸變弱,蔓藤拉扯著的,一點點朝著夏傾的方向靠近。
約間似乎可以聽見風謠和紀飛臣的聲音由遠及近,但因為蔓藤的阻隔,所有的聲音都變得不真切了起來。
“到我這兒來。”夏傾的聲音很低,無比清晰地在沈挽耳畔響起,“我們是一樣的人,沒有人會比我更了解你了。”
是這樣的嗎。
火焰在頃刻間匯聚一把劍的形態,從沈挽手中生出,幾乎就在眨眼間,一個翻,接著兩人之期間無比近的距離,迅速將那柄劍準確地刺夏傾的之中。
抬頭看著夏傾的臉,無奈地嘆了口氣:“都說了,沒有人比我更懂。”
夏傾的確很聰明,一直在利用沈挽的肋,刺激著來放松神經,以此來找到突破口。
“而且。”沈挽補充了句,“我和你一不一樣,你說了不算。”
說著,趁著夏傾承下這一擊,還無法彈的間隙,迅速手穿進一旁被藤蔓束縛著的和尚的腔。
夏傾的瞳孔在一瞬間,發出一聲幾近撕心裂肺地尖。然后在頃刻間強行掙了那把劍,手夠向和尚的方向。
但沈挽已經握住了那和尚,夏傾的心臟。
滾燙的。
在跳著。
“大師。”
“大師。”
“給我講講佛經吧,大師。”
夏傾坐在廟前的石階上,手托著腮,笑意瀲滟地看著掃地的僧人。白的擺拖在地上,沾上了些許灰。
那不是什麼好的邂逅。
夏傾年的時候,父母招惹到了江湖上的人,一家人全被殺了個干凈。月影樓的樓主看長得漂亮,于是將人從死人堆里撈了出來。
自小就以殺人為營生,練了一,玉溫香后見封。只要出得價錢漂亮,什麼人都能殺,什麼人都敢殺。
樓主將養大,給錦玉食,對很好。
但人對你好,都是想從你上得到什麼。
夏傾一直都知道。
有活兒的時候推出去,沒活的時候就當個寵似的養在邊玩。夏傾什麼都有,但什麼都沒有。
時間長了,許多東西都變得不太在意。
殺的人多了,每晚都要暗自神傷,未免也太矯。
從頭到尾都是個惡人,自己選的,沒誰強迫。
有許多事夏傾都能料到。
比如月影樓招惹了仇家,樓主推出去擋刀,沒了庇護的人,就算夏傾是再好用的一把刀,也終究是會斷的。
被被玩壞了子,但也終于找到機會逃了出來。
然后被他救了。
僧人不是什麼得道高僧,很年輕,法號清遠。
廟很小,周圍的村莊都很窮,沒什麼香火錢。但每次遇到有逃荒的人來到這討飯,清遠總會均出大半的糧食。
只顧活命的人是不知道恩的。
時間一久,隔三差五就有窮人往廟前一躺,好手好腳不愿意去找活,能混一頓就混一頓。
夏傾總會撐著下看著清遠大師揣著米兜出去,明明心知肚明那些人的心思,但卻還是溫和地分出大半的米。
心想:白癡。
但想了想,不是白癡也不會救自己。
一腥味,就算躺在大道上,也沒有人敢管這個閑事。
但廟里真的太窮了。
多了這麼個累贅,還得照顧附近那些窮人,僧人碗中的粥越來越稀,但還是每次都會先把水瀝干,撈出大半的米來給。
夏傾不喜歡白人恩。
但是除了殺人,什麼都不會做。
但長得很漂亮,許多店家都愿意花高價錢請來干活,是站在那兒都攬客。
夏傾不是個在乎面的人,偶爾遇見些借機揩油,都會笑瞇瞇地調笑回去。一來二去,店里的生意好上不。
直到某日來了個大人,得寸進尺。
夏傾得罪了人,上傷沒好全,被那人手下的侍衛攔住,辱了一番。
那日正好下了場大雨。
店家不敢再留。
靜靜地看了會兒雨,突然就看見了清遠。
他撐著傘站在不遠,說雨天擔心施主不好回去。
夏傾突然發現,總會有人會沒有理由地對人好。
喜歡誰,就直接說了。
想做什麼,就直接做了。
原本就不是個良善守禮的人,清遠讓回頭,偏不回頭。
但許多東西都是沒有結果的。
無論那團火燒得有多麼熱烈,清遠總是安靜地站在火的對岸,靜靜地喊:“施主,切莫明知故錯了。”
沒過多久,村莊鬧了荒,死了大半的人。
清遠想救人。
他撐著禪杖,拿出廟所有的糧食,挨家挨戶的敲門。
但那些只是飛蛾撲火。
廟的糧食空了。
村的人沒得選,易子而食。
清遠又去了一趟。
回來的時候渾是,夏傾揭開他的袈裟,饒使是見過無數的,都不由覺得目驚心。
他為了救那些孩子,割去了自己的。
夏傾罵他白癡。
他說怎能不渡蒼生。
是的。
清遠渡的是蒼生,從來不是一個人。
夏傾又干起了殺人的營生,沒再回去寺廟,只是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在廟前放上一包袱的銀子。
直到某天夜里,放下包袱準備離開,廟門卻開了。
夏傾放下斗笠,轉準備離開。
清遠卻喊住,說外頭風重,前路難行,要不要進來喝杯茶。
一杯熱茶。
清遠勸回頭。
夏傾問他憑什麼勸他回頭。
意料之中的沉默。
夏傾笑著站起,清遠一言不發,抬頭看著廟宇中那盞佛像。
俯親吻那盞佛像,轉頭看向清遠。
“佛都敢看我,你為什麼不敢?”
沒了月影樓,夏傾很快就再次被佛家找上門。
不記得那天自己殺了多人,只記得自己倒在冰冷的泊之中,突然看見了一個人的影。
黃袍,禪杖。
他背著離開,但卻被仇人卻追上。
他讓走,對說:“施主,不要回頭。”
夏傾回來的時候,僧人被掛在十字架上暴曬,上全是鮮,將袈裟染紅。
出手,捧起他的臉。
僧人睜開眼,只剩下最后一口氣,定定地看著的眼眸。
他問為何回頭。
夏傾:“我偏要回頭。”
周遭的瞬間燃起大火,仇敵囂著,這次一定要將燒灰燼。
但夏傾沒有死,變了靈魅。
那是一場殘忍的屠殺。
夏傾滿是地在僧人面前跪下,掏出了自己的心臟,塞進了僧人的膛里,出手著他的臉頰,讓他醒來。
僧人睜開眼。
但雙眸一片空。
夏傾卻對此視而不見,出手將他擁懷中。
“施主,莫要再明知故錯了。”
“如果我非要一意孤行呢。”
晚了一步。
沈挽在夏傾趕過來之間,將清遠腔的心臟給扯了出來。
“不——”
夏傾的力量在一瞬間突然突破了瓶頸,帶著強烈的沖擊撲向沈挽,出手要躲回心臟。
“把他還給我,還給我。”
“抱歉。”沈挽說。
下一秒,將心臟碎。
夏傾的瞳孔瞬間,臉上全是強烈的憤怒和絕,嘶吼了起來,仿佛要和沈挽同歸于盡。
“夏傾。”沈挽喊住,“回頭。”
夏傾剎那怔住,僵地轉過頭。
僧人的尸極速腐敗著,但眼睛卻不知何時已經睜開,眸底閃爍著些神,看著夏傾的方向。
夏傾上的狂躁一點點地平靜了下來,轉,邁開步子,走到僧人邊,跪坐了下來。
僧人張張合合,但聲音卻聽不清。
將趴下,近他耳邊。
清遠說:“夏傾姑娘,我不敢看佛。”
這是他第一次喊的名字。
而不是施主。
他也沒再自稱“貧僧”。
“佛都敢看我,你為什麼不敢?”
“我不敢看佛。”
這是他想對說出口的,私心。
“所以我必須毀掉你的心臟。”沈挽說,“這是他最后一點殘念,連你都不知道的殘念。是他當年,想要對你說出口的最后一句話。”
“有了這點殘念,他或許還有轉生的機會。如果你不肯放他離開,他就會徹底死去。”
“我不想要轉生。”夏傾抖著直起,眼淚一滴一滴落下,出手,抱住清遠已經潰爛的軀,抵住他的額頭,“我不想要下輩子。”
夏傾的迅速腐化著,將自己的魂魄當做引起,纏繞起清遠最后一點殘念,一點點地包裹了起來。
…是想消耗自己的魂魄將清遠的殘念留下,兩個人從此變無法超生的惡鬼嗎?
終于,清遠的徹底腐化,甚至都無法凝的形態。
夏傾抬起頭,閉上眼睛。
“下輩子?”
“我不想再過一輩子了。”
沈挽看。
夏傾的眼睫抖著,終于,發出一聲絕的嘶吼聲,匍匐在地。
的通散著,一點點地匯聚起來,鋪了一條直通天際的路,將清遠的殘念送走。
最后還是沒有留下清遠的殘念。
而是用自己的魂魄當做保護,確保他能安穩地轉生。
只是這樣,夏傾的魂魄會徹底消散。
沈挽一言不發地轉。
“沈挽。”夏傾突然喊住了。
沈挽側過頭。
夏傾站起,但軀也開始一點點消散:“當謝無衍的意念消失之后,如果他還沒有復活,拿他就會和清遠一樣,再也無法轉世。”
沈挽:“我知道了。”
夏傾突然笑了起來,眼底含淚,似乎是在嘲笑,但卻也是對自己的絕:“看,我就說了,你也得和我一樣。”
“你也要走到這一步的。”
影過后,夏傾的軀消失在夜幕之中。
沈挽抬頭看向不遠。
剛才趕來的紀飛臣和風謠,在看見沈挽攻向夏傾的時候,就已經轉選擇去控制住暴的謝無衍。
謝無衍還在失控。
即使兩人人合理,也只能勉強將他束縛住。
沈挽了鼻子,走上前:“我來吧。”
“你……”風謠言又止,憂心忡忡地看了一眼,但還是讓開。
沈挽出手搭上謝無衍的肩,卻被他甩開。
他想被困的兇一樣,一下下撞擊著紀飛臣設下的屏障,鮮順著傷口淌下。
從一開始就忍著的緒,終于難以控制。
沈挽咬著下,緩緩蹲下子,將手撐住額頭,終于難以控制地落下眼淚。
不知道過了多久,周圍突然安靜了下來。
有人蹲在了自己前。
那人出手,握住了沈挽的臉頰,帶著些溫度的拇指去眼角的眼淚,作生疏而又僵。
沈挽稍怔,錯愕地抬起頭。
謝無衍看著,眼底看上去依然空,但約間仿佛能看到一點星。他皺起眉,角了,似乎說了什麼話。
沈挽下意識靠近,在聽清他說的那幾個字之后,剎那間哽咽了起來,將謝無衍抱。
“沈挽。”
讓他拼死活下去的不僅僅只有那個承諾。
他還記得的名字。
猜你喜歡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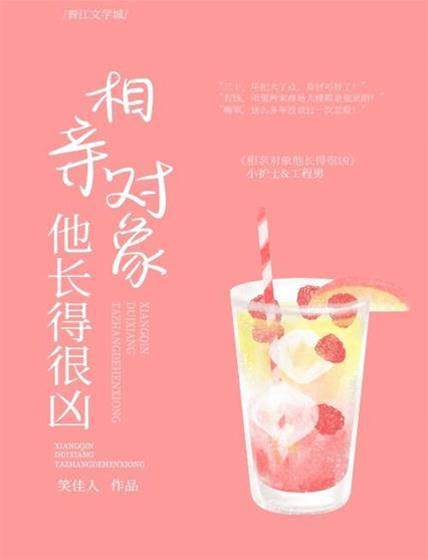
相親對象他長得很兇
江桃皮膚白皙、面相甜美,護士工作穩定,親友們熱衷為她做媒。 護士長也為她介紹了一位。 「三十,年紀大了點,身材可好了」 「有錢,市裡兩家商場大樓都是他家的」 「嘴笨,這麼多年沒談過一次戀愛」 很快,江桃
20.8萬字8.57 43539 -
完結320 章

奸臣的話癆婢女
裴沅禎是個大奸臣,玩弄權術、心狠手辣,手上沾了無數人命,連龍椅上的小皇帝都被他擺佈於股掌之間。 朝堂上下,無一不談“裴”色變、諱莫如深。 沈梔梔是剛賣進裴府的燒火丫頭,原本只想搞點錢以後贖身嫁個老實人。 某日,裴沅禎心情不好,伺候的婢女們個個戰戰兢兢不敢靠近。 負責膳食的婆子慌忙之下逮住沈梔梔,哄道:“丫頭,這頓飯你若是能伺候大人舒舒服服地用了,回頭管家賞你二兩銀子。” 沈梔梔眼睛一亮,奔着賞銀就進去了。 她看着端坐在太師椅上面色陰沉的男人,小聲道:“大人,吃飯啦,今晚有桂花魚哦。” 裴沅禎摩挲玉扳指的動作停下,冷冷掀眼。 沈梔梔脖頸一縮,想了想,鼓起勇氣勸道: “大人莫生氣,氣出病來無人替;你若氣死誰如意,況且傷身又費力;拍桌打凳發脾氣,有理反倒變沒理;人生在世不容易,作踐自己多可惜......大人,該吃晚飯啦。” 裴沅禎:“..........” 此時門外,管家、婆子、婢女驚恐地跪了一地。 紛紛預測,這丫頭恐怕要血濺當場。 卻不想,沈梔梔不僅沒血濺當場,反而從個燒火丫頭扶搖直上成了裴奸臣的心尖尖。. 他一生銜悲茹恨,自甘沉淪。後來,她陪他走過泥濘黑夜,萬千風雪。 裴沅禎才明白,世上並非只有仇與恨,還有一種,是煙火人間。 小劇場: 近日,朝堂文武百官們發現首輔大人越來越陰晴不定了,衆人膽戰心驚。 有人私下打聽,才得知原委。 據說——是因爲府上丟了個小丫鬟。 文武百官們:??? 城門牆角,裴沅禎騎在馬上,目光凜冽地盯着膽大包天的女人。 剛贖身出來沒兩天的沈梔梔:QAQ 我想回去嫁個老實人來着。
50萬字8.18 44535 -
完結99 章

天鵝頸
南城歌劇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舞臺上的今兮吸引—— 女生腰肢纖細,身材曲線窈窕,聚光燈照在她的臉上,眼波流轉之間,瀲灩生姿。 她美到連身上穿着的一襲紅裙都黯然失色。 容貌無法複製,但穿着可以,於是有人問今兮,那天的裙子是在哪裏買的。 今兮搖頭:“抱歉,我不知道。” 她轉身離開,到家後,看着垃圾桶裏被撕碎的裙子,以及始作俑者。 今兮:“你賠我裙子。” 話音落下,賀司珩俯身過來,聲線沉沉:“你的裙子不都是我買的?” 她笑:“也都是你撕壞的。” —— 賀司珩清心寡慾,沒什麼想要的,遇到今兮後,他想做兩件事—— 1.看她臉紅。 2.讓她眼紅。 到後來,他抱着她,吻過她雪白的天鵝頸,看她臉紅又眼紅,他終於還是得償所願。
31.2萬字8.18 27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