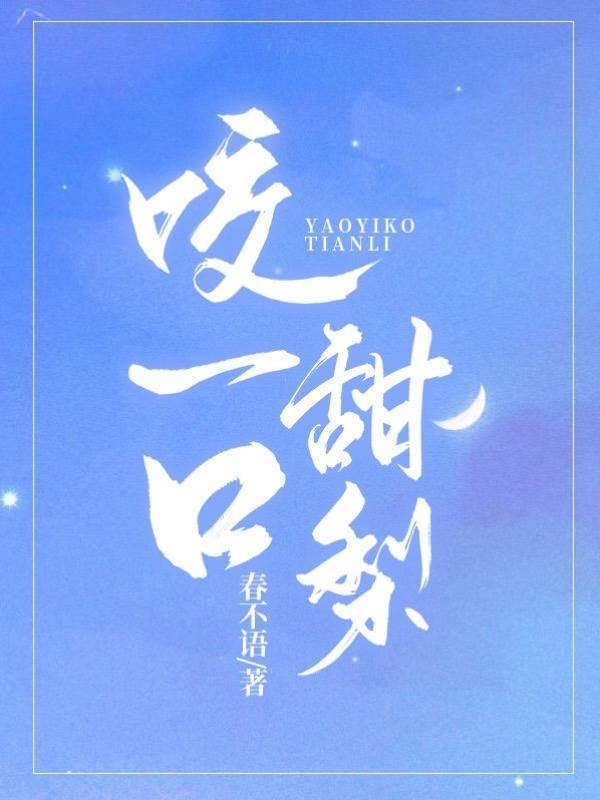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重生軍婚之肥妻翻身》 番外1、尋訪前世(2)
沈東遠臉上的神凝重起來,大姨家,他是知道的,曾經梅子告訴過他關于自己的來歷,但是這幾年來,他從沒有聽梅子提起過關于從前的事,他也不敢提。
梅子向來是那種非常懂事的人,知道他訓練任務重,去年臘月里,土豆和苗苗了風寒,發燒很嚴重,怕耽誤他訓練都沒有告訴他,那麼發生了什麼讓突然想去了呢?
不管什麼原因,只要梅子需要,他就陪去。
他沉聲說道,“好我陪你去,什麼時候出發,我先去請個假。”
“越快越好,”朱海眉說道,“從這兒開車過去的話,大概五六個小時的時間,現在白天的時間長,如果中午能出發的話,到了青州應該天還不算晚,我們找個地方住宿,明天一早,就直接去大姨家。”
“好,你現在辦公室等我電話,我立刻就去請假。”
朱海眉覺得心中溫暖極了,說道,“好,我等你電話。”
他們離開北京的時候,已經一點多了,朱海眉借了公司的車,沈東遠開著,坐在副駕駛上,手里拿的是早上宋清波給的那份報紙。
大姨和大姨夫從未提起過的父母,即便是后來知道自己是被寄養在這里的,不止一次的追問,他們也是諱莫如深。
朱海眉靜靜的看著報紙上的照片,希能揭開這個謎團。
晚上的時候他們在青州住宿,朱海眉大半夜都沒有睡著覺,現在的大姨和大姨夫也就是三十歲左右的年齡,比現在稍大一點,但是表哥現在也得有七八歲的樣子了,表姐也得四五歲了,在想要怎麼樣給大姨留點錢或者想辦法讓他們過上好日子。
小時候家里孩子多,用錢的地方也多,大姨和大姨夫都是老實的莊稼人,偶爾做點買賣,也僅僅是能夠解決溫飽,離著奔小康可是差的遠。
沈東遠聽見翻來覆去的睡不著覺,索把摟在懷里說悄悄話,“梅子,為什麼睡不著呢?”
朱海眉嘆口氣,“對父母,我倒是沒有太大的,我就想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把我寄養到大姨家。但是對于大姨和大姨夫,我還是希他們能過上富裕的生活,我在想,要怎麼樣才能幫得到他們?”
沈東遠想了想說道,“確實不太好辦,如果你教給他們做生意,那也得看他們有沒有這個頭腦,若是給他們錢,又該怎麼樣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解釋呢?”
“有沒有解釋,我覺得無所謂,我是在擔心,若是給他們錢,讓他們有那種不勞而獲的思想,到最后就是害了他們呀。”
梅子說的話很道理,但是沈東遠卻安道,“別想了,就是想也沒有用,日子還長著呢,我們可以從其他的地方慢慢的幫助他們,完全沒有必要急于一時。”
朱海眉嘆口氣,“我應該早點來的。”
“不怪你,”沈東遠說道,“咱們家家里家外的都要靠著你,所以要怪,也只能怪我。”
朱海眉沒有回答,這也不是怪不怪的問題,說道,“你說我會不會在大姨家中,看到小時候的我?”
呃,沈東遠從來就沒有往這方面想過,他說道,“那看一下小時候的你也不錯呀,不如我們領養吧,當自己的孩子來養,讓永遠開心快樂。”
“難道你不覺得很怪異嗎?”
“按照你之前說的,現在應該也就是有兩三歲的樣子吧,那就是和土豆和苗苗一樣大,一個小孩子而已,有什麼怪異的。”
朱海眉不知道說什麼好,怎麼說都有一種怪怪的覺。
雖然朱海眉整個晚上都沒有休息好,但是第二天仍然起了個大早,和沈東遠吃過早飯,匆匆的上路了。
對于整個青州,朱海眉還是很悉的,畢竟的高中時代,就是在青州度過的,雖然現在的房屋和后來的建筑有很大的變化,但是道路基本上,還是原來的道路,只不過是有些土路還沒有修柏油馬路而已。
憑借對前世的記憶,從青州市里,一直開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村子,朱坊村。
村里的路還很窄,里面也坑坑洼洼的,車輛進去就出不來了,他們把車停在村口, 然后進了村。
朱海眉站在村口仰視著那棵悉的大槐樹,仿佛又回到了前世一般,小時候和很多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景又浮現在了眼前,那麼無憂無慮的年時,現在回味起來,是那麼的讓人覺好。
沈東遠站在后面說道,“走吧。”
他們一進村,便有人好奇的看著他們,畢竟這個年代開輛車到村里來,還是很稀罕的。
朱海眉循著記憶中的路線,在村西頭,找到了大姨的家,他們家最好認了,在村的最西頭,第一家,大門朝著大路的那一家就是。
原來小的時候住的是這樣的土房呀,都快忘記了。
抬起腳來,就往里進,沈東遠剛想拉住,便聽見院子里響起一個細細的小孩的聲音,“你找誰呀?”
沈東遠趕跟過去,一看是一個大概是有三四歲的小孩,梳了兩個羊角辮,一個上面,扎了一朵紅的花,換了一紅的裳,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一只手拿著瓢,一只手拿著竹竿,周圍有幾只拳頭大小的小仔,爭著搶著吃地上的谷子。
他看看梅子。
朱海眉雖然不知道小時候的表姐長的什麼樣子的,但是很確定,這個小孩絕對不是自己。
“請問你們家大人在家嗎,我們想喝口水?”
小孩手指了指東屋前面的水缸說道,“要喝水自己去缸里舀吧,里面有瓢。”
朱海眉看了一眼那個大水缸,很確定這就是大姨家,別的不太記得,但是大水缸記得一清二楚,因為學了司馬砸缸的故事,差點把那個大水缸給砸掉,被大姨給揍了一頓。
“你們家大人呢?”朱海眉問道。
“誰呀,”從屋里傳出來一個壯年男子的聲音。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3163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629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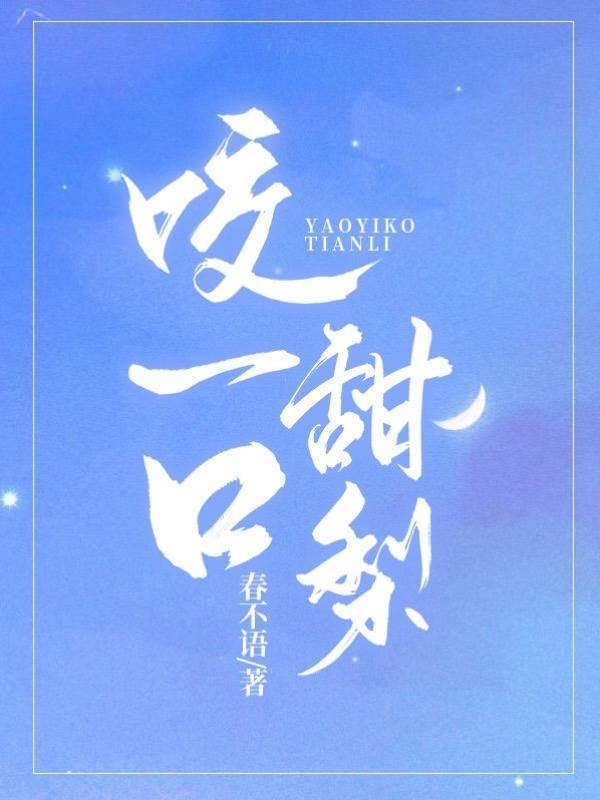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