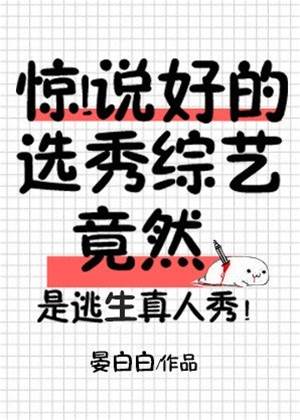《望春冰》 第58章 歧路楊朱
奉冰閉了閉眼,鎮定心神,到榻上坐下,吳致恒便將那四函書推給他。
“郎主讓我送給您的。”他道。
奉冰拆開書函,書是早被絕的緯書,辭句既無聊又危言聳聽,奉冰一頁又一頁緩慢地翻過,試圖從中拆解裴耽的意思,但腦子已經快要銹住,一旦開始運作,竟還發出吱嘎吱嘎陳舊的疼痛。
吳致恒道:“郎主還讀了兩句。”
奉冰抬頭。
吳致恒回憶:“是什麼……不知夏,不知冬,不見父,不見兄……”
“是《易經是類謀》。”奉冰沿著目錄尋知這一卷在第三函,打開,便翻到這一頁。
“不知夏,不知冬,不見父,不見兄,之莫莫,視之盲盲……其王可諫者全,不移者亡。”
“對!”吳致恒立刻道,“就是這一句。”
奉冰咬了咬牙。
——“王”是誰?
這長安城里的“王”,已只剩下趙王了。
裴耽曾對他說過:“若真有那一日,遇上危難,你可以去找趙王,他曉得如何做。若沒有危難,那你最好便不要手,置事外即可。”
奉冰的眼神變幻,他一頁又一頁地往后翻,可是書上的句子已不再能他的眼。
找趙王。
是了,趙王在京多年,一定立有基,裴耽既與圣人不睦,或許便與趙王走得更近。
其王可諫者全,不移者亡。
奉冰翻完了整三卷書,挪開后,卻見書函底部還有的夾層。他將手指探,便慢慢出一張窄幅的黃帛。
春時驀地倒一口涼氣,又立刻捂住了,再看吳伯,后者卻好像并不十分驚訝。
除了黃帛邊緣暗繡的龍紋,這一張小小帛書,看起來實在是平平無奇。奉冰正要展開,吳伯卻按住了他的手,眼神沉沉地道:“這是郎主留給您最后保命用的,您可千萬不要……”
奉冰沉默。黃帛一分分從末端展開,他先是認出了自己父親的璽印與圈紅,而后是一行極簡短而鋒銳的字,每一個字上竟全都蓋了鄭重的璽印:
“皇帝行事如有不可,可領北衙六衛,行便宜。”
一團茸茸的東西忽而拱了拱他的腳掌。
奉冰低頭,卻見是那只灰撲撲的小野兔,鼻翼正一聳一聳地往他的腳里鉆。奉冰將詔放回原,矮將那小野兔抱起來,那野兔卻朝著他齜了齜牙。
奉冰與它在極近的距離里對視,眸中閃過一溫的笑意,仿佛花樹上吹來的新雪。
“春時。”他站起,將小野兔放春時懷中,又了它的耳朵,“去給宅中的人手都放個假,就說是上元將至,都回家團圓去。”
春時領命去了。奉冰又看向吳伯,“圣旨查抄裴耽的舊宅舊人,估計您是要上通緝榜的,且在此呆著吧。”
吳致恒點頭應是,但仍不放心,追問:“郎君預備如何做?”
奉冰道:“我去找趙王。”
“——可眼下,還沒有到如此——迫的時候。”
說出這樣的話,吳致恒也覺頭發,但他必得說了,仿佛是裴耽奪了他的嚨,他必得為裴耽說這一句:“郎主他寧愿自己下獄刑,也不想您趟進這個渾水,趙王那邊,乃至北衙六衛的諸將軍,他都早有聯絡,如今于您最要的,是置事外——”
“我最恨的就是置事外!”奉冰突然抬高了聲音,“他要逞他的英雄,死便死了,我可也有我要做的事,不須他掛記到死!”
吳致恒眼皮直跳,“郎君,您不要總談這個‘死’字……”
“這麼厲害的東西,”奉冰冷笑,手指抓皺了緯書那已近殘破的書頁,“他留給我保命?!我真是謝謝他昏了頭的大恩大德。”
吳致恒從沒聽過李郎君說出如此尖刻的話,甚至到自己有些招架不住。奉冰容溫潤,但那外表上霏微的霧都被刺破了,出嶙峋的極扎手的鋒芒,花同雪俱散去,日凌凌,不留余地。吳致恒忽然疑,郎主知道李郎君有著這樣的鋒芒嗎?
奉冰讓春時陪著吳伯,自己穿一布裳,兩手空空地往十王宅走去。
距離裴耽接旨而趕赴刑部,尚且不到一個時辰,但長天風雪,已然覆蓋了舊的車轍,適才還津津有味地看著熱鬧的行人們也早都散去,各自奔忙。街道里坊間仍留有過年的余慶,紅的碎紙片點綴著白的雪泥,肅肅的風似刀刃,帶著威脅意味拍上來,奉冰裹了衽。
他先去興寧坊的十王宅尋找奉硯,奉硯卻不在家,據仆人說,是昨夜歇宿在平康坊了。于是他又折回南返,到平康坊去。
天尚早,平康坊的勾欄酒肆甚至還未開張,他走這座沉寂的歡樂場,雕金的闌干,嵌銀箔的燈籠,重重疊疊的紗幔,此刻滅著掩著,都像前朝的風景。趙王李奉硯最常去的地方名芳辰館,前門正閉著,奉冰繞到后院,那里據說是趙王包下來,住著傳言中他豢養的外室人。
奉硯或許是得到了家丁傳來的消息,竟已在院門口候著他。看他臉,奉硯也不多說什麼,便延請他。
一名淡妝子從室里探出頭,又回去,奉冰聽見低聲地喚人:“過來,不要跑!”俄而那室的簾帷便拉。
奉硯看著奉冰落座飲茶,才緩緩地道:“你是為裴相的事而來的?”
奉冰點頭。
奉硯盯住了他,“你如此信任我?”
茶香裊裊,兩兄弟的目在空中錯,奉冰的面紋不,低垂了眼睫,淡淡地道:“是裴耽信任你。他說,若遇上危難,可以來找你。”
李奉硯笑笑,“即使五年前,我將你拋下,獨自逃去了驪山?”
“我們四兄弟中,你是唯一一個還有母親在的。”奉冰平和地道,“汝南周氏也不算小家族了,你多所顧慮,謹小慎微,凡事都不出頭,是以能保全至今。”
“除了母妃,”李奉硯頓了頓,“我其實……”他的表晦,奉冰很難看懂,他卻還掩飾地站起來走了兩圈,才又道:“驪山圍獵時,裴相已做了部署——你知道神策軍中有他的人吧?圣人將神策中尉撤換,我們便已到警惕。或許圣人也察覺風聲,所以從驪山回來便要撤他的職,然而這才第幾天,圣人又坐不住了。”
李奉硯的措辭讓奉冰有些微不適,在案邊挪了挪子。“我們”。他心想。裴耽與三哥,何時了“我們”?那他呢,他只是一個拿著裴耽送的東西“保命”的,最好是“置事外”的存在嗎?
然而李奉硯卻好像全然看穿了他的心思,默然一陣,慢慢地道:“我與裴相的,其實——”
“哎,哎!”一陣急促又低聲音的喚,一個男孩從室的簾下鉆了出來,那名淡妝子焦急地追在后,“殿下在議事呢,不要去吵殿下!”
那孩子卻不聽,手腳并用地要爬上李奉硯的,李奉硯自己也被嚇一跳,險些出“祖宗”,將那孩子抱起,那孩子卻還雙足蹬,一手去抓李奉硯的頭發。那子作勢要打孩子,孩子卻笑得更頑皮,直往奉硯懷里躲——
李奉硯頗狼狽地躲避著孩子的踢打,方才的沉穩全不見了,眼風瞟到奉冰,忽然靈機一地道:“阿川你看,這是四叔!四叔!”
奉冰結結實實地呆住。
一陣手忙腳之后,幾人重新落座。
那個阿川的孩子當真喊了聲“四叔”,嗣后子終于找著一只小竹馬給他玩,吸引去他的全部注意。子跪坐在奉硯邊,斂袖添茶,奉冰見眉眼綽約,神容端莊,與三哥間相得極其自然,心下已有了幾分論斷。
“裴耽……他早就知道了,對不對?”奉冰低聲。
李奉硯默認。
奉冰又抿了一口茶。對面是其樂融融的三口之家,沒有寶妝靚服,也無金玉雕飾,只是閑閑地吃著茶,用著點心,看孩子玩竹馬。但這平凡的景象,卻似乎已許久不曾在奉冰的生命里出現。
這個孩子,至已三歲了。
他的三哥,看起來謹慎、溫和、圓、真誠,但的確,也絕不是個簡單的人。
裴耽投向趙王,恐怕就是因為他知道趙王有牽累,也有希。
“說實話,我與裴耽,不算是過命的,我們只是各取所需,各有盤算。”李奉硯停頓了一下,沉聲地道:“他既讓你來找我,說明他的確信我,那我定不會背諾。”
--------------------
明天休息嗷~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走紅后豪門大佬成了我粉頭
江放因體質弱從小被家人送去寺廟當和尚,後來被老和尚趕回家,碰巧練習生出道的弟弟正準備參加一檔綜藝,需要邀請一位親人參加。 看在錢的面子上江放答應參加,誰知弟弟自帶黑熱搜體質,兄弟倆參加綜藝的消息剛在網上傳開。 黑子:怎麼什麼低學歷的人都能上綜藝,碰瓷王江齊這次嫌一人不夠,打算帶著他哥組個碰瓷組合嗎? 江?人送外號高冷校草學神?放:? ? ? ? 你們怕是不知道什麼叫碰瓷,傷殘那種。 節目開拍後 “臥槽,怎麼沒人說江齊的哥哥長這樣,這顏值我能舔壞無數隻手機!” “是我眼花了?為什麼我會在一檔綜藝上看到我們學校的校草。” “說江放低學歷的人認真的嗎,燕大學神了解一下?” # 只想撈一筆項目啟動資金沒想過混娛樂圈的江放爆火後,收穫了土豪粉一枚和後台黑粉連發的99條恐嚇私信。 土豪程肆:等他再發一條。 江放:? 土豪程肆:湊個整送他上路。 江放:順便撒點紙錢,走得安詳一點 。 # 程肆的妹妹為某明星花百萬砸銷量驚動了程家,程父程母擔心女兒被騙,讓程肆幫忙照看。 程肆在監督的過程中,學會了簽到打榜,學會了給愛豆應援,學會了花錢砸銷量,還學會了監守自盜。 妹妹:說好監督我的呢,你怎麼就成了我愛豆的粉頭? 表面高冷學神實則壞心眼受X表面霸道總裁實則老幹部攻
48.7萬字8.18 10821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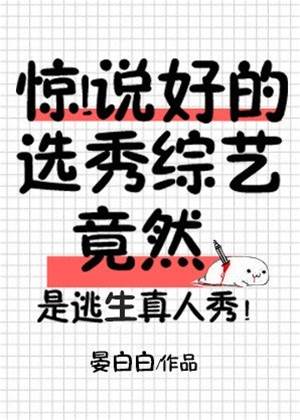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5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