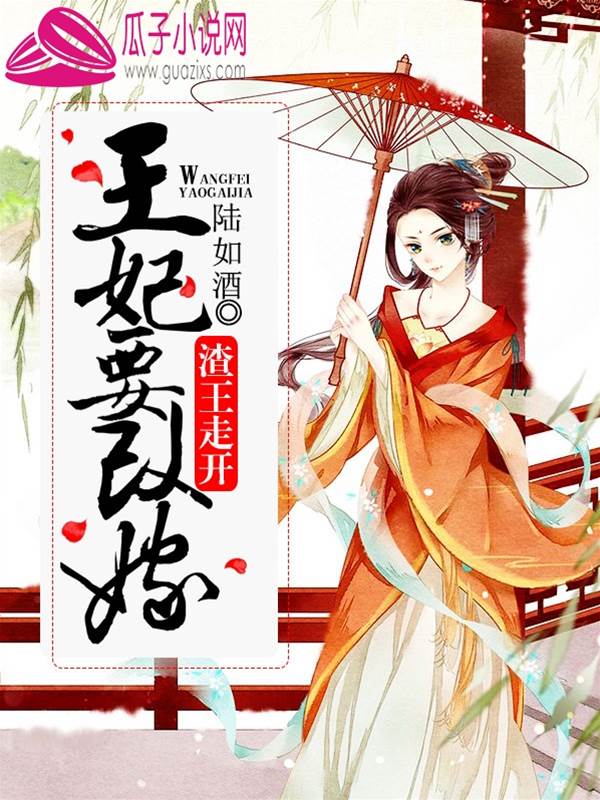《重生之貴婦》 第196章 追妻番外3
從殷家那里籌集了銀子, 燕王就再次離開平城去了邊關,留徐王妃、世子魏旸坐鎮燕王府。
十九歲的魏曕沒能跟隨父王出征,這會兒他還在王府里面的侍衛司當差, 協理侍衛們的調度、練等。
就像二爺魏昳在王府庫房那邊當差一樣,主事人都是燕王任命的正經屬, 魏曕兄弟只是前來觀學習,并非真的要他們負責這兩, 所以他們想懶休息,找個理由跟各的屬打聲招呼便可。
燕王不在,魏昳經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魏曕卻從來沒有懈怠過。
直到這日, 被他派出去的澄心堂小太監汪平匆匆找到侍衛司。
“爺, 二小姐要出城了,我回來時二小姐的馬車還在城門前排隊。”
魏曕:“何人陪同?”
汪平道:“只二小姐一個主子, 帶了一個丫鬟,八個護衛。”
魏曕不再多問, 命長風去馬廄牽馬,他先去了東華門外。
很快,長風牽了兩匹馬來,一匹是他的黑馬, 一匹是魏曕的白蹄烏。
主仆二人翻上馬,直奔城門前而去。
北地有戰事,燕王也不在平城,最近平城各城門看管得比平時要嚴很多,百姓們無論進出城門, 守城士兵都要仔細核驗份與隨行囊,遇到商隊, 更是要將貨一車一車地詳細檢查。
檢查得仔細,速度就慢下來。
殷家的馬車中,金盞好幾次挑開簾子往外,然后朝殷蕙抱怨:“今日怎麼這麼慢?”
殷蕙笑道:“慢就慢些,急什麼?”
金盞看向自家小姐,莫名就覺得今日小姐好像心特別好,好到連白白在這里浪費時間都不介意了。
殷蕙的心確實好,之前在燕王府、蜀王府關了那麼久,如今重回未嫁時,總算可以隨便出門風了。
本來祖父也要陪的,可惜臨時遇到老朋友初進平城,祖父還得去款待友人。
城門前的隊伍緩緩前進,終于到了殷蕙。
平城百姓,人人都知道燕王府,亦知道巨富殷家,守城士兵接過金盞手里的文書,簡單往車廂里掃了一眼,確定沒有藏著什麼人,這就給放了行。
離開城門不久,殷蕙便下了馬車,騎上的馬飛絮。
飛絮通雪白,殷蕙則穿了一套白中的馬裝,縱馬而去,仿佛一朵隨風而飛的海棠花。
魏曕策馬通過城門,看到的就是遠上馬的這一幕。
也有貴會騎馬,但沒有像跑得那麼快的。
魏曕先是心中一,怕從馬背上摔下來,下意識地加快速度去追,然而很快魏曕就放慢速度,只遠遠地跟著。
前面那道輕盈的影,一會兒縱馬疾馳,一會兒勒馬緩行,或是折樹枝放在手里把玩,或是跳到路邊看看不知名的野花,甚至還逗弄過一個農家,送了一朵頭上的絹花。
好像很快活,無論何時出臉龐,魏曕都看到在笑,桃花眸明亮似水。
走了一段距離,又上了馬,那姿何等練。
魏曕走了神。
親十載,他從不知道殷氏會騎馬,一嫁過來就像大嫂徐清婉看齊,舉止端莊,說話也是聲細語,魏曕就以為本也是如此。
可眼前這個十四歲的殷蕙,哪里與端莊沾邊了,端莊的子不會輕易拋頭面,更不會在沒有家人的陪同下單獨出門。
確實不端莊,可此時此刻,魏曕生不出任何訓斥的念頭,他只是目不轉睛地追隨著的影,默默地觀察著這個悉又陌生的妻子。
秋高氣爽,從附近來東山賞秋或上香的游人香客絡繹不絕,魏曕與殷蕙中間隔了很多影,大家同往一去,也就看不出是否有人在刻意跟蹤誰。
到了東山,殷蕙棄馬,步行往山上走去。
魏曕仍然保持距離跟著,看著與金盞有說有笑,看著有輕佻的公子想要上前搭訕卻被殷家的八個護衛趕走。
那八個護衛,個個形健壯魁梧,雖然平城最的姑娘就在眼前,這些護衛卻盡職盡責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訓練有素,可見殷墉對小孫的寵與看重。
長風走在主子后,對著那八個護衛暗暗發愁。他覺得,三爺第一次放下差事跑出來,肯定是想跟殷家二小姐見面的,可殷家二小姐說什麼都不愿意嫁給三爺,能高興理會三爺?如果三爺想強來,主仆倆對上那八個護衛,長風真的沒有信心。
到了東山寺,殷蕙先虔誠地跪拜佛祖上香,再捐了一筆厚的香油錢。
謝過佛祖,殷蕙就在寺里隨意地逛了起來,對東山上的一切都很悉,今日來乃是故地重游,哪怕只是東山寺里的一棵老槐樹,殷蕙也如見了老朋友一般高興,手輕輕那兩人才能合抱的樹,再仰起頭,看明的秋在碧綠的樹葉間跳躍。
有碎落到的上,十四歲的貌,仿佛也散發出一圈和的暈。
揚起的臉龐瑩白艷,長長的睫愜意地垂落,竟有種天人合一的融洽。
魏曕突然很想將這一幕畫下來。
念頭剛落,睜開眼睛,隨意般朝這邊瞥來。
魏曕竟下意識地往后一躲,長風見了,馬上也跟著躲開。
殷蕙沒有注意到香客里面有兩張悉的面孔,帶著金盞繼續往前走,漸漸來到了寺里的放生池前。
放生池里養著一只大烏,據說已經活了百年了,厚重的殼呈現出一種墨青,一不地趴在池水中間的山石腳下,半邊殼出水面,半邊泡在水里。
有一群孩子圍在池邊,喊來喊去的想讓大烏爬過來。
殷蕙走過去的時候,孩子們的注意力就都落到了上,畢竟,大烏哪里有人姐姐好看呢。
殷蕙笑著看著那只大烏。
小時候也喜歡看這只大烏,想出各種辦法哄大烏給點回應,甚至還要祖父花銀子把大烏買回家中,祖父笑著說這是寺里的烏,已經有了佛,怎能拿銀子./,殷蕙才罷了這個念頭。后來,祖父在自家的池子里養了烏,殼也很大,但殷蕙就是更喜歡寺里的這只。
坐到池子邊上,殷蕙解開腰間的荷包,里面裝了一些最新鮮的苞谷粒。
魚蝦昆蟲都不方便拿,幸好這只大烏也吃苞谷。
殷蕙先丟了一顆苞谷粒在大烏邊。
大烏了腦袋,旁邊一只小烏撲通一聲從山石上翻下,游過來吃了苞谷粒。
殷蕙繼續丟,丟到第七顆的時候,大烏終于吃到了,并且直接游到了殷蕙面前。
有孩子抓著樹枝要大烏的殼,被金盞勸止了。
殷蕙陪夠了大烏,趁日頭還不高,決定去山里面的道上跑馬。
金盞與六個護衛待在路口等著,只有兩個護衛保持距離跟在殷蕙后。
.
跑馬的人不算多,但也并非只有殷蕙主仆,因此,當后有馬蹄聲靠近,殷蕙也沒有回頭去看。
直到一匹四蹄雪白的黑馬從旁經過,才吸引了殷蕙的視線。
殷蕙知道,魏曕的坐騎便是一匹白蹄烏,乃燕王所贈,魏曕每次都門都騎白蹄烏。
就在殷蕙剛因為這匹白蹄烏想起魏曕的時候,那馬突然放慢速度,再與保持半個馬頭的距離同跑起來。
殷蕙終于看向馬背之上。
悉的清冷面容闖進視野,殷蕙心頭大震,本能地攥韁繩,再迅速垂眸,避開了他的視線。
魏曕則將的神變化看在眼里。
這一路,都快活得像只小蝴蝶,除了數幾個輕浮子弟,幾乎對誰都笑。
可就在剛剛,看見他的瞬間,笑容消失了,臉也冷了下去,回避的眼神,不知是怕他還是厭棄。
魏曕同樣攥了韁繩。
兩人的婚事沒有上輩子那麼順利,魏曕想過各種可能,在這一刻之前,他都沒有想過是自己不愿意嫁。
難道,真的也從景和二年回來了,而且不愿意再嫁他?
白蹄烏跑得很快,殷蕙勒住馬,如果魏曕守禮,就該繼續往前跑。
可魏曕也停了下來。
搭訕的意思顯無疑,殷墉派來保護孫的兩個護衛立即一前一后地擋在殷蕙面前,橫眉冷目地瞪著魏曕。
魏曕示意長風退后,他看著躲在二人后的殷蕙道:“在下魏曕,燕王三子,可請二小姐移步說話?”
殷家的兩個護衛:……
對付過的浪子弟那麼多,眼前這個是份最尊貴的一個。
攔還是攔著,二人卻不約而同地看向殷蕙。
在這短短的功夫,殷蕙已經想了很多,不知道魏曕為何而來,可都不想多與其糾纏。
最好的辦法,就是裝作今日只是兩人的初次見面,他長得那麼冷,剛剛的震驚完全可以推被他嚇到了。
再聽魏曕自報份,殷蕙便裝作嚇得一晃。
殷家的兩個侍衛剛要下馬,魏曕已經跳了下來,一副要沖過來扶的架勢。
殷蕙晃了一下就穩住了,再居高臨下地看著魏曕,咬咬,質疑地問:“你說你是燕王三子,有何證據?”
好像有點怕,但眼神也有點兇,仿佛把他當謊報份的紈绔看。
魏曕抿,到底認不認得他?
心里這麼想,魏曕還是拿出了燕王府的腰牌。
殷蕙接過來,翻來覆去地看。
看過腰牌,再上下打量他一番,殷蕙好像終于信了,視線一轉,指著前面一條山間小路的路口道:“那邊清靜些,三爺有什麼想問的,去那邊說如何?”
魏曕地看著的臉:“好。”
殷蕙就先跑過去了,吩咐兩個護衛就在旁邊等著,不用跟著,也不用離開太遠。
說完,殷蕙騎馬拐進山間小路。
魏曕很快跟了進來,長風也留在了路口。
野樹叢生,拐進來幾丈之后,殷蕙下馬,站在一樹蔭下。
魏曕也跳下馬,朝走來。
沒等他靠近,殷蕙低頭行禮,忐忑地問:“三爺可是因為我拒婚而來?”
魏曕停步,看著道:“是,我誠心求娶,不知二小姐為何不嫁。”
殷蕙像普通的閨秀面對外男一樣,局促地攥著手:“祖父沒跟您說嗎?我不敢高攀。”
魏曕不信:“是不敢高攀,還是有人威脅你?”
殷蕙抬起頭,茫然地問:“威脅我?”
魏曕沒有回答,只審視地盯著的眼睛。
殷蕙仿佛被他嚇到一樣,轉過去,低聲道:“沒人威脅我,三爺乃人中龍,我只是鄉間野草,確實不敢高攀。”
魏曕看眼路口,忽然走過去,抓住的手腕。
殷蕙驚恐地看過來。
魏曕冷聲道:“你真的沒見過我?”
殷蕙連連搖頭,試著將手掙出來。
魏曕看著這張害怕的模樣,倘若不是跟了一路,倘若不是親眼見過面對紈绔子弟也從容不迫的淡然,魏曕可能真的要信了。
只需要再試探一句,就知道到底是十四歲的殷蕙,還是景和二年回來的殷蕙。
“你可否想過,你我都回來了,衡哥兒會如何?”
魏曕一手扣住的手腕,一手抬起的下,直視自己。
聽到“衡哥兒”的瞬間,殷蕙的掙扎頓住了。
這次重生,能彌補很多憾,唯一新生的憾,便是衡哥兒。
那是懷胎十月生下來的孩子,是魏曕冷冰冰待時在澄心堂最大的藉,雖然后來衡哥兒變了小冰塊,可衡哥兒也是孝敬的,只是不會再像小時候那麼依賴罷了。
十歲的衡哥兒脾氣像魏曕,模樣也像的。
再對上眼前這個十九歲的魏曕,殷蕙就好像看到了衡哥兒。
再也裝不下去,眼淚滾落。
那眼淚流到魏曕的手上。
魏曕猛地松開手,轉過去,面如冰霜,口因為憤怒而高高地起伏著。
殷蕙都能聽到他的氣聲。
親十年,他雖然幾乎每天都是因為生氣而沉著臉的樣子,卻從來沒有氣得如此失態過。
氣什麼?氣竟然敢拒婚?
多沒道理,不嫁,不正是全他與他的好表妹嗎?
冷靜下來,殷蕙掉因為想念兒子而落下的眼淚,等了會兒,見魏曕還在那里站著不,殷蕙想了想,走到飛絮邊,看著他道:“既然你我一樣,那回來就是回來了,過好眼下便是,以后三爺是三爺,我是我,你我互不相干,還請三爺別再過來……”
還沒說完,魏曕轉了過來,目如冰,又仿佛灼灼:“互不相干?親十年,我自認沒有苛待過你,何至于你連衡哥兒都不要了,也要拒絕這門婚事?”
虎毒尚不食子,那麼疼衡哥兒,竟能舍下衡哥兒而不嫁他,該對他有多恨?
魏曕不明白,他做了什麼,竟讓如此恨他!
換個時候,殷蕙一定會被這樣盛怒的魏曕嚇到,可魏曕那句“自認沒有苛待過”的話,竟把逗笑了。
迎著魏曕憤怒的目,殷蕙心里也燃起了一把火,一條一條地列舉起來:
“你是沒有苛待過我,你只是把我當個暖床的,除了夜里需要我伺候,你白日可與我多說一句話,我生病的時候,你可關心過我?”
“你是沒有苛待過我,你只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的家人,父王都陪郭夫人去過郭家,我是你的正妻,你可能連殷家大門在哪都不知道吧?”
“你是沒有苛待過我,你只是在心里藏了一個好表妹,只是在我傻乎乎地以為你會對我一心一意時,一聲招呼不打地就帶了個表妹回來,讓我被全府下人看笑話!”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魏曕,你凍了我十年,憑什麼還指我高高興興地嫁給你!”
明明很憤怒,殷蕙的臉上卻都是淚。
積了十年的委屈,終于有機會朝罪魁禍首道出來。
而魏曕的憤怒,則被的眼淚一滴滴澆滅。
他沒有只把當暖./床的,他把當妻子,當家人,夫妻倆再加上衡哥兒,是他最重要的家。
他沒有瞧不起,也沒有瞧不起的祖父,只是年輕時好面子,等他能夠從容時,殷墉不在了,他也沒有機會再陪回去。
這兩點可能不知道,有理由怨他,可他何時在心里藏了一個好表妹?
“阿蕙,我……”
“別這麼我,只有祖父可以,我跟三爺不!”
殷蕙發泄完了,抓住馬鞍就要上去。
魏曕幾步過來,在殷蕙抬的時候抓住,重新將人拉了下來。
殷蕙冷冷地瞪著他。
魏曕看著道:“別的你可以誤會,但我對表妹絕無私,納妾只是因為……”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狂妃來襲:丑顏王爺我要了
殺手之王穿越而來,怎可繼續受盡屈辱!皇帝賜婚又怎樣,生父算計姨娘庶妹心狠又怎樣?淪為丑顏王爺未婚妻,她嗤笑:“夫君如此美如天仙,不知世人是被豬油蒙了眼嗎?”“女人,嫁于我之后,你還以為有能力逃離我嗎?”…
89.5萬字8 120838 -
完結905 章

空間娘子要馭夫
二十一世紀神醫門后人穿越到一個架空的年代。剛來第一天被浸豬籠……沒關系,她裝神弄鬼嚇死他們……又被打暈喂狼?沒關系,她拉下一個倒霉蛋……只是,這個倒霉蛋貌似很有性格,白天奴役她,晚上壓榨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年翻身得解釋。雙寶萌娃出世…
127.8萬字8 22083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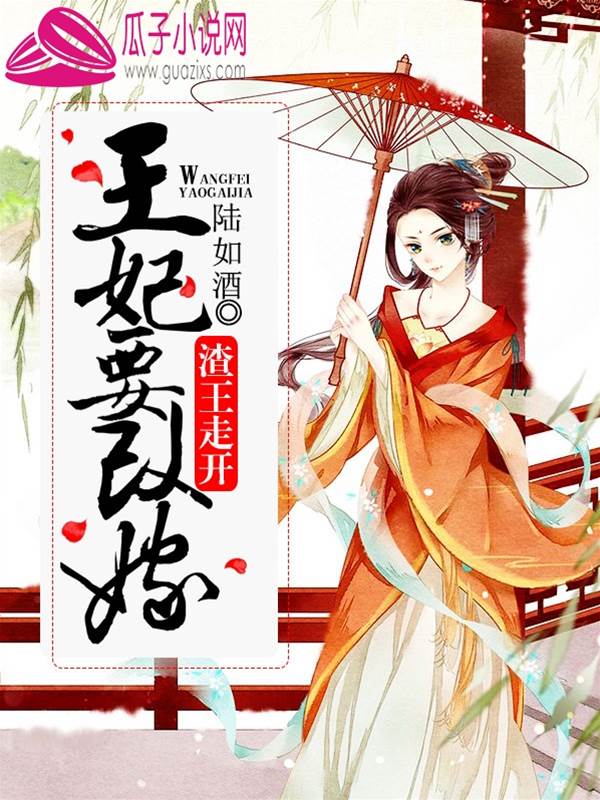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7 -
完結163 章

嫁三叔
顧長鈞發現,最近自家門口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年徘徊不去。一開始他以爲是政敵派來的細作。 後來,向來與他不對付的羅大將軍和昌平侯世子前後腳上門,給他作揖磕頭自稱“晚輩”,顧長鈞才恍然大悟。 原來後院住着的那個小姑娘,已經到了說親的年紀。 顧長鈞臉色黑沉,叫人喊了周鶯進來,想告誡她要安分守己別惹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卻在見到周鶯那瞬結巴了一下。 怎麼沒人告訴他,那個小哭包什麼時候出落得這般沉魚落雁了? 周鶯自幼失怙,被顧家收養後,纔算有個避風港。她使勁學習女紅廚藝,想討得顧家上下歡心,可不知爲何,那個便宜三叔總對她不假辭色。 直到有一天,三叔突然通知她:“收拾收拾,該成親了。” 周鶯愕然。 同時,她又聽說,三叔要娶三嬸了?不知是哪個倒黴蛋,要嫁給三叔那樣凶神惡煞的人。 後來,周鶯哭着發現,那個倒黴蛋就是她自己。 單純膽小小白兔女主vs陰晴不定蛇精病男主
25.4萬字8.18 163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