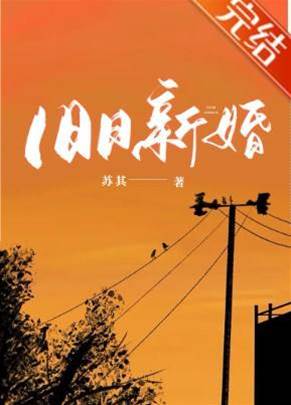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荒野植被》 61
說:“以免給他任何希。”
許言沒有回答,他清楚湯韻妍絕不是會夸大其詞的人,他在腦海里反復回憶早上和沈植對話時有什麼異常,但唯一能作為線索的只有最后那幾秒——沈植險些站不住的樣子,以及逃避對視的眼神。
熬了個通宵,許言凌晨五點才收工回家,他累得睜不開眼,洗完澡后倒頭就睡,按理說應該能睡得很香,但并沒有。這一覺不太安穩,做了些七八糟的夢,夢里的畫面斷斷續續,大學時寬闊的場,籃球場上蹦跶的球,樹影斑駁的一地落葉,取景里模糊的臉,只有那雙眼睛很清晰,墨黑的,過來。
他和那雙眼睛對視,很久,沈植的眼睛。
你要說什麼。許言想問他,他覺沈植有話要說,沈植卻始終沉默。
“不說就算了。”許言閉上眼。
“救我……”
低啞痛苦的嗓音,許言猛然睜眼,但已經不在夢里。
許言從床上坐起來,低著頭發呆,他昨天把話說得那麼重,歸結底是想法不夠堅定。心剛剛化一點,就被迫又僵起來,束得高高的,收,懸空,如此反復,太罪了。
但凡他真的可以對沈植做到視而不見心如止水,也不至于用再出國一次來做威脅。
聽起來很堅決,仔細一想就會發現里面包含了多心虛、搖、矛盾。
已經十二點了,吃過午飯就要去攝影展,許言發了會兒呆,起床洗漱。
出門前收到一條快遞短信,許言下樓去快遞柜取件,他不太清楚是什麼,拿到車上以后他把小小的快遞盒拆開,在氣泡的最里面,是一摞單反存卡和幾個U盤。
許言愣愣地看著那些東西,幾年前他剛和沈植分開,讓沈植把這些寄過來,但沈植說找不到了,結果今天它們卻毫無征兆地到了自己手上。
看了一眼發貨地址,是沈植的小區。
許言往后靠在椅背上,他很想問問,之前為什麼不給?找了三年才找到嗎?現在寄過來是什麼意思?
還想問問,為什麼你又進醫院了。
太久沒來這座城市了,攝影展結束后,許言跟朋友一起吃了晚飯,對方喜氣洋洋地給他看兩歲兒的萌照,許言一邊看一邊想到葉瑄也懷孕了,高興的。
吃完飯又坐著聊了很久,出餐廳時已經是十點多,許言跟朋友道了別,上車。這塊地方他很,是離沈植家最近的大商圈,到了街盡頭,右轉,過一條江大橋,再開幾里路,是個公園,繞過公園就是沈植的小區。
許言以前出來買夜宵,開到橋上時總要降下車窗,吹晚風,看燈火,聽船笛。他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沈植能跟他出門買東西就好了,風景這麼棒,一起看看。
沿著大道開到盡頭,右轉,許言看著前路,筆直往前開是江大橋,走右行道會進快速路。如果要回家,他應該變車道走快速路,接著上高速。
許言握著方向盤,前方大橋上燈灼灼,無數車流匯,開向橋的那一端。
該變車道去快速路了,但許言遲遲沒有打轉向燈。岔道口的那塊藍指示牌很顯眼,白字反著,指示直行或右行,越來越近,離必須變道的終點也越來越近。
還剩七米。
“沈植進醫院了。”
還剩六米。
“不清楚,但應該不是小病。”
五米。
“我記得明天下去你會去那邊參加攝影展,要是有空,可以順便去看看他。”
四米。
“當然,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完全不關心,那還是別去吧。”
三米。
“以免給他任何希。”
兩米。
“救我……”
許言的心重重一跳,深吸口氣,維持直行路線,朝大橋開去。
橋上風景依舊,許言有點恍惚。下橋后開過公園,車在小區門口被攔住,門衛過來敲窗,許言懷疑自己進不去了,但門衛仔細看他幾眼,笑起來:“許先生?”
許言才發現保安沒換人,不嘆對方的記憶力。他點點頭:“好久不見。”
他被下車做人臉識別——通過。沈植一直沒讓人刪掉許言的信息,他依然可以自由進出小區。
車緩緩停在路邊,許言轉頭看著房子,里面一片漆黑,不知道沈植在不在家。
許言下了車,推開圍欄門,那棵白玉蘭比以前高了。他走到大門前,應燈亮起,許言盯著電子鎖,抬手,食指指腹按上去,嘀哩哩幾聲,門打開了。
門外的燈照亮玄關,也約約照亮客廳其他地方,總還是看不太清。但許言有種很怪異的覺,這種覺從房子的各個角落里一點點向他聚集,像來的藤蔓,纏住他的腳腕。
作者有話說:
后天更
第54章
你走的時候,就算沒有刻意去記離開時房子里是什麼模樣,但無論時隔多久再歸來,都會看出變化,因為日常的記憶已經習慣地刻在腦子里。
同樣的,當它完全沒有任何改變,你也能瞬間察覺。因為眼前的場景會和記憶中的畫面無重合,清楚告知你這里還是原來的樣子。
就比如許言從腳下的玄關,到開燈之后整個明亮的客廳,看過去,如果不是這幾年的記憶還在,他會懷疑自己本就是才剛離開了一兩天,甚至再短一點——一頓晚飯的工夫。
窗簾、沙發、地毯、壁畫、茶,玄關的拖鞋、靠枕的數量、茶幾上的雜志、懶人沙發里的遙控、垃圾桶和落地燈擺放的位置……許言在客廳里走了一圈,開始變得不能置信——眼前的一切,它們的樣式、數量、位置,跟三年前他離開時都一模一樣分毫不差,幾乎讓他錯以為這棟房子幾年間都沒住過人,所以才能一直維持原樣。但它干凈整潔,垃圾桶里有幾個紙團,玻璃茶壺里盛著半壺白開水,勉強可以作為有人居住的證明。
餐廳也是,廚房也是。許言站在冰箱前,看著門上的冰箱,有幾個是他旅游帶回來的,有幾個是網上刷到覺得喜歡買的,看起來舊了些,但一個不。冰箱右門上的留言板也還在,寫著“記得喝酸!”,左下角畫了個丑丑的笑臉,都出自許言之手。
以前沈植覺得許言畫得丑,總會手把那個笑臉抹掉,他抹一次,許言就重新畫一次,堅持不懈,百折不撓。
許言在冰箱前站著,站到都酸了,麻了。他轉上樓梯,到主臥門前,不知道沈植在不在里面,許言敲了敲門。
沒回應,許言打開門,房間里漆黑一片,只有臺燈亮著,他徑直走過去,臺的茶幾上歪著幾個空酒瓶,風一吹就酒氣陣陣,只是沒見到人。許言回頭看,床上是空的,但約可以看見左邊枕頭上有個黑乎乎的東西。
心跳不控地快起來、重起來,許言手到開關,視野驟然明亮的那刻,他看著那只墨綠的小鱷魚,覺有一雙手狠狠按在肩上,異常沉重的力道,將他整個人向下,讓他不能彈。
很久以后,許言的目才艱難移開,床頭柜放著他以前常用的水杯,那本沒看完的書倒扣著,許言還記得是看到第157頁——之所以記得,是因為沈植曾經隨口問了他一句看到哪里了。
許言走到床邊,拿起小鱷魚了,是原來那只,很,丑丑的,肚子底下有點線,小小的破口里可以塞進一/手指頭。
他看得出神,忽聽見帽間里傳來一聲很輕的悶響,許言放下小鱷魚走過去,打開燈。往里走,還是一左一右兩個大大的柜,沈植的柜關著,但許言的柜是開的,里面的壁燈亮著,懸掛的服被全部推到一頭,留下半個柜子的空間。
許言停下腳步,站在那里,一不,他的表變得茫然和震驚,微微睜大雙眼。
柜子里掛的依然是他從前的服,而沈植正蜷在空出的那一半位置里,膝蓋曲起,頭歪著抵住柜板。從許言的角度看過去,他的側臉、耳朵、脖頸都是紅的,顯然已經喝了太多酒。他懷里還抱著一件灰衛——許言的。
猜你喜歡
-
連載1471 章
盛少,情深不晚
年輕幼稚的周沫被爸爸算計,稀裡糊塗睡了高冷男神盛南平,陰差陽錯生了兒子。 盛南平恨透周沫 三年後,為了救兒子,他必須和周沫再生一個孩子。 周沫是有些怕盛南平的,婚後,她發現盛南平更可怕。 “你,你要乾什麼?” “乾該乾的事兒,當年你費儘心機爬上我的床,為的不就是今天?” “……” 傳聞,京都財神爺盛南平是禁慾係男神,周沫表示,騙人滴! 終於熬到協議到期,周沫爆發:“我要離婚!我要翻身!” 但盛南平是什麼人,他能把你寵上天,也能殺你不眨眼......
357.7萬字8 15379 -
完結1203 章

五年後,龍鳳雙寶攜她炸了大佬集團
夏梵音被繼妹陷害懷孕,被迫假死逃出國。 五年後,她帶著萌寶們回國複仇,竟意外收穫了個模範老公。 安城裡的人都知道紀三爺性情殘暴冷血,可卻日日苦纏全城知名的“狐貍精”。 夏梵音掙紮:“三爺,麻煩你自重!” 紀爵寒抱起龍鳳胎:“孩子都生了,你說什麼自重?”
214萬字8.18 87494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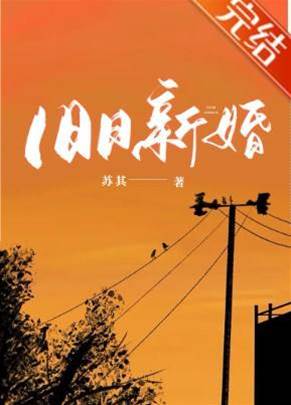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276 -
連載959 章

賀總夫人又來蹭氣運了
姜糖天生缺錢命,被師父哄下山找有緣人。 本以為是個騙局,沒想到一下山就遇到了個金大腿,站他旁邊功德就蹭蹭漲,拉一下手功德翻倍,能花的錢也越來越多,姜糖立馬決定,賴上他不走了! 眾人發現,冷漠無情的賀三爺身邊忽然出現了一個軟乎乎的小姑娘,會算命畫符看風水,最重要的是,總是對賀三爺動手動腳,誰不知道賀三爺不近女色啊,正當眾人等著她手被折斷的時候,卻見賀三爺溫柔地牽住她的手。 “嫁給我,讓你蹭一輩子氣運。”
174.2萬字8.18 12970 -
連載317 章

避孕失敗!沈小姐帶崽獨美,厲總慌了
十年深愛,四年婚姻,沈瀟瀟畫地為牢,將自己困死其中,哪怕他恨她,她也甘之如飴。直到一場綁架案中,他在白月光和懷孕的她之間選擇放棄她,間接害得父親離世。她終於心死,起訴離婚,遠走國外。三年後再見,她攜夫帶子歸國。厲行淵將她困在身下,“沈瀟瀟,誰準你嫁給別人的?”沈瀟瀟嬌笑,“厲先生,一個合格的前夫應該像死了一樣,嗯?”男人眼眶猩紅,嗓音顫抖,“瀟瀟,我錯了,求你,你再看看我……”
53.8萬字8.18 501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