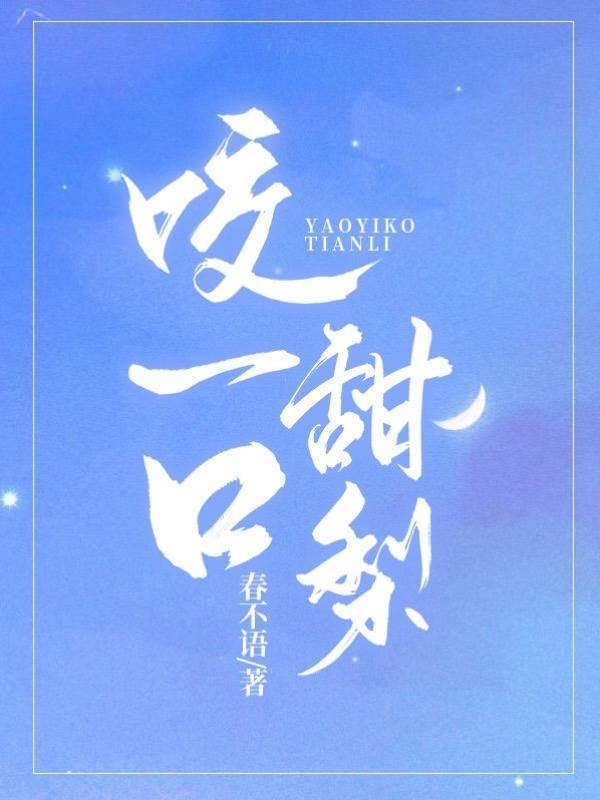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你說巧不巧》 第49章 第 49 章
于是,他們倆開始不死心地去摳門、找東西撬門、扣鎖眼,卻毫無用,被封死的大門本打不開。
希變絕,失敗了一次又一次之后,倆人漸漸死了心。
這就是一間被封死的室,本逃不出去,門外還守著持槍歹徒,隨時會沖進來要了他們的命。
顧別冬長嘆一口氣,一屁坐在了后方的冰柜上。許詞話面無表地盯著面前的大門,不甘心又無可奈何。
顧別冬苦笑一下:“許個愿吧,這門要是能自彈開,從今往后我必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爭當年級第一。”
話音剛落,“咔嚓”一聲,門彈開了……
顧別冬瞬間傻了:“我艸?!”
許詞話也傻了,呆若木地盯著眼前的大門。
幾分鐘前,顧祈舟盯監控的時候突然捕捉到了一個細節:飯店倉庫的位置恰好和樓上書店的安全通道的位置重疊。于是他立即把飯店負責人和書店老板一起喊上了車,詢問他們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原來這棟小樓在十幾年前同屬于一個業老板,起初開的是一家出版社,但由于經營不善倒閉了,于是就拆分賣出了,但是防煙樓梯間還是連在一起的——通往二樓書店的樓梯間就是曾經的防煙樓梯間。
后來華明飯店開業,把通往樓梯間的安全通道改了倉庫,但是門卻沒拆,從部堵死后上了壁紙,外部則是直接用石膏板擋上了,刷完漆后看起來和旁邊的實墻無二,站在樓梯間里本開不出來這兒原來有扇門,而且這事兒已經過去好多年了,若非顧祈舟問起,飯店和書店的老板都快忘了這事兒了。
得知況后,顧祈舟立即安排人手去破門。
昆鳴帶著一隊特警隊員過去了,拆了石膏板后,一位負責破門的隊員用靜態破門破開了沉重的、銹跡斑斑的安全通道大門,昆鳴立即帶著人手沖了進去。
顧別冬和許詞話兩臉懵地盯著突然沖進來的特警隊員們,覺好像在做夢——門兒竟然真的彈開了,比爬通風管道還離譜的想法,竟然真了?天、天無絕人之路!
昆鳴也驚訝的,沒想到他們倆竟然這麼機靈,竟然還能發現這兒有扇門,連壁紙都給撕了,但他也沒時間夸獎他倆了,因為還有一個人質尚未被解救出來,立即讓其他隊員帶著他們倆安全撤離,然后帶著其余的人手沖進了倉庫,在通往飯店過道的門前站定后,他一手持槍,一手扶住了通訊對講耳麥,小聲匯報:“B組就緒。”
顧祈舟將隊伍分了ABC三組,C組守后門,以防歹徒逃;B組破倉庫門;A組守前門。
當B組的營救行功后,A組就從前門強攻。
顧祈舟加了A組,親自帶隊守在飯店門前,等待著強攻時機。
林毅在指揮車中看監控,昆鳴匯報完畢,林毅的嗓音在通訊耳麥中響起:“大廳中的兩位劫匪還在爭執,人質在柜臺后,可以進攻。”
王偉山不放心人質在黃手中,擔心他這個瘋子會殺了人質害死大家,黃則擔心王偉山會臨陣倒戈,兩人爭執了一會兒,最終達了共識,把陳染音綁起了起來,扔在了柜臺下面,黃站在邊看守——不看守他也不害怕,因為他已經給上了炸/彈,誰也救不了。這娘們兒,今天,必須死!
但是王偉山還是有“想要全而退”的念頭,畢竟,他和那個姓趙的不一樣,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本錢拿回來,沒想真的玩命兒,誰能還他錢他就聽誰的話。黃看出了他的搖,既憤恨又惱怒,覺王偉山就是個傻廢,很想一槍把他崩了,但是他現在又需要王偉山的幫助,更何況旁邊還有個虎視眈眈的王長河,一對二他沒有勝算。
所以兩人一直在爭執不休。
顧祈舟看向了站在他對面的吳鏘,對著耳麥,一聲令下:“進攻!”
吳鏘迅速拉來了大門,開簾布的同時,猛然甩手臂,將閃/彈丟了進去。
大廳瞬間暴起了強烈的閃,同時發出了巨大分貝的噪音。
王偉山和黃同時到了巨大的沖擊,無論是視覺還是聽覺都出現了暫時障礙。
顧祈舟立即帶人沖了進去。
王長河站在過道,閃/彈對他的視覺沖擊不大,卻對聽覺造了障礙,但他的反應還是很快,準備去挾持倉庫的人質,迅速去拉倉庫門,然而門卻忽然用力地撞向了他。
在A組行的同時,B組也開始了行:直接用破門錘撞門——特警隊破門的工有很多種,使用哪一種要看況——倉庫門恰巧是外開式,破門錘更合適。
王長河直接被撞了出去,手中的槍都被撞掉了,昆鳴帶著人從倉庫沖了出來,立即捕捉了王長河,并收繳了他的武。
大廳,王偉山在閃暴起的那一刻就知道敗局已定,立即扔掉了手中的槍,抱著頭蹲在了地上。黃卻瘋得很,自知必死無疑,但就算是死了也要拉幾個警察陪葬,所以即便是視聽到了障礙,他還是舉起了槍,瘋狂扣扳機,閉著眼睛沖著大廳無差別掃,打死一個警察是一個。
顧祈舟帶隊沖在最前方,果斷舉槍擊,正中眉心。
黃的一僵,無力地倒在了地上,臉上卻掛著一抹瘋狂又詭異的笑容。
吳鏘帶人逮捕王偉山的同時,顧祈舟沖到了柜臺后,把陳染音從地上扶了起來。
陳染音的手腳手被纏上了黃的膠帶,上也被纏了膠帶。
顧祈舟立即把在上的膠帶撕掉了,又冷靜迅速地拿出了隨匕首,隔斷了纏在手腕和腳腕上的腳步。
陳染音坐在地上,雙目通紅,淚眼模糊地著他,雖然不舍得、不甘心,有千言萬語想對他說,但最終說出口的卻是:“你快走吧!你快走!我上有炸彈!快炸了!”
的嗓音嗚咽又絕。
顧祈舟渾一僵。
陳染音哭著出了右手,撕掉了纏在手腕上的黃腳步,手腕式的定時炸彈已經啟,剩余時間九分二十四秒。
顧祈舟突然抬起了頭,頸部青筋暴起,厲聲大喝:“周海!排!排!”
周海,特警隊的專業排手。
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流失著,陳染音本不確定自己的生命還能不能延續十分鐘,舍不得顧祈舟,卻又不想讓他陪著一起死。
他的人生已經夠苦了,想讓他好好活下去,平安又燦爛地活下去。
“你快走吧……”哭著去推他,用力地推搡著他的肩膀,“別管我了!別管我了!”
顧祈舟置若罔聞,單膝跪地,攥著的手,目不轉睛地看著,神極為堅毅:“我陪你,不管發生什麼,我都會一直陪著你。”
其實有他這句話就夠了,死也滿足了。
但是現在,真的不需要他陪了……只想讓他好好活著。
“我、我不需要你陪!我不需要!”陳染音竭力抑著哽咽,不容置疑地對他說,“現在就滾蛋!滾蛋!我不想再看見你了!”
顧祈舟的頭一哽,嗓音開始嘶啞,態度卻無比堅決:“我不走!”
陳染音哭著搖頭:“不行!不行!你還有冬子!你必須走!”
“顧隊!”周海穿著防服趕來了,他把工箱放在了地上,然后對顧祈舟說,“您現在必須立即撤退。”
顧祈舟知道這是規定,但他做不到,無論如何也做不到。
許支帶著林毅走了過來,神嚴厲厲聲呵斥:“顧祈舟!撤離!”又低聲提醒:“督查也在,你剛才開槍了,在這兒停留時間越長對你越不利!”
顧祈舟卻無于衷,甚至可以說是執拗,他所有的理智和克制都盡數喪失了……他已經失去了所有,不能再失去了。
林毅盯著他,很冷靜地對他說:“你留下沒有任何用,只會影響周海的分析和判斷。”
仿若一頭被了絕境的困,顧祈舟紅了眼眶,萬般無奈地閉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氣,又長長地吐了出來,睜開眼睛后,對陳染音說了一句:“我在門外等你。”他努力地讓自己的語氣變得輕松、鎮定,嗓音卻無比嘶啞。
他明白自己必須撤離。
不然只會害死。
陳染音長舒了一口氣,含著眼淚,笑著點頭:“好呀!”
顧祈舟咬著牙從地上站了起來,紅著眼,深深地看了一眼,轉離開了。
但是他后悔了,特別后悔,后悔自己推開了。
他想和在一起,這輩子再也不分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2724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4802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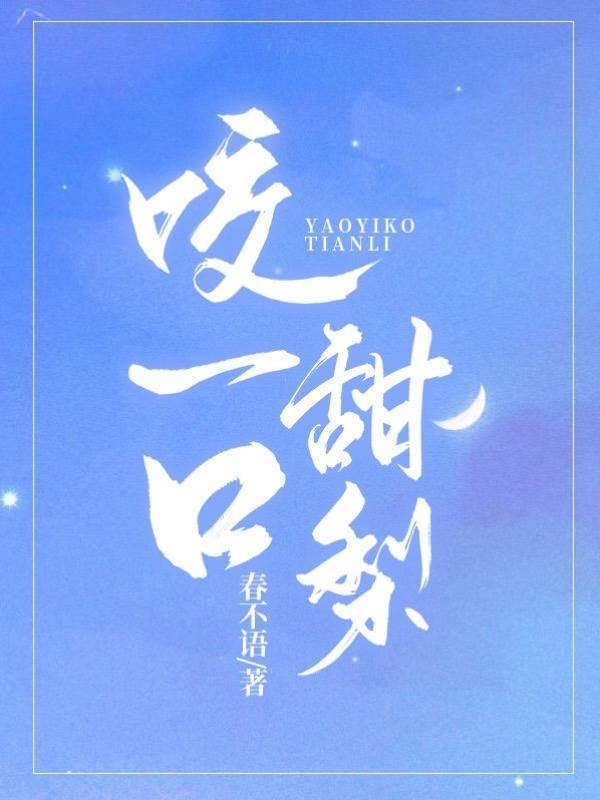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