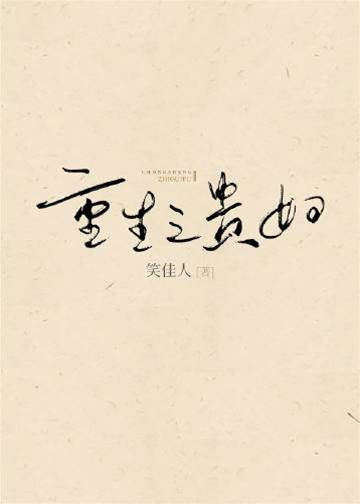《榜下貴婿》 第87章 躲避
屋里的說話聲漸漸消失, 燭一暗,陸徜和宋清沼似乎已經談妥,陸徜送宋清沼離開,人去屋空。
天上一皎皎明月, 照出呆滯的人, 明舒仍舊站在原地。
也不知過了多久, 才從震驚中回神, 頭頂的雷就又捶到心上,整顆心不控制地劇烈跳, 幾乎要撕出腔。這滋味, 猶勝第一次瞧見宋清沼, 將他視作夢中人。
腦中極,一時間竟不知是去問陸徜關于自己的世,還是當作什麼也不知道繼續與他兄妹相待,又恐陸徜回來發現自己聽墻角,于是勉強拔悄悄往外走去。
待走出十多步, 回到廊下, 已經無被發現的風險, 明舒方又放緩步伐, 孤魂野鬼般沿著長廊往前走。
可能剛才的焦雷太厲害,打得魂魄出逃吧。
這半年多來,一直將陸徜視如長兄般敬重戴, 雖然也有小兒的撒討好時刻,二人之間親厚非常,卻從沒往別去想,從兄妹到男,這其中隔著天塹。
腦中閃過凌畫面, 一會是今夜州橋夜市上,陸徜以指腹拭過瓣的景,一會又是兩人分食,共吃一份小點的景,一會是替陸徜整襟束帶、敷簪花,一會又是早前二人共馬,一會又化急病之時他守在床畔……
這點點滴滴,如春雨綿綿,潤無聲。
猛地搖晃腦袋,將這些畫面從腦中搖走,又想自己的過去。
既然非親兄妹,那又是誰?是曾氏從小收養的孤兒?還是半道救下的弱?按照他們對的悉,他們與必定認識了很久,可他們對的世卻絕口不提,哪怕被陸文瀚誤會,也不肯說出實,這其中定有別。
疑慮重重,仿佛回到剛醒轉之時。但矛盾的是,這半年多的相,曾氏的疼、陸徜的為人,他們是好是壞心中有數,若說他們對存有歹念,是不信的,可他們又瞞了什麼事?
明舒想找陸徜問清楚,可又不愿面對他,不想揭破這層紗。
好好的兄妹,突然變……世俗男,這樣的轉變太突然,接不了。
無數的念頭充斥在腦中,鬧得額頭又約作疼。
“明舒?”
陸徜的聲音響在后,震醒,腦中各中雜念轟地消散。
“不是讓你回去歇息,你怎還在外頭?”陸徜送完宋清沼回來,打算去后院找曾氏,半道看到夢游般的明舒。
明舒霍地轉頭,果然瞧見提著燈籠的陸徜,他波瀾不驚的模樣與先前一般無二,聽到的那些話,就不像他這中人會說的。但他就是說了,不是的錯覺,也不是在做夢。
荒謬的現實,比夢更嚇人。
“屋里悶,我出來走走,這就回。”道。
“你臉不太好,不舒服?”陸徜瞧臉不好,上前兩步,提燈又照。
燈火晃眼,明舒微撇開頭,只道:“有些頭疼,沒事。”
“頭疼?”陸徜手,探額頭。
明舒驚退了一大步,避開他的手:“可能吹了點風,無礙。我先回房了。”
“我送你……”陸徜見沒有提燈,便想送回去。
“不用,我自己回就,你忙你的吧。”明舒拒絕了他,轉飛快跑走。
陸徜來不及多說話,就見的影消失在長廊盡頭。
————
陸徜很快就發現了,明舒在躲他。
滿堂輝開鋪之后,明舒每天早上都要去鋪,而他也要往開封府衙點卯,所以二人早上常常是一起出門,陸徜會把先送到滿堂輝所在的街道外,再去開封府衙,到了傍晚,倘若衙門沒有什麼公務,他會親自來滿堂輝接明舒。
有時,他到的時候,滿堂輝還很忙,明舒不得,他就會在堂小坐片刻,喝上兩盞茶等;又或者,他公務繁忙難以早歸,明舒也會留在鋪多忙段時間等他過來,再一起回家;偶爾,兩人也會相約去汴京城游玩、下館子,把先前沒來得及游覽的風景都一一補起來,譬如州橋夜市。
滿堂輝的伙計和明舒的閨中友都說從沒見過這麼深的兄妹,那時明舒可是極其得意地挽著他的手,臉上全是炫耀的神。
日子平順,各自忙碌,也彼此陪伴,陸徜所有說不能的心思,便都釀進這日復一日的尋常生活之中。
然而有一天,明舒變了。
不再和他一起出門,也不再與他一起歸來。早起之時,明舒已經先一步出門,夜歸之時,明舒卻更早回家,然后躲在房中閉門不出。他連最常見的,的笑容,也很難看到,在宅中偶爾上,還沒待說上兩句話,就匆匆走了。
這一反常態的況,讓陸徜心生焦躁。
————
明舒已經躲了陸徜三天。
不知要如何面對他,索遠遠避開,待心平靜后再做打算。
如今心暫時不跳了,頭頂雷也不打了,緒也有所回轉,漸漸冷靜,只是還有些心不在焉。
“掌柜的?掌柜的?”伙計連喚了幾聲,才把明舒的魂神喚回來。
“怎麼了?”明舒此時才發現,自己坐在案前已經發了好一陣子的呆。
“國公府世子夫人來了。”
“什麼?”明舒霍地站起,“許姨來了?”
邊說邊往外走去,掀開珠簾一看,果然看到許氏正站在堂中欣賞曾氏的繡屏,兩步上前,一邊命伙伴倒茶,一邊又向許氏道:“這大熱的天,許姨怎麼親自過來了?”
許氏仍是老作派,端著架子,不過在明舒看來,這點架子又著可。
“這街上開了家新的綢緞莊,我在家呆得煩悶,所以出來逛逛,順路來你這里,正好瞧瞧有沒新鮮花樣。”
“我這幾天正整樣品與圖樣,正準備送到府里給許姨挑選,沒想到你親自來了。”明舒揚起笑臉,把許氏往堂迎去。
一時間伙計倒來茶水,又把樣品送進來,明舒親自拿了圖樣給許氏瞧。許氏看了一圈,樣品都是舊的,并沒看中,倒是在圖樣里挑了兩件新款。
“許姨好眼,這兩件……工藝復雜,還在嘗試階段,也沒辦法大量定制,本不開放預定。不過許姨喜歡,我自然先著你,等樣貨出來,我先拿到府上給你過目。”明舒笑道。
許氏聞言心愉悅,將圖樣遞回給,又談起另一樁事。
“昨日你托人送到我家里的舊……”揮揮手,丫鬟就將木匣捧到桌上。
明舒認出,那是裝有柳婉兒長命鎖與帕的木匣。四天時間,聞安與殷淑君都已回復,家中無人識得此,相的幾家也不清楚來歷,明舒最后才送去宋府,讓許氏看的。
比起郡王妃和殷夫人,許氏猶際,的見識強于二人。
“許姨可是認出這兩樣舊?”明舒按著匣子問道。
許氏點點頭,卻又不是很肯定道:“那中款式的長命鎖,汴京到可見,我認不出,不過那方帕,我倒是見過。”
似曾相識的帕子,也是想了許久才約記起來的。
“那個‘蕙’字,我在工部尚書的夫人……就是盧家三娘子的母親馮蕙手上見到過,的閨名就是一個‘蕙’字。”許氏道。
明舒一怔。
“盧三娘子和母親馮夫人,你也見過的,那日你們還鬧了不愉快。你手上怎會有馮夫人的舊?”許氏反問。
明舒也很驚訝,只道:“這是有人給我代為查找原主的。”又問,“許姨,你可知馮夫人或者說盧家早年有沒丟失過孩子?大約十六、七年前。”
許氏蹙起眉頭:“十六、七年前?那我可記不清,不過印象中一直沒聽說盧家丟過孩子……誒,不對,是有那麼一樁舊案,大約十七年前,盧家發生過一件嬰兒被盜的案子,聽說是在嬰兒剛滿月沒多久時,娘抱著孩子出門,結果半路被拐子盜走了孩子。不過那伙拐子好像半年后被抓捕歸案,那孩子也找了回來。”
“不知那孩子是盧府的哪位……”明舒問到一半,忽然想起柳婉兒的年紀恰與盧三一樣,“是盧三娘子,盧瑞珊?”
“正是。”
————
送走許氏后,明舒獨自己在后堂,對著那木匣坐了半晌。
柳婉兒付的東西,來歷是找到了,可又陷新的謎團中。明舒拿不準主意是將這個結果告訴柳婉兒,還是再查清楚些……
最近的煩心事有些多,夜里難寐,白天神便不濟,到了近午時分尤其困倦,想著想著就不知不覺睡過去,及至醒來時,已是傍晚。
眼,忽然驚起。
時辰似乎不早,得收拾東西回家,否則又要撞上陸徜。
如此想著,飛快來伙計,代好當日之事后便匆匆離開,豈料人才走到鋪門口,就聽鈴鐺一聲響,陸徜出現在門前。
兩人面對面,撞個正著。
明舒一僵,瞅著外頭天尚早,還沒到陸徜下值時間。
“今日公務不多,我告了一會假,先回來。”陸徜看穿的疑,解釋道。
他是專程來逮人的。
“回家?”見不語,他問道。
剛想搖頭,陸徜一語封住退路:“我聽到你和伙計告辭要回家。”
“……”明舒有些恨恨地呼口氣——這人能不能別這麼了解?
陸徜不著痕跡笑笑:“走吧,一起。”
夏日傍晚,暑氣未散。明舒跟在陸徜畔,往街巷口走去,夕余暉還在,明舒走在路旁房檐的影里,陸徜在外,大半個子都落在中,影在地上拖得老長。
平時都是明舒嘰嘰喳喳說笑,但今日,一聲不吭,反而是陸徜主開口,問起近日況,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心思已經飛到天外。
就這般走了一段路,有兩個追打嬉鬧的孩從巷旁的胡同里突然竄出,險些撞到明舒。
“小心!”陸徜拉住的手往邊一扯。
明舒躲過了兩個孩子,挨在陸徜側,手被他握掌心,如被蜂蜇般飛快甩開他的手,迅速退離兩步。
就這兩個舉,點燃陸徜了三天的焦躁郁悶。
明舒還要往前走,他已一臂橫來,撐于墻上,攔住的去路。
“陸明舒,到底發生了何事?你為何……避我如蛇蝎?”
明舒用力咬了下瓣,不能再這麼躲下去了。
“你不是我阿兄,對嗎?”
陸徜聽到緩慢且不似往常清脆的沉音,心間劇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鳳隱天下
洞房夜,新婚夫君一杯合巹毒酒將她放倒,一封休書讓她成為棄婦!為了保住那個才色雙絕的女子,她被拋棄被利用!可馳騁沙場多年的銀麵修羅,卻不是個任人擺布的柔弱女子。麵對一場場迫害,她劫刑場、隱身份、謀戰場、巧入宮,踩著刀尖在各種勢力間周旋。飄搖江山,亂世棋局,且看她在這一盤亂局中,如何紅顏一怒,權傾天下!
17.9萬字8 43254 -
完結418 章
鳳逆九天:一品毒妃傾天下
她是將軍府的嫡女,一無是處,臭名昭著,還囂張跋扈。被陷害落水後人人拍手稱快,在淹死之際,卻巧遇現代毒醫魂穿而來的她。僥倖不死後是驚艷的蛻變!什麼渣姨娘、渣庶妹、渣未婚夫,誰敢動她半分?她必三倍奉還。仇家惹上門想玩暗殺?一根繡花針讓對方有臉出世,沒臉活!鄰國最惡名昭著的鬼麵太子,傳聞他其醜無比,暴虐無能,終日以麵具示人,然他卻護她周全,授她功法,想方設法與她接近。她忍無可忍要他滾蛋,他卻撇撇唇,道:“不如你我二人雙臭合璧,你看如何?”【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109.7萬字8 73395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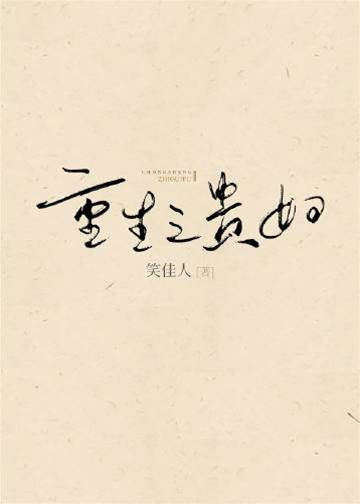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2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