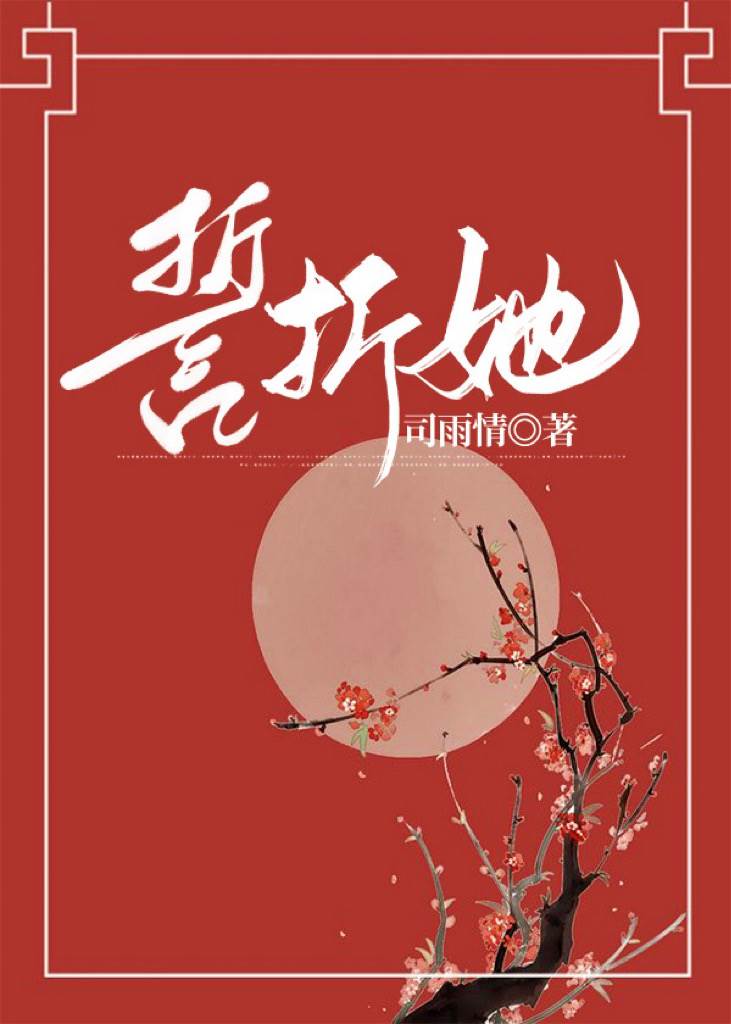《榜下貴婿》 第110章 唐離之死記憶恢復前夕。
明舒沒想到自己與陸文瀚談完出來時,曹海竟還在花廳里等著。
“我瞧你著急,怕你要事,索就在這等著。”曹海已經在陸府喝了半天茶,見到明舒就如獲大赦般站起。
明舒亦很驚訝,不好意思道:“在抱歉,耽誤曹將軍了。”
“不礙事,要不是你,我也沒機會進這尚書令的府邸。你還要去哪里?我再送你程吧。”曹海咧笑起,問道。
“大相國寺。”
這次,是真的要去大相國寺。
雖然不知道唐離究竟意何為,但明舒心里非常強烈的不祥預,這次的盂蘭盆節法會,不會太平。
新坐曹海的馬車,聽著曹海在外頭喝了聲:“走。”馬車了起來,由緩至快,明舒的心也越發沉甸。
其實說起來,三皇子登禪臺與柳婉兒辦普渡會,這二者間,雖然像是兩件毫無相關的事,但仔細琢磨便能品出其中的巧妙關系。
如果沒有三皇子登禪臺,柳婉兒的普渡會不會順利進行,而豫王如果目標只在三皇子上,唐離又何必大費周折促普渡會?若只是想借工部尚書之名在法會中手腳,那已經功把柳婉兒送進盧家,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如果三皇子在法會出事,盧則剛做為督建法會的負責人,必罰,此局已經是一箭雙雕,不僅助力豫王,還能復仇盧則剛。
那……如此盛大的普渡會又是為了什麼?
總不可能在事之后柳婉兒還打算留在盧家扮演盧三,繼續博取好名聲……盧家都要倒臺了,這太說不通。
————
就在明舒忘我的沉思中,馬車漸漸停下,外頭曹海道了聲:“陸娘子,到了。”明舒方醒神下馬車。
因著這場盛大的法會,大相國寺附近的三條主街巷都被封鎖,不論是達貴族還是平民百姓,都只能步行,盡管天漸漸暗下來,但街往來的百姓依舊非常多,街道兩邊掛的燈籠也已亮起,整條街璀璨如晝。
“陸娘子,可有需要幫忙之。”曹海見神急切,便主開口。
明舒怕大事發生,倒是想借曹海之力,人多點好辦事,可沒憑沒據,也不知道法會發生什麼事,無法對曹海解釋,只能道:“能勞煩曹將軍陪我走一遭嗎?”
“,沒問題。”曹海倒是爽快,召喚了屬下陪著一道往寺門走去。
“曹將軍,今日您的副沒跟著您?”路上,明舒問了句。
“那小子不耐煩看這娘們兒的熱鬧,我就讓他自己找樂子去了。”曹海隨口回道,又覺這“娘們兒”好像罵到明舒頭上,故又抱歉道,“不是說你。”
明舒也只是隨口問問,并沒在意他問什麼。
連著魏卓安排保護明舒的人在,行十數人浩浩走到了大相國寺山門外。寺已經是燈火輝煌,除了高懸的燈籠外,還熊熊燃燒的篝火,濃烈的檀香味伴著焚燒紙的氣息,彌漫在偌大寺院中。
明舒站在山門外,就能嗅到那談不是香還是刺鼻的氣味。
寺廟之中已是經幡遍掛,各寶殿燭火熠熠,哪怕天已晚,仍舊香客攢,寺院里也隨可見負責守衛的軍影,寺院的大雄寶殿外更已拉起明黃帷幔,每隔五步便設一個衛軍,防之就是高筑的禪臺,法壇設在禪臺之下,百名僧人圍坐禪臺誦經不斷。
帷幔景外人難以窺探,只有禪臺高聳,遠可見。仿七層浮屠的高臺,四周包裹著經幡,臺上似乎人坐著,只是隔太遠,天又黑了,看不清那人是何模樣。
但資格登上禪臺的,只有三皇子趙景然一人。
————
明舒隔遠遠看了幾眼,法壇四周戒備森嚴,魏卓親自帶著把守,進其中的僧人也經層層篩查,而禪臺又建這麼高,比四周建筑都要高出許多,附近不可能安弓、弩手行刺,安全上應該無虞,明舒定定心,問明普渡會所在后,匆匆趕去。
因為要派米派粥,寺院安排了西側禪院與廂房給柳婉兒與各府夫人娘子,既設棚贈粥,又供眷們休憩。明舒沿路跑去,都能看到從西禪院出來的與正要趕去的百姓。
從西禪院出來的百姓除了能領到一碗平安粥外,還能拿到一袋平安米,除此之外,還孔明燈。
“阿娘,什麼時候能放燈?”路上,個小男孩抱著孔明燈問母親。
他母親他的頭:“要到前頭的放生池,再過會就能放了。”
小男孩高興極了:“我在上面寫了保佑父親母親大人安康!”
“乖。”他母親溫笑,牽起他的手要走。
“這位娘子,請問他手中的孔明燈是在哪里領的?”明舒前問道。
“今晚放孔明燈的祈福儀式,盧家的粥棚那里可領,不過限九十九盞,現下恐怕已經派完了。到前頭的放生池集中后,再起放燈,娘子若是喜歡,可以前去觀看。”那母親回答完明舒,拉著兒子離開。
明舒看著兩人背影遲疑了片刻,問曹海:“曹將軍,您可知今日刮什麼風?”
“這我倒是沒留意……”曹海邊說邊站在原地,帶兵行軍之人,對風勢自有些研究,加之山中風略大,片刻后他就又道,“大約是西北向的風。”
西北向……風往西禪院附近刮。
是多心了嗎?
明舒搖搖頭,又朝西禪院跑去,沒幾步就到禪院外。
派發米粥等的棚子都搭在禪院外,因著這日趕來大相國寺的百姓非常多,派發的粥與饅頭都得現煮現蒸才勉強趕及派發,所以棚下都是剛壘不久的土灶,頭架著大鍋,不是在咕嘟咕嘟煮粥,就是在蒸印著平安與福壽字樣的包子。
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燒著,食的馨香彌散開來,攪明舒胃中陣陣翻涌,今日午飯和晚飯皆未食半粒米,然現下也顧不。
“明舒?”人群中有人忽然住了。
“宋清沼?”明舒轉頭就見到宋清沼,“你怎麼在這里?”
“過來看看我母親的,答應盧三娘子,參加這次的普渡會,在這里忙了整天了。”宋清沼向曹海抱拳打了招呼,回答明舒,“你呢?你也來參加法會?”
“不是,我來找柳婉兒和唐離的。”明舒道。
聽到這兩個名字,宋清沼不由蹙起眉頭:“柳婉兒……不就是盧三娘子,已經去放生池準備放燈祈福儀式,唐離……這兩人關系?”
解釋起來又要長篇大論,明舒沒有時間,搖搖頭只問他:“你可知這次都有哪幾府參加柳婉兒的普渡會?”
宋清沼想了想,道:“知道。我母親也掛名負責這次普渡會,人員名單曾經送到母親手中,正巧讓我核對過……不過我也只記七八。”
記得七八,已經是記絕佳了,何況還只是他謙虛。
宋清沼逐報出名單的人員,以及他們的來歷份,明舒越聽臉越差,聽到最后,手已抖。
如果沒記錯,這所人中三是當年與蘇昌華案子相關的人員,或多或都沾了些邊,不是做了人證就是落井下石。除了最直接的告人盧則剛外,陸文瀚也說得很清楚,順安王的案子牽涉甚廣,當時京為求自保相互攀咬,以圖赦免的機會,另有些則踏著這些涉案員的尸往爬,蘇昌華也許微不足道,無形中卻也了很多人的踏腳石。陸文瀚提及了幾個員名字,當時注意力全在盧家,并沒完全記牢,但就零星記住的這些人,已經足夠讓發寒。
唐離絕對不是無緣無故把這些人聚在一起的。
“他們現下何?盧家人呢?”明舒急道。
派粥的只剩下各府的下人,主子們已經不見。
“都回禪房休憩了。”宋清沼剛從里面出來,那里頭眷太多,他呆著難,就找個由頭離開了。
盧家的主母馮氏、幾個嫡庶兒還兒子,其余各府的夫人娘子等,如今已全去禪房休憩。
明舒又開始頭疼——唐離到底想做什麼?
正想著,遠又跑來兩個人,正是應尋和他的同僚。
“總算找到你了。”應尋跑氣不接下氣,可以看出他亦心急如焚,“已經用你給的畫像問過彭氏母子,確認是唐離。”
明舒當機立斷道:“不管了,既然已經確認柳婉兒并非盧三,那就先將拿下問話,能個威脅是一個。”
語畢又見應尋人手單薄,便朝邱明等人開口:“柳婉兒邊有不護院,你們幾個陪應捕快去放生池走一趟,還,現下那邊百姓很多,萬不可引起。”
邱明等人還要留在邊,卻被斷然拒絕:“現下已不是計較個人安危之時了,今日百姓很多,若是出事恐涉及無辜,快些去吧。”
邱明這領命與應尋離開,明舒又將應尋手中那張畫像遞給曹海,只道:“畫中此人很危險,我猜必定就在寺,也許就在附近,煩請將軍幫忙,我們分頭找人。”
曹海收下畫像又分于手下看,只道:“沒問題。”
很快曹海就帶著手下四散搜人,明舒與宋清沼都認唐離,并不需要畫像為憑,也跟著分頭找起來。宋清沼往外邊搜去,明舒在禪院又找了遍,并沒發現與唐離相似的男人,正站在樹下著氣歇腳,忽見長廊走來個丫鬟。
那丫鬟微垂著頭,緩緩行過,走進長廊拐角往廂房后去了。明舒盯了片刻,邁步追。跟著的方向追到廂房后面時,卻不見那人影,只剩下空的后巷。
后巷里堆滿用油布蓋著的雜,撂撂疊高,這兒沒掛燈,只有廂房的燭火過窗紗灑下朦朧的芒,外面的喧囂被襯出幾分不真來。
明舒追進后巷徘徊了幾步,只狐疑那人的去向,忽然背后發出窸窣聲音,心頭一凜,猛地轉,卻見那丫鬟自兩撂雜隙間走出,冷冷道了聲:“陸娘子在找我?”
已然抬頭,出張沒有表的清秀臉龐。
不是唐離又是何人?
難怪找了半天沒發現人,原是又換回了裝。
“果然是你!”明舒退后兩步,警惕道,“設局利用我送林婉兒進盧府的人是你吧?借三殿下之手促這次的普渡會也是你的安排吧?你究竟意何為?”
“你既然能找到這里,不是應該心中有數,何必還要問我?”唐離的聲音在黑暗中冰涼而深。
“你替豫王辦事,要謀害三殿下?”明舒試探問道。
聲音剛落,就見唐離笑開,出幾顆森白的齒,道:“枉我將你視作勁敵,還道你什麼真本事,原來也與普通世人一般見識,怪沒新意的。這世間還沒人資格讓我替他賣命,豫王又算了什麼。”
的笑容與言語間都著自負的意,高高在上的模樣著人不愉快。
明舒道:“哦?這麼說你不是為了幫豫王爭位?”
“在我眼中,哪怕天潢貴胄也不過是與張松、謝熙之流樣的庸人,所求者必可控,我借來用用而已。”唐離嗤笑道,說完忽又宛如對閨中友般嗔道,“這都怪你,當初在松靈書院若非你們兄妹橫腳,如今我就不是跟著豫王了,也沒今日這許多事了。”
“所以……”明舒倒口氣,“松靈書院果然是你導張松殺楊子書,而你本借此案大展拳腳,找出真兇得三殿下青睞?”
然后憑著本事為三皇子的幕僚,堂堂正正離開書院,而不是一個被逐出書院的罪臣之后。
如果這個故事換個方向發展,會與現在全然不同。
唐離笑笑:“可惜了……一場籌謀卻全了你們。”只能另尋辦法,靠著通過謝熙接近了豫王。
說著了天空,又看向明舒:“怎麼?你想在這里與我敘舊?”
明舒瞇了瞇眸:“何不可?我想看看你在等什麼。”不能走,不能放任唐離一個人在這里,否則也不知道唐離會做出什麼瘋狂的舉。
唐離似乎嘆口氣:“你還心思與我夾纏?不去看看你的阿兄?要知道今日三殿下登禪臺的提議,可是你阿兄提出來的。若是三殿下在禪臺上出事,你阿兄要背負的罪名你可清楚,連同你們的母親在……恐怕都難逃劫。”
明舒心中劇震:“不可能,我阿兄為何要遂你的愿讓三殿下登禪臺?”
“我說了,所求者必可控。誰讓周秀清在我手里,而陸徜又只剩下這個證人。他為了你,可是豁出了家命,你真的不去救他?按計劃,三殿下在禪臺上的最后一步,可是致命的,你現在趕過去,或許還來得及阻止。”
從豫王知三皇子皇命徹查江寧簡家劫案,心生疑,便勸說豫王派人前往江寧,演了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戲碼,不僅查到明舒份,還在半途從陸徜手里劫走了周秀清,加以利用,威脅陸徜。
明舒面頓白,驚懼地看了唐離兩眼,飛快轉。唐離畔那抹得意的笑越綻越開,卻沒想明舒只跑出了兩步就又停下轉。
“你當我阿兄是傻子嗎?”明舒臉上的驚懼全失,換上嘲弄的笑。
縱然心臟跳得像要撕開膛,在此時也必需冷靜。不是不擔心陸徜,不是不想馬飛到陸徜邊,但是現在不行。得相信陸徜——從前幾天他要求一起演戲開始,陸徜應該自有安排,只不過沒能想到,他們的敵手竟是同人而已。
就算是九死一生的局面,此時也必須相信陸徜。
這回到唐離的笑容微滯。
“你這箭雙雕的計策使得不錯呀。設計三殿下登禪臺既滿足了豫王的要求,又能令工部尚書盧則剛為替罪羔羊,報你蘇家私仇。什麼東宮爭戰,不過是你用來掩蓋私心的煙幕罷了。豫王以為自己找了把刀,沒想到卻被刀利用了去。”
唐離一介孤,想要完這麼大的布局,只能借勢借力。設計三皇子,不過是取信豫王的手段而已,否則豫王又憑何任調用人力力去完這場計劃?
“你知道如此清楚,那還站在這里同我廢?”唐離冷笑道,并不反駁明舒的猜忖。
“可你不是說我與世人一般見識,毫無新意?唐離,你我對話這段時間,你知道自己已經看了三次天嗎?你在等什麼?等柳婉兒?”明舒勾反問,現出幾分咄咄人之勢,半點沒給唐離留余地問道,“‘柳婉兒’是豫王借你的人,裝作柳家那病故的兒回到城中。為了坐是盧三娘這個份,家里那把火,不是出于意外吧?蔡氏也不是因為害怕別人知道柳婉兒就是盧三娘登門的,因為不管是真的柳婉兒還是假的柳婉兒,都不是盧家真正的盧三娘!你們挑中柳婉兒,只是因為的份最好造假。蔡氏是被你們引上門,而后故意縱火謀殺的……我可有猜錯?”
猜你喜歡
-
完結282 章
傲嬌醫妃
她是醫學界的天才,異世重生。兇險萬分的神秘空間,低調纔是王道,她選擇扮豬吃老虎翻身逆襲。他評價她:“你看起來人畜無害,實則骨子裡盡是毀滅因子!”她無辜地眨著澄澈流光的眸子,“謝王爺誇獎,只是小女子我素來安分守己,王爺可莫要聽信了讒言毀妾身清譽!”錯惹未婚夫,情招多情王爺,闊氣太子與帥氣將軍黏上來……美男雲集,
74.4萬字8 78129 -
完結539 章

世子爺他不可能懼內
顧淮之救駕遇刺,死裡脫險後染上惡疾。夢中有女子的嗓音怯怯喚著淮郎。此等魔怔之事愈發頻繁。 顧淮之的臉也一天比一天黑。 直到花朝節上,阮家姑娘不慎將墨汁灑在他的外袍上,闖禍後小臉煞白,戰戰兢兢:“請世子安。” 嬌柔的嗓音,與夢境如出一轍。 他神色一怔,夜夜聲音帶來的煩躁在此刻終於找到突破口,他捏起女子白如玉的下巴,冷淡一笑:“阮姑娘?” ……
89.2萬字8.18 15272 -
完結105 章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幾年,與哥哥走散,被賣進定國公府給詹五爺做妾。詹司柏詹五爺只有一妻,伉儷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無子嗣,只能讓俞姝這個盲妾生子。他極為嚴厲,令俞姝謹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連每晚事后,都讓俞姝當即離去,不可停留。這樣也沒什…
49.6萬字8 28751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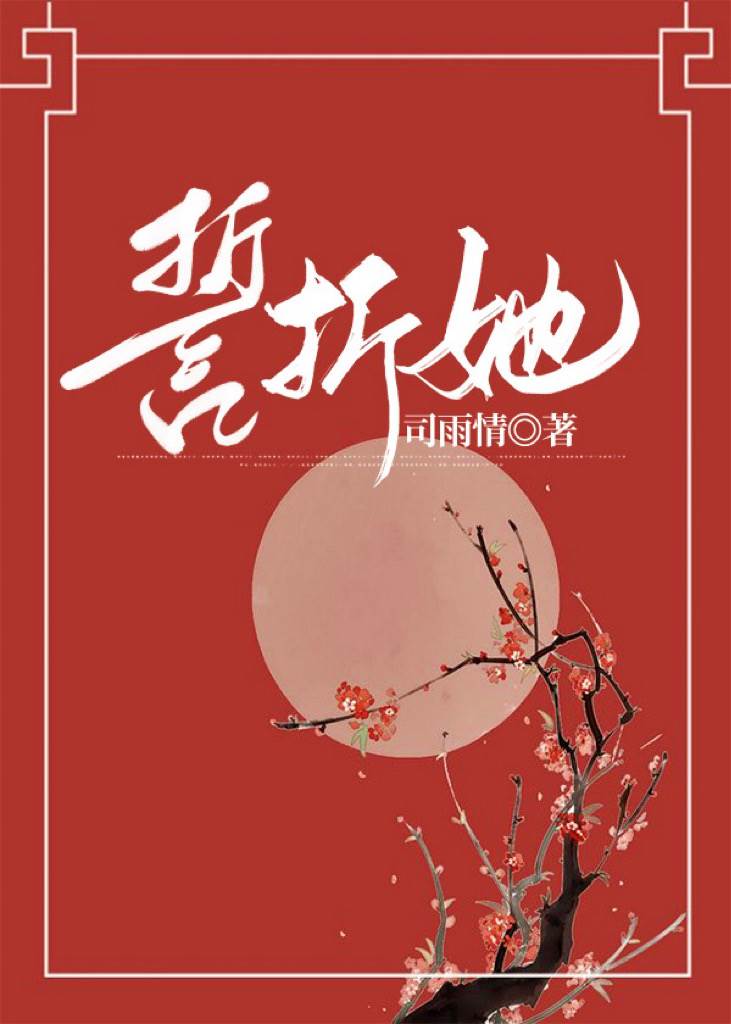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445 -
完結587 章

戰神重生,王妃帶著醫術炸翻王府
堂堂大夏國掌政帝姬,重生到相府不受寵的嫡長女身上。被逼著嫁給一個瘸腿不受寵的王爺,想要不動聲色除了她?姐姐一門心思的想要弄死她?很好,她難不成是小白兔,任由這群人欺負嗎?想要弄死她,那也得看看有多大的本事。本想逃離王府,計劃復仇,卻沒想到,被那瘸了雙腿的夫君抱起,苦苦追求,愛她入骨。她要報仇,他為妻善后。她要殺人,他為妻磨刀。她要打胎,他雙眼含淚,跪在地上祈求不要!
103.1萬字8 34588 -
完結339 章

王爺每日一問,小妾今天宅鬥了嗎(九重錦)
宅鬥,非雙潔被壓製了十幾年的庶女,一朝被重新安排了命運,入了王府,助長了她的野心。生父的漠視,任由嫡母欺淩她們母女半生,從不庇護半分。嫡姐以為,她是個空有美貌的草包美人,想利用她的美色為自己固寵。卻不曾想,她脫離了所有人的掌控。為了往上爬,她也用盡手段,沉浮在虛虛實實的感情裏,直到她徹底認清現實,這一切的人和事都在教她如何做一個立於不敗之地的女人。
60.8萬字8 218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