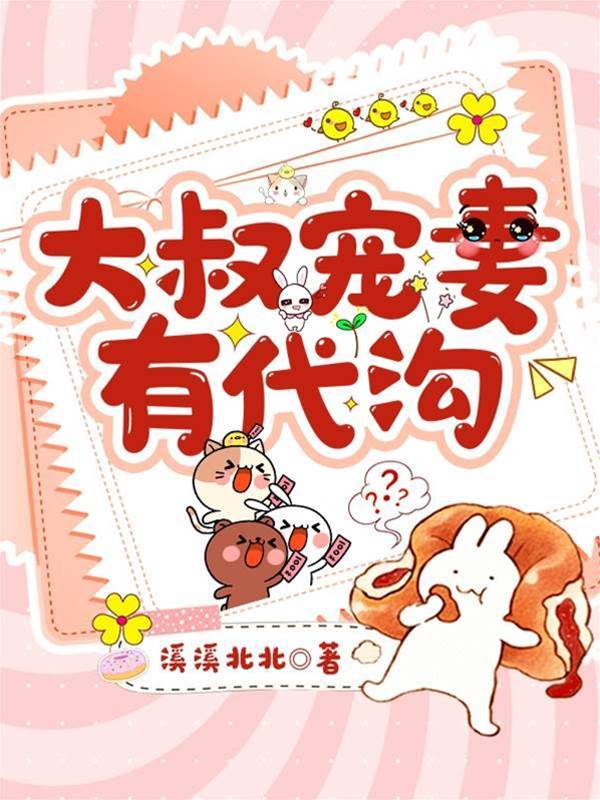《雙軌》 第36章 Chapter 36
此時此刻的一切都讓姜暮無比煎熬, 無論是周圍這些份不明的人,還是今晚發生的事,亦或是現在靳朝帶著溫度的手, 每一個紋路都烙在的皮上, 清晰到讓本難以忽視。
姜暮覺自己的心臟都在漂浮, 那種不真實讓腳步虛,卻在這時那輛白的車子開了過來,姜暮一眼認出是在沙土地上幾度和他們并駕齊驅的男人。
當時靳朝故意帶起一片塵土干擾對手視線,只有這個男人沒有減速,甚至一度超出他們半個車位,只是當時在兩輛車都不能停下來的況下, 他們多了個人,所以占了點優勢。
剔著圓形寸頭的男人走下車來, 穿著貴氣的貂皮上,雙手抱著靠在車邊對著靳朝說道:“有酒, 你的領航員有價嗎?”
說著眼神興趣地盯著姜暮,旁邊有個男人了句:“怎麼?現在改口了?也喜歡的?”
梁彥沒有答這人的話,只是對著姜暮出意味深長的表。
靳朝呵笑一聲,直接回道:“不好意思, 無價。”
梁彥挑著眉, 幾個跟他悉的人對著靳朝笑道:“有酒你注意點啊, 看中的人沒有哄不到手的。”
靳朝無所謂地回睨著他, 語氣里帶著幾不屑:“試試看啊。”
梁彥邊的笑意逐漸擴散, 低頭點燃一煙,又慢悠悠地抬起頭朝著姜暮吐出一個個心形狀的煙圈, 姜暮沒有看過還有這種作的人,頓時判定這人不正經, 一臉嚴肅地盯著那個花花大。
梁彥從來沒見哪個姑娘會用一種考古的眼神瞧著他,那不的小表讓他瞬時就笑出了聲。
靳朝皺了下眉轉過頭平淡地掃向他,姜暮尷尬地收回視線對靳朝說:“好冷啊。”
周圍禿禿一片,夜里寒風四起,靳朝緩緩收回目,眼神落在姜暮凍得通紅的臉上,拉開夾克拉鏈眼里泛起饒有興味的笑:“要抱抱嗎?”
姜暮的瞳孔逐漸放大,濃郁的眸子微微著,可即使這樣也本無法分辨現在的靳朝到底在演戲還是跟說真的,他眼里像有鉤子,溢出一抹心神俱當的神采,讓姜暮的腔也跟著微,相比而言,的演技略顯拙劣,本不敢對他有任何,只是把雙手過去放進他的外套里,還不敢著他的腰,基本懸空著。
靳朝低眸淺笑,直接收外套將圈進懷中,姜暮的猝不及防跌進他溫熱的口,被他的外套包裹著,暖和的溫度和悉的安全瞬間將淹沒。
第一天來銅崗看見靳朝站在路邊上看著的時候什麼?也曾想過像這樣和他來個久違的擁抱,可那時候已經發現,現在的靳朝已經不是過去的哥哥了,他不再會主臉,冷的時候幫捂手,沒事抱著轉圈。
這一個擁抱遲了整整五個多月,姜暮的手漸漸抬了起來穿過他的腰環住他,眼圈發酸。
靳朝對著旁邊人說道:“我對象怕冷,先帶回去了。”
其他人說著是冷的,都散吧,姜暮的神僵住,不知道靳朝把拽過來是不是只為了找個借口離開?
從他懷中抬起頭看他,靳朝垂眸,難辨真假的碎在眼眸中對笑道:“沒抱夠回家慢慢抱。”
旁邊的男人說道:“行了,你們趕回去辦事吧。”
靳朝抬起頭臉上掛著玩世不恭的表和那人笑罵了一句,姜暮松了手倉皇失措地轉過去,靳朝摟著的肩帶著往車子那走,可是一離開人群靳朝就松開了,大家都陸續上了車,一轉眼的功夫所有車子都開走了,靳朝的手機還在姜暮口袋,一上車手機就震了下,將手機拿出來看見剛才那個群解散了。
姜暮把手機還給靳朝,余看去,他臉上哪里還有那些和風流氣,早已恢復往日的平淡和冷漠。
所有人都被他那副樣子騙了,只有明知道是假的,某一刻還是沉溺在他滾燙的眼眸中,姜暮把目移向窗外,整個人異常沉默。
靳朝不時瞧上一眼,姜暮的表很繃,雙手死死握著安全帶,明明車速開得不快,可還是很僵的樣子,滿臉愁容。
大約開了十多分鐘,靳朝將車子拐上一個荒郊野嶺的小山坡,一直開到了山坡盡頭才緩緩停了下來。
前方是看不到底斷崖,頭頂是漫天的星空,四周沒有一點亮,在姜暮從小長到大的城市似乎很難找到這麼一安靜得仿若真空的地方。
靳朝打開門下了車,從車后繞到的車門邊,車子沒有熄火,暖氣還在開著,靳朝敲了敲車窗,姜暮把窗戶落了下來,他的替擋去了窗外的冷風,點燃了一煙,深吸一口抬起頭將煙霧吹散消融在夜空中,對說:“打開信封看看吧。”
姜暮把一直攥在手中的信封撕開,里面是一張張百元鈔票,垂著眸,著那疊錢。
靳朝叼著煙著蒼茫的黑夜:“這就是你想知道的。”
姜暮的涌現出寒意:“為了錢。”
“不然呢?還能為了什麼。”
姜暮后怕道:“剛才那個人撞了車。”
“死不了。”靳朝的語氣冷淡甚至稀松平常。
姜暮抬起眸難以置信地看向他的背影:“什麼死不了?是我讓你繞一圈拐進二道的,我想你甩開他,沒想讓他撞車,萬一他有什麼事會查到我們頭上來的。”
靳朝將煙拿到手上,半垂著眸:“全國每天那麼多車禍,都怪附近的車?”
“可是,你們這是,這是非法飆車啊,萬一有人報警怎麼辦?”
“能怎麼辦,誰知道我們在場?”
“其他那些人......”
靳朝嗤笑了一聲:“順便把自己供出去?”
“如果有路人看見呢?”
“我不認識那群人,這條路還能不給我走了?”
“群里那個定位,群……”
群解散了,全員言,沒有留下任何聊天記錄,易是現金,無法追查,附近是未開發的地段,連監控都沒有。
姜暮突然覺一涼意從腳蔓延至口,將信封狠狠甩在座位上,拉開車門下了車一把狠狠甩上門盯著他:“即使做得再蔽又怎麼樣?萬一出了事呢?為了錢難道還要把命搭進去了?今天是他,明天是你呢?錢就那麼重要嗎?為什麼要過著這種命懸劍上的生活?”
靳朝的眉骨投下一片影讓他的眼窩深邃得像無法探索的星海,他的聲音仿若從山谷里傳來,帶著渾厚的抑重復低喃著:“命懸劍上的生活。”
他的邊突然劃過一諷刺的笑意:“那你覺得我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
冷風吹起姜暮的短發,轉走向崖邊,看著無際的黑暗,回答他:“不知道,起碼不是這樣的,不能安安穩穩嗎?”
“既然不知道,那我來告訴你。”靳朝將煙扔在泥土地里,厚厚的鞋底碾了上去,直至將煙頭徹底踩地底再也掙扎不上來。
“我和靳強剛來銅崗沒地方住,租了個地下室,沒有窗戶沒有,白天當晚上,只要下大雨屋子能淹到,作業書包床墊全泡在水里,還有老鼠尸漂在水上,只能把桌子拼一拼睡覺,第二天再把積水一盆一盆往外潑。
他聽人說可以介紹他去做土石方,要介紹費,把上的錢都了出去,那個人電話直接了空號,我們連地下室都沒得住。
睡過天橋,睡過馬路,睡過澡堂子,你跟我說錢不重要?
后來他終于找了個靠譜的工作,上趙娟,他離過婚,趙娟是頭婚,他沒有房還拖著我,好不容易湊足了首付,一點工資每個月付完房貸本沒有多余的錢,學校一要錢我就得在他們房門口拿著繳費單為了兩三百塊難以啟齒,你說錢不重要?
二十年的房貸,無止盡的醫藥費你以為靳強一個人能抗得住,他最難的時候沒有丟掉我,你覺得我應該對你爸拍拍屁走人嗎?”
北方的天際掛著一顆最亮的星,無數漆黑的夜里那顆星星指引著姜暮,順著它的亮一點點索到今天,以為,以為爸爸和靳朝離開以后,的生活從此四分五裂,在羨慕其他孩子有爸爸,為了自己的需求傷春悲秋時,大地的另一頭靳朝卻在為了生存苦苦掙扎,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都解決不了。
姜暮再抬起頭時,那顆星星依然掛在北邊,只是它的變得刺眼,像冰錐扎進的心臟,讓淚眼模糊。
轉過對他說:“我媽知道嗎?知道爸過來被騙的事嗎?知道你們沒地方住的事嗎?”
黑暗的影勾勒出靳朝的側臉,他低著頭,在姜暮提起姜迎寒時,他眼里的神到底還是波了一下,只是最終歸于一片死寂,淡淡道:“知道又怎麼樣?不知道又怎麼樣?他們離婚了。”
姜暮幾步走到靳朝面前,噙淚著他:“即使是這樣也不至于,不至于要去干那些鋌而走險的事。”
靳朝起眼皮,表淡漠嘲弄地說:“對我來說只要能弄到錢就至于,命懸劍上的生活又怎樣?命都沒了還怕懸在劍上?我不想讓你看到這些事,對,你說的沒錯,你來這里不過就是上一年學的,本來就不應該摻合進來,現在知道怕了?”
姜暮踮起腳死死抓住他的前襟吼道:“你非要這樣嗎?明大道不走,偏偏一條道走到黑?”
靳朝只是低垂著眼眸,對說:“松手。”
“不松,我為什麼要松?”
靳朝的外套被死死攥著皺在一起,他的耐心已經耗盡,最后一次警告道:“松手。”
姜暮睖著雙眼拽得更:“你看我會不會松?你以為沒人能管得了你了嗎?”
靳朝下微抬,削薄的抿出一道邪的冷厲,直接握住的肩膀將整個提離地面回在車門上,近道:“你想管是吧?以什麼份管?你還以為自己姓靳?你連姓都改了,你忘了自己姓什麼我提醒你,姜暮。”
在他面前太小只,整個人被他錮在車門上脆弱卻又固執地著他,靳朝上那強悍卻森冷的氣息覆蓋而來,無孔不地鉆進姜暮的心臟,氣得連都在發抖。
他沒有喊過的名字,來到銅崗后他從來沒有一次連名帶姓過,就連靳強也沒有,他們都是在意的吧,一個小小的姓讓他們的關系,讓他們的生活從此天南地北。
的聲音哽咽著問他:“所以…這就是你不回來看我的原因?你怪我們?怪媽讓爸凈出戶,你恨對吧?”
靳朝握著姜暮肩膀的手幾不可察地晃了下,漸漸耷下眼皮邊掛著不屑的弧度將苦咽進里,拉開車門,把姜暮重新塞進車,再關上門。
姜暮坐在車子里面,靳朝站在車外一接一著煙,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吵架,事實上他們的兒時,吵架幾乎充斥著每一周的日常,為了玩能吵,為了吃飯能吵,為了玩能吵,甚至為了一筆都能吵,可每次都是靳朝退讓,他可以把玩讓給,可以把好吃的魚籽和胗讓給,可以遷就陪玩那些在他看來稚無聊的游戲。
可是有一件事他不會退讓,每周六下午去模型店,即使姜暮對著他哭鬧,即使靳強和姜迎寒都不準他去,他也會梗著脖子獨自站在門口僵持到他們拿他沒有辦法。
姜暮清楚他可以對所有事做出讓步,可他真正想做的事,沒有人能攔得住,從小就是這樣,正是因為這樣,才愈發焦慮,怕他在向一條萬劫不復的道路走去,怕他的未來會重蹈覆轍,怕走了以后他會更加無所顧忌。
不知道過了多久,靳朝接了個電話,隨后滅了手中的煙敲了下車窗問:“靳強打電話來了,回去吧?”
“不回。”姜暮沒有看他,沒有落窗,只有這兩個字。
靳朝繞回駕駛座關上車門,單手搭在方向盤上側過子睨著,一生起氣來,臉總是嘟嘟的,跟了多大的委屈一樣,靳朝的語氣緩了幾分:“怎麼樣才能回去?”
“你先答應我。”
靳朝邊史最富的就是金瘋子,雖然談了很多對象,但是一般不出三個月就被甩了,常年在被甩和失的路上狂奔。
一失就喊兄弟出來喝酒,喝到后面大家也習以為常了,頗有種他為了喝頓酒才去驗的覺。
金瘋子最常說的就是:“人吧,一委屈起來總覺自己做了什麼特對不起的事。”
雖然靳朝從沒有過這種煩惱,但此時看著姜暮嘟著臉的模樣,他也莫名其妙有了這種覺。
靳朝無聲輕笑著,手指敲打著方向盤,眼里已經重新掛上松散的神:“你要我答應你什麼?”
姜暮不知道他怎麼還能笑出來的,沒好氣地說:“答應我干正經事,別瞎混了,你不答應今晚就都別回去了。”
靳朝繃著下目很靜,墨瞳淡淡地看了一會,然后放下靠背直接躺了下去。
姜暮坐直子急道:“你……”
靳朝雙手叉在腦后,一副隨遇而安的模樣:“那就不走吧。”
姜暮氣得快要炸了,靳朝還干脆閉起了眼,要是小時候早到他上跟他干一架了,現在又打不過他,又不敢他上去,只能也把椅背一放,重重地“哼”了一聲,翻過去。
靳朝聽著故意鬧出的聲響,瞇起眼朝看去,拿背對著他,一團。
靳朝腦子里的事太多,被姜暮今晚一攪,得好好順一順,所以他閉著眼但并沒有睡著。
倒是姜暮,躺下去后沒一會呼吸就均勻了,靳朝坐起盯看了看,微卷的睫乖巧地順著,睡著了還微微皺著眉,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他抬起拇指輕輕了下的眉心,姜暮翻了個,潤的臉籠在月下像鍍了層溫的紗拂過他的心口。
他無無源,從南到北,這是唯一一個會始終牽掛他的人啊!
無論夜有多黑,路有多長,在這一晚,靳朝心里常年寒的角落因為眼前的人進了。
猜你喜歡
-
連載958 章
俏皮甜妻娶進門
被送給活死人做沖喜小妻子的夏安然,隻想裝蠢賣醜,熬死老公後跑路。可是,躺在床上的活死人老公,怎麼轉眼變成了冷酷毒辣、心狠手辣的的商業帝王?最最最關鍵的是……她之前才一不小心、趁火打劫,將他吃乾抹淨了!!!肚子裡揣著的那顆圓滾滾種子,就是她犯下滔天罪孽的鐵證!夏安然抱著肚子,卑微的在線求救:現在跑路,還來得及嗎?淩墨拖著試圖帶球跑的小妻子回家,一邊親,一邊逼她再生幾個崽崽……
88萬字8 61172 -
連載768 章

婚婚欲睡:陸少夫人要離婚
童心暖暗戀陸深多年,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給陸深,結果……新婚第一天,陸深的白月光帶著孩子回來了,新婚第二天,她的父親死了,自己被逼流產,新婚第三天,她簽下了離婚協議,原來陸深從未愛過她,所謂的深情都是她自以為是而已。
170.3萬字8 38374 -
完結5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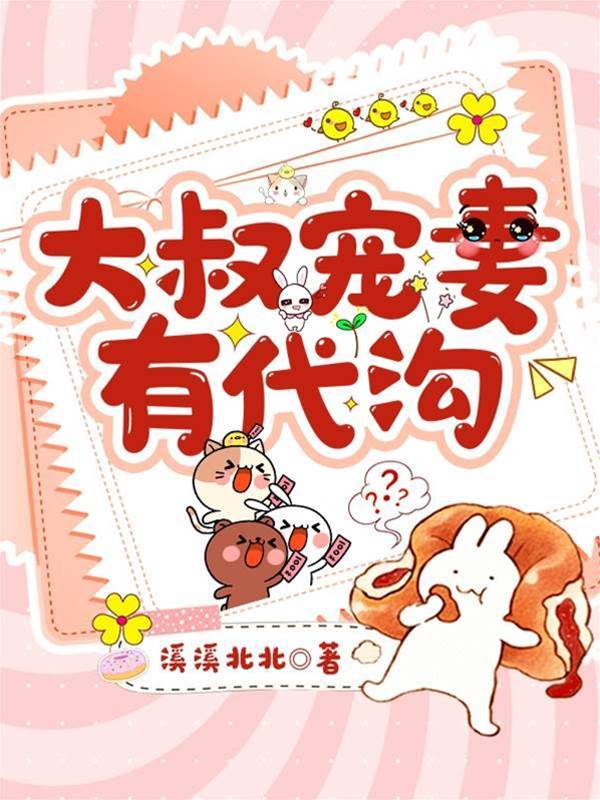
大叔寵妻有代溝
等了整整十年,心愛的女子終于長大。略施小計民政局領證結婚,開啟了寵妻之路。一路走下,解決了不少的麻煩。奈何兩人年紀相差十歲,三個代溝擺在眼前,寵妻倒成了代溝。安排好的事情不要,禮物也不喜歡,幫忙也不愿意… “蘇墨城,不是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怎麼現在搖身變成了公司的總裁。” “蘇墨城,不是說,以前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嗎,那你父親和我母親之間怎麼會是這種關系?”
55.3萬字8 51537 -
完結2072 章

幸孕六寶寵上天
一場陰謀,她被親爸賣了,還被人搶走孩子,險些喪命。五年后,她帶著四個孩子強勢回國尋找孩子,懲治兇手,沒想剛回來孩子就調包。發現孩子們親爹是帝都只手遮天活閻王顧三爺后,她驚喜交加,幾番掙扎后,她舔著臉緊抱他大腿,“大佬,只要你幫我收拾兇手,我再送你四個兒子!”三個月后,她懷了四胞胎,“顧南臣,你個混蛋!”“乖,你不是說再送我四個兒子嗎?”顧三爺笑的很無恥,逢人就夸,“我老婆溫柔體貼又能生!”她:滾!
198.5萬字8.18 526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