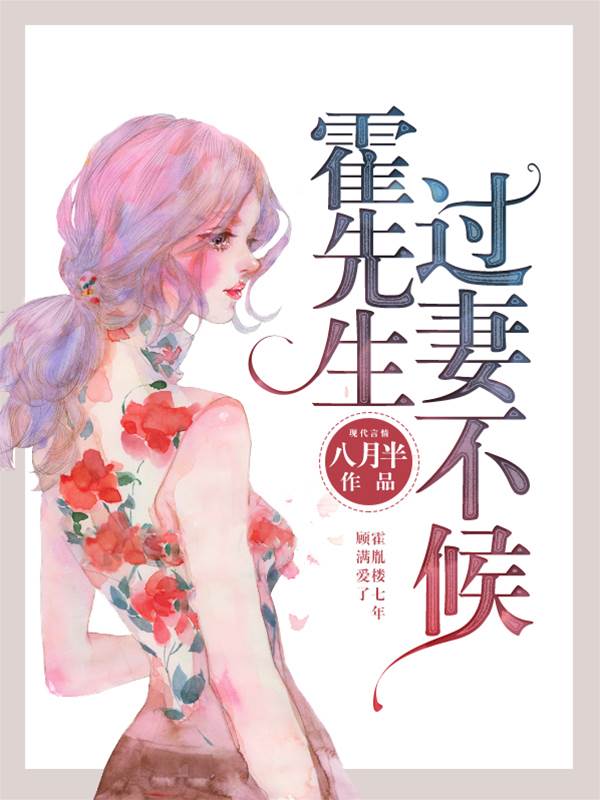《只要你》 第62章 心愿
陳忌扯了下角,森冷的笑容里似是藏了無數的冰刀,眼角微垂,看都懶得看那垃圾一眼,只睨著剛剛戴好的手套,漫不經心地調整著,還當真有點兒和故人敘舊的閑散模樣:“幾歲了,挨打就喊爹?”
“你要是喊我一句爹,應該比喊外邊兒那個管用。”陳忌嘖了聲,“算了,那老子家門得多不幸,才能出這個東西。”
付其右此刻沒心也沒膽量和他說話,他深知陳忌此刻的不不慢之下,藏著是多麼駭人的怒。
付其右只能將所有希寄托在門外的父親上,見父親關了門,還是不死心,扯著嗓子繼續喊:“爸!我可是您兒子!”
陳忌眉心輕蹙,大抵是嫌吵了,深黑皮質軍靴稍稍抬起,往床尾的羅馬柱上猛踹了一腳,大床瞬間門偏出大半,直直將地上的付其右橫堵在墻壁轉角的隙之中。
付其右一下噤了聲,面發白,連呼吸都不敢用力。
陳忌舌尖懶洋洋地抵了抵臉頰,慢條斯理道:“別他媽喊了,你爸又不止你一個兒子。”
“大老婆那邊兒還有倆,你該不會忘了吧?連給你取名都取個球,你在你老子心里,估計也就是個球,必要的時候,丟出來給大家打著玩兒,尋個開心。”
“你放屁!”付其右頭皮發麻,上逞了一時之快后,下一秒便發起慌來,大概潛意識里也知道,陳忌說的是對的,畢竟他只是個私生子,平日里呼風喚雨也不過是仰仗付家主家留下的幾代家業,若是將他與付家的未來放在一塊相較量,父親付王毫不猶豫放棄的,一定是他。
陳忌帶來的迫和威懾實在太過駭人,付其右蒼白,嚇得幾近不上氣,片刻后,他里喊的人從父親變了母親。
那是他最后的希,畢竟他是他母親唯一的兒子。
然而他似乎高估了母親在父親心中的地位。
陳忌眉心蹙著,沒耐心再和這垃圾耗下去,渾上下的戾氣毫不掩飾,堆積已久的心疼與暴在頃刻間門,雜相融,面上表仍不改,從容淡定,下手的力道卻一下比一下狠絕。
付其右幾乎是沒有半點回擊之力。
幾年前他和陳忌過手,邊十來個兄弟一塊上,都沒法傷陳忌分毫,還手帶來的只會是更大的痛苦。
屋傳出陣陣哀嚎慘,屋外,付王和小老婆齊鈴一左一右守著房門。
付王閉著眼,裝聽不見,默不作聲。
小老婆齊鈴顯然沒有他淡定,畢竟里頭挨打的是自己這輩子唯一的命子,屋傳出的喊聲聽了不出幾分鐘,便忍不住紅了眼眶,沉不住氣地拽著付王的手臂直求:“進去救救兒子吧?這樣下去會被打死的!”
付王深吸一口氣:“放心吧,為了你這個混蛋兒子,人家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搭進去,你覺得可能嗎?陸天山這兒子,心思比他老子還深,做事有分寸得,你兒子頂多去半條命,死不了。”
“再說了,咱們進去怎麼救?那塊頭,讓保安全進去,也不是人家的對手。”
一聽到去半條命,齊鈴更是不了了,心里發慌忍不住開始嘀咕:“報警吧,啊?報警吧老公!我們讓警察來抓他——”
“你清醒點!”還沒等齊鈴把話說完,付王便出口呵斥住,“你兒子從小到大犯過的事,你自己數得過來嗎?得虧是沒人報警,花點兒錢了事,你難道還想親手把兒子送進去?老實點兒!之前你兒子打別人的時候,沒見你這麼張。”
“里頭那位可是陸家獨子,得罪了陸天山,付家想要在北臨繼續混下去,比他媽登天還難!”
齊鈴這會兒也是氣上了頭:“付家付家,你一天天就知道付家!”
付王偏過頭,眼神里的火氣也不小:“沒有付家,你和你兒子就他媽是路邊兩條人人喊打的狗!”
正如付王所說,陳忌在打架這件事上,分寸十足。
從前在今塘,從小到大就沒混過,如今又長了幾個年頭的歲數,知道怎麼理能又疼又不把人弄死。
他還得陪周芙走完往后幾十年的路,不可能因為一個付其右,臟了自己的手。
因而打打休休,五次之后,陳忌停了手。
男人眼神往床邊起居區的層架上一瞥,各種各樣的小提琴擺滿了一整面墻。
陳忌眸黯了黯,深不見底,沉著臉走到層架跟前,隨手拿了一把下來。
付其右這會兒在墻與大床的隙間門,閉著眼,沒敢抬眸看他,連哀嚎也只剩下小小的氣音。
陳忌了后槽牙,咬紋路清晰可見,握著小提琴的大手朝著付其右高高揚起的一瞬間門,手臂停頓在空氣中。
付其右的喊幾近失聲,神帶著極度的恐懼。
那面墻的小提琴,曾是他用來欺凌他人最有力最得心應手的工。
他清楚的知道,每一個在他小提琴下挨過打的人,表有多痛苦。
陳忌那揚起的琴停留的時間門多一秒,付其右心中的張與懼怕就多煎熬一秒。
良久,男人大手緩緩垂下,面無表將小提琴往付其右上一砸。
待地上那灘垃圾稍稍舒了口氣之后,忽而沉聲道:“自己割,別他媽老子親自手。”
他不可能允許自己為周芙影中最恐懼厭惡的樣子。
付其右此刻兒不敢有任何異議,幾乎是陳忌說什麼,便順從地做什麼,哪怕是對自己下手,也只能咬著牙關強行著。
陳忌面無表地垂眸輕撣著手套,看都懶得往付其右那頭多看一眼。
再抬眸時,眼神不經意間門掃過小提琴層架墻后的玻璃窗。
男人不自覺蹙起眉心。
玻璃窗上著各各樣竹林的照片,一些照片的拍攝角度看起來還莫名有點眼。
玻璃窗下的臺面上,整齊擺放著手表,錢夾,老式相機等一系列看起來上了年頭舊。
陳忌偏頭瞥了眼還沉浸在痛苦和恐懼中的付其右,隨手掏出手機,遠遠往玻璃窗拍了幾張照片,最后給事先安排好的人去了個電話。
醫護人員隨其后,進門之后將地上的付其右直接打包擔走。
出了臥室門時,陳忌的表從容到真像去里頭喝了杯茶,敘了敘舊般,閑散淡定。
付王看著付其右被擔走,也不敢有異議,只同陳忌客氣道:“麻煩陳總了。”
陳忌隨意點了個頭,也沒看他,淡淡開口:“應該的。”
而后頭也不回地出了祿戚山莊。
上了花園外停著的黑大g之后,陳忌隨手將手套摘下,正要往副駕駛座丟時,作停頓了下,而后拐了個彎,往后座拋去。
副駕駛是周芙的專座,不能被這玩意臟了。
車子一路開到山腳時,陳忌兜里的電話震了下。
見是周芙打來的,他忙接起來。
小姑娘糯糯的嗓音從電話那頭傳過來時,陳忌只覺得心頭都了幾分。
應該是剛睡醒,說話的腔調里還帶著極其濃重的鼻音,含含糊糊的嘟囔著:“陳忌,你什麼時候走的呀?”
“你睡著之后沒多久。”他如實回答,“不是提前和你說了?”
“唔……”
確實提前說了,但是迷迷糊糊轉醒之時,沒有人抱著,往后翻過去,也沒能抱到他,一時之間門便有些委屈,腦子也不太清醒,沒想起來那麼多,眼睛都還沒來得及全睜開,就出手機來給他打電話了。
此刻回想起來,自己近來似乎黏他黏得有些過分了。
不過如今的周芙沒有半點心虛,黏人也坦,直截了當說:“醒來沒到你。”
陳忌扯壞笑了聲,拖腔帶調的,語氣極其和:“那行,你等著,一會兒到家了給你個夠。”
周芙:“……”
周芙這會兒多說了幾句話,腦子也不像剛起來時那麼迷糊了,想了想,又繼續問他:“接到咕嚕了嗎?”
“還沒有。”陳忌隨口扯了句,并不想在面前提起任何關于付其右的事,只說,“剛剛見完甲方,現在正在醞釀緒。”
周芙有些懵,順著他的話接著問:“醞釀什麼緒?”
“和你異父異母的親哥哥見面,不提前醞釀醞釀緒,不然一會兒忍不住打起來怎麼辦?”陳忌角輕勾著,面上帶著笑意。
周芙也忍不住笑出聲:“陳忌,你有病。”
男人哼笑一聲:“說什麼呢,周芙,你有點兒良心,小心一會兒回去收拾你。”
周芙:“……”
安靜了幾秒鐘。
兩人都沒說話,卻也都沒舍得把電話掛斷。
片刻后,周芙裹在被窩里舒舒服服的抱著枕頭,說:“你不是早就知道申城和凌路雨是一對的嘛?”
明明上次四個人見過面一塊吃過飯后,他就已經知道他倆的那層關系了。
可不知道怎麼還是有醋可吃。
陳忌那頭沉默了會兒,須臾,他淡淡開口:“因為嫉妒。”
周芙眨眨眼,沒懂:“嗯?”
“他們和你從小一塊長大,參與過你過去十多年我不曾參與的人生,所以不管你們是什麼關系,我都很羨慕,很嫉妒。”
周芙張了張,愣住,從沒想過會是這樣的原因。
小姑娘得很,眼眶漸漸有了意,癟著,心頭揪了揪,良久后說:“沒關系,我們有以后。”
“以后的人生,都有你參與。”
“嗯。”陳忌應了聲,而后語氣又忽然變為吊兒郎當,滿不正經補充了句,“我會盡全力負距離參與。”
“?”
周芙反應了半分鐘。
“!”
臉頰后知后覺地灼燒起來。
“……”
一個小時之后,陳忌回到家門口。
周芙聽見聲響,忙從床上下來,拖鞋也沒顧上穿,打著赤腳噠噠噠跑到玄關給他開門。
屋外,男人一手拎著貓包,一手拎了個三層的大蛋糕。
周芙愣了下,就聽見陳忌淡笑了聲說:“生日快樂,我的寶貝。”
周芙這才想起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是個特別容易的人,聞言便想撲到陳忌上要抱抱。
然而換做往常,陳忌對的主毫無招架之力,幾乎是全盤接收,并且十分。
可是今晚下意識往后退了一步,只將手中貓包遞給,說:“先和咕嚕玩會兒,我去洗個澡再抱。”
周芙眨了下眼,眸中帶著些不解。
陳忌輕描淡寫地解釋道:“今兒見的那甲方了不煙,上味道不好。”
周芙點點頭,也沒想太多,蹲在貓包前,手拉開拉鏈,將咕嚕從里頭解放出來。
好多天不見,早就想死它了,此刻抱著一個勁兒地吸。
陳忌垂眸睨了兩秒,笑了下,自行去了浴室。
去過祿戚山莊那地方,不洗就抱,他可舍不得,嫌晦氣。
陳忌在浴室里折騰了半個多小時,出來時換了居家的睡。
和周芙方才上穿的那套睡是同系列男款。
天知道剛才小姑娘從里頭開門,想要往他上撲的時候,他有多麼心和難以克制。
此刻洗過澡出來尋,見正孩子氣地趴在餐桌上,著生日蛋糕上的櫻桃梨吃,陳忌腳下忍不住地朝的方向靠近。
大手從周芙后圈上,微俯下,下顎搭在頸窩,不自覺深吸一口氣:“好香。”
周芙臉頰控制不住燒了燒。
良久,他從周芙上起,懶洋洋去了客廳。
回來時拖了一箱東西到周芙面前。
小姑娘眨了下眼,還不知:“是什麼?”
這箱子在倫敦也見到了,回來時,陳忌還特地將它們一塊帶了回來。
“禮。”陳忌隨手將箱子打開攤在地上,而后將里頭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擺到周芙面前,“你走之后的八年,每一年的生日禮,我都準備了,好在今年終于能送出手了。”
周芙愣在原地,看著他一個接一個給自己介紹。
周芙眼眸紅紅,癟著,也顧不上看禮,黏黏糊糊往他懷里蹭:“你干嘛對我那麼好啊。”
“喜歡你啊。”陳忌答得不假思索,理所當然。
周芙吸了吸鼻子,說:“你八年前在今塘送我的第一個生日禮,我也一直留著。”
陳忌表一滯,而后迅速恢復如常:“嗯,我知道。”
周芙被他抱起來,放回餐椅上。
“給你點蠟燭許愿。”
周芙想了想,覺得自己如今已經很幸運很幸福了,似乎沒什麼愿要許,于是抬頭看向陳忌:“我好像沒什麼心愿了,不如把這個愿讓給你吧?”
陳忌眉梢輕挑了下:“那我許你晚上求著我多弄幾次”
“……”
周芙:“我收回愿自己許。”
男人輕笑了下。
蠟燭熄滅之后,陳忌切了塊水果糖霜最多的給,周芙滿意地吃了幾口,想到八年前在今塘的那個大蛋糕,說:“你還記得這家蛋糕店啊?你八年前也給我買過。”
陳忌“嗯”了聲:“你說過你以前的每一個生日,都是吃這家的蛋糕過的。”
只要周芙說過,他就一定會記得。
小姑娘彎了彎,招呼他一塊吃。
陳忌對甜食興致缺缺,不過為了不掃的興,還是陪著吃了一小塊。
周芙一邊吃,一邊漫無目的地聊著:“你那時候在今塘,是怎麼買到北臨的蛋糕的來著?”
陳忌隨口一提:“不是和你說過,那會兒路澤舟在北臨讀大學,正好圣誕前要來北臨,就讓他幫忙帶了,搭著飛機來的。”
周芙點點頭,回想起確實有這麼回事,下一秒,啃著蛋糕的作一頓,猛地抬眸看向陳忌:“你說是誰帶的蛋糕?!”
陳忌眉梢輕挑了下:“路澤舟。”
周芙驚得眼睛都圓了不,語氣激道:“是最近特別火的那個歌手對不對?!”
陳忌:“?”
“他確實干過這行沒錯,但是你這個表是怎麼回事?”男人語氣染上酸味。
周芙連蛋糕都顧不上吃了:“啊啊啊啊!真的是他?!他最近超火的!音樂會門票一秒搶空,想買都買不到!超帥的。”
陳忌:“?”
男人臉沉下來:“行。”
“周芙你可真行。”
小姑娘眨了下眼,就見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轉就走。
“你去哪啊?”
陳忌語氣淡淡:“做晚餐。”
周芙一邊吃著蛋糕,一邊了下,問:“晚上吃什麼呢?”
陳忌冷冰冰留下兩個字:“豆腐。”
周芙現在對這兩個字已經有條件反了,脊背一僵,弱弱說:“怎麼……我過生日,你還收禮呀……”
男人不咸不淡冷笑一聲,反問道:“老子不就是你最好的生日禮?”
周芙:“……”
夜里,陳忌送起禮來,可謂是盡心盡力。
周芙的嗚咽被他全數吞下,興致上頭之時,男人掐著腰間門,啞著嗓問:“路澤舟和我,誰更帥?”
周芙這會兒雙眼失神,兒沒法思考:“……嗯?”
陳忌磁沉的嗓音環繞在耳畔:“我是誰?”
周芙帶著氣音,努力出兩個字:“阿忌……”
陳忌不依不饒:“誰更帥?猶豫一秒多做一次。”
周芙:“……”
猜你喜歡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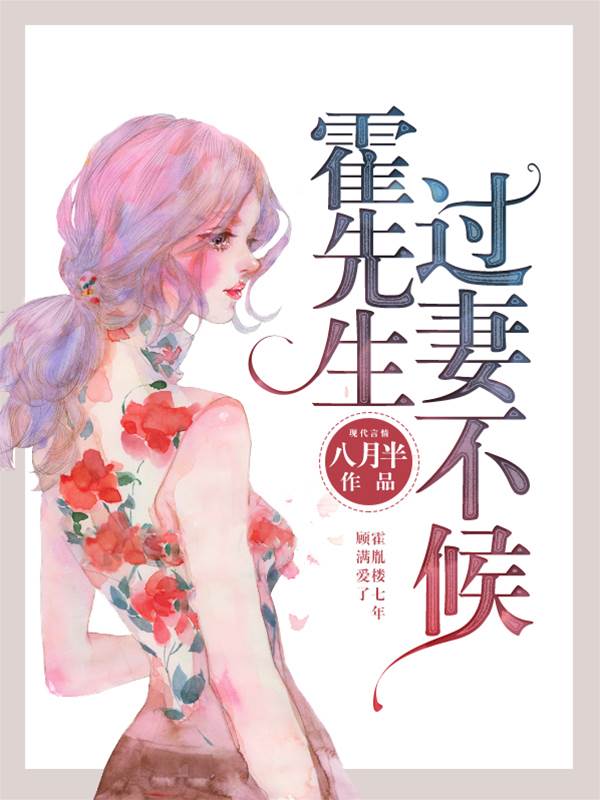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09 -
完結283 章

獨占偏寵
葉奚不拍吻戲,在圈內已不是秘密。一次頒獎典禮上,剛提名最佳女主角的葉奚突然被主持人cue到。“葉女神快三年沒拍過吻戲了,今天必須得給我們個交代。”面對現場追問,葉奚眼神溫涼:“以前被瘋狗咬過,怕傳染給男演員。”眾人聽後不禁莞爾。鏡頭一轉來到前排,主持人故作委屈地問:“秦導,你信嗎?”向來高冷寡言的男人,笑的漫不經心:“女神說什麼,那就是什麼吧。”*人美歌甜頂流女神VS才華橫溢深情導演。*本文又名《返場熱戀》,破鏡重圓梗,男女主互為初戀。*年齡差五歲。*男主導演界顏值天花板,不接受反駁。
52.6萬字8.18 6381 -
連載368 章

少帥既然不娶,我嫁人你哭什麼
楚伯承像美麗的劇毒,明明致命,卻又讓人忍不住去靠近。可他們的關系,卻不為世俗所容。姜止試圖壓抑感情,不成想一朝放縱,陷入他的牢籠。他步步緊逼,她節節敗退。一場禁
65.8萬字8.18 18639 -
完結507 章

離不掉!高冷佛子為我墜神壇
【追妻火葬場 雙潔 假白月光 虐男主 打臉發瘋爽文】“離婚吧。”傅樾川輕描淡寫道,阮棠手裏還拿著沒來得及給他看的孕檢通知單。整整四年,阮棠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一場車禍,阮棠撞到腦子,記憶停在18歲,停在還沒愛上傅樾川的時候。麵對男人冷酷的嘴臉,阮棠表示:愛誰誰,反正這個戀愛腦她不當!-傅樾川薄情寡性,矜貴倨傲,沒把任何人放在心裏。阮棠說不愛他時,他隻當她在作妖,總有一天會像從前那樣,哭著求他回頭。可他等啊等啊,卻等來了阮棠和一堆小鮮肉的花邊新聞。傅樾川終於慌了,將人堵在機場的衛生間裏,掐著她細腰,聲音顫抖。“寶寶,能不能……能不能不離婚?”
88.1萬字8.18 184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