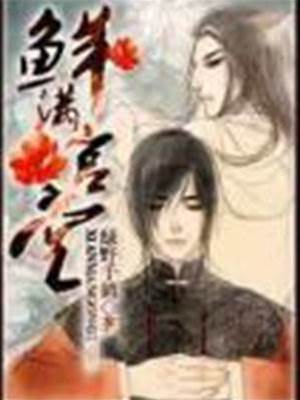《不能說的事》 第120章 回到高一
電影還在放著,曲很輕,如同人的呢喃。
黃單聽到周圍的竊竊私語,才知道男人已經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問題,他把淺的抿上,松開了,又抿,這個細微的作暴著他的不平靜。
“陸匪,你別哭。”
陸匪用手捂住臉,頭埋在膝蓋裡,哭的整個子都在。
黃單索著到男人的頭發,他輕輕了,“只是暫時的,我會好的,不要哭了。”
陸匪的嚨裡發出哽咽,一聲接著一聲,他的憤怒,悲傷,恐慌都在頃刻間噴湧而出,絕在心底滋生,“嘭”地一下炸開了,五髒六腑都不了的痛。
黃單的耳朵邊只有男人抑的哭聲,他心裡難,莫名覺得這次的任務有一個月期限,是三哥在暗示他,時日無多了。
電影散場,們從男主人公的裡離出來,和自己的另一半膩歪著往外面走,他們有說有笑。
那種幸福的氛圍跳過了一,明顯的沒有統一對待。
陸匪嘶啞著聲音,“手給我。”
黃單到男人的手臂,把收放進他寬大的掌心裡面。
陸匪牽著他起,“回家。”
黃單走的慢,每一步都走的很陌生,好像腳下的路已經不是來時走的那條,充滿了未知。
陸匪扣著青年的手指,“怕就抓進我的手。”
黃單說他不怕。
陸匪通紅的眼睛裡滿是痛苦,“不是說自己運氣好嗎?這就是你說的運氣好?!”
黃單說,“我只是暫時的失明,跟別人比起來,已經很好了。”
陸匪說誰要你跟別人比了?“為什麼要跟別人比?季時玉,你必須要給我好起來,聽見沒有!”
黃單蹭蹭男人掌心裡的汗,“聽見了。”
他的腳邊沒有障礙,卻還是不控制的踉蹌了一下。
周遭人聲嘈雜,黃單聽到男人的聲音,從他前面發出來的,帶著不容拒絕的霸道,“上來。”
他手去,到了實的背部。
陸匪催促。
黃單趴上去,手摟住了男人的脖子。
陸匪背起青年,“輕點,你想勒死我?”
黃單松了手。
陸匪又發脾氣,“為什麼不摟著我?你想摔下去嗎?”
黃單說,“陸匪,冷靜點。”
陸匪重重氣,直覺一腥甜往上泛,“冷靜?你讓我怎麼冷靜?要是瞎了的是我,你能冷靜?”
黃單不說話了,他的索著到男人的後頸,落下安的痕跡。
陸匪淚如雨下。
一天,兩天,三天……黃單的視力都沒恢複,他知道自己完全看不見了。
失明對他來說,是一次從未會過的,整個世界都是黑的,像是有一盞燈壞了,或許很快就能維修好,也有可能永遠都無法修複。
在那個黑的世界裡面,有個聲音陪著黃單,有雙手牽著他往前走,給他溫暖的懷抱。
陸匪不去公司,一顆心都在黃單上,只想做他的眼睛,做他的手腳。
黃單起初只是眼睛看不見,後來手也出現了問題。
那天晚上,陸匪把黃單帶到衛生間的水池邊,給他了牙膏遞過去,他手去接,發現手不聽使喚。
黃單在一片死寂中喚了聲,“陸匪。”
陸匪啞聲說,“我在。”
黃單的眼瞼了,“明天帶我去醫院吧。”
陸匪說好,他舉起牙刷,“陸太太,張。”
黃單乖乖張,有薄荷味沖進齒間,他任由男人給自己刷牙,聲音模糊的說,“這是我第一次讓別人給我刷牙。”
陸匪的聲音裡帶著濃重的鼻音,“這也是我第一次給別人刷牙。”
他抹掉青年角的牙膏沫子,“陸太太,你先生這輩子就沒這麼伺候過誰。”
黃單說,“我知道的。”
“知道還不夠,你要記著,別給忘了。”
陸匪把漱口杯遞到青年邊,“漱漱口。”
黃單的齒到杯口,他咕嚕咕嚕漱口,“我會一直記著的。”
陸匪總是著的角勾了勾,“知道我的好了吧?怎麼樣?到了沒有?”
黃單心說,第一次聽的時候就到了。
有時候,從天堂摔下來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摔進地獄,摔進深淵。
陸匪在醫院裡發火,要不是黃單阻止,他能把人辦公室給砸了。
生死由命,強求不來。
黃單再努力鍛煉,都控制不了那些腦出帶來的癥狀,他半夜會醒過來,在枕邊到人才能安心。
因為陸匪前幾天半夜都在外面煙,一晚上幾包,中間不帶停的,他在慢自殺。
直到黃單夜裡要到他,他才沒有再跑出去煙。
陸匪全世界的給黃單找醫生,尋方子,就想他活的久一點,再久一點。
黃單什麼時候都配合著,他怕自己哪天不能說話了,就總是找話跟男人說。
陸匪看出來了,一邊嫌他嘮叨,一邊回應,不知不覺就紅了眼睛。
“你天天醒來就跟我扯閑篇,嗓子有沒有事?”
黃單說,“你忘了,我不痛的。”
陸匪咒罵,“媽的,誰忘了?你不會痛,其他覺總有的吧?別他媽的不把自己當回事,季時玉,你是我的,全部都是!”
黃單,“好哦,我是你的,全部都是。”
陸匪的心一下子就疼了起來,疼的無法呼吸,他死死皺著眉頭在床前踱步,又走回去,俯在青年沒有的上碾||,啃||咬。
黃單的臉上沾了一滴溫熱的,他手去,到男人的眼睛,“哭了?”
陸匪的舌頭探進去,將青年裡苦的藥味卷走了吞咽下去,他的額頭抵著青年,沉沉的說,“被你氣的。”
黃單對他笑,“別氣了。”
陸匪的嚨裡發出模糊不清的聲音,似是哽咽,“你讓我別氣了,我就能不氣嗎?”
話落,陸匪就把青年拉起來,一手扣著他的腰,一手扶著他的手臂,“多走走,別老躺著,你乖乖的,就不生氣。”
黃單嗯了聲,“我乖。”
陸匪側低頭凝視著青年蒼白的臉,他扯扯皮子,沖他出一個溫暖的笑容,哪怕他看不見。
眼看都冬了,兒子還不回家,陸父陸母就找了過來。
他們一進大廳就察覺到了不對勁。
家裡的生活用品都是雙人的,但是就沒見那個孩子的影。
陸母問道,“他呢?”
陸匪說,“睡了。”
“大白天的就在房裡睡覺?年紀輕輕的,一點都不上進。”
陸母打量著兒子過於消瘦的臉,“你怎麼回事?這才多久,怎麼就瘦的沒人樣了?”
陸匪沒給回應。
陸母盯著兒子,“你不說,爸媽也能查得到。”
想到了什麼,腦子裡有塊,迫了神經,好不到哪兒去的,卻能壞到難以想象。
“人是不是癱了?”
陸匪要端茶喝,被他爸給攔下來了“你媽問你話呢!”
他淡淡的說,“就是那樣。”
陸父陸母聽到兒子的答複,他們滿臉駭然。
癱了就是個生活不能自理的廢人,瑣碎的事多起來能讓人崩潰,他們不能理解,兒子跟那孩子非親非故的,怎麼還能這麼淡定的把人留屋裡。
“你有什麼打算?手呢?能做就給他做了,風險大是肯定的,就算不幸死在了在手臺上,也總比一天天的痛苦下去好,那種折磨沒人的了。”
陸母說,“要是他不願意,就把他送到最好的醫院去,那裡會有專業人員照顧。”
陸匪還是那種語氣,“他哪兒也不去,就在這裡住著。”
陸父拍桌子,“這是說的什麼混賬話?你以為自己是誰?不是醫生不是護士,讓病那樣的人住在這裡,你是想他早點死嗎?”
陸匪說,“爸,你跟媽別一口一個死的,我聽著刺耳。”
陸父看兒子深陷下去的眼窩,快瘦到皮包骨的樣子,他心裡就堵得慌。
有一瞬間,陸父都在想,算了算了,只要人過來,就讓他們在一起吧。
可是老天爺的心思誰能猜的到?
陸母跟老伴換了一下眼,老兩口沒走。
下午陸母就等到了機會,趁兒子分不開,立刻推門走進臥室。
黃單的眼睛是閉著的,他看不見,一邊的耳朵還能聽,“伯母,是你嗎?”
陸母驚訝他的敏程度,“小季,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黃單沒說話。
陸母握住他的手,“醫院是怎麼說的?做手的話,有幾把握?”
黃單搖了搖頭,“做不了。”
陸母語重心長,“為什麼做不了?是風險太大了,陸匪不同意你做?還是你自己的意思?小季,即便手功的幾率只有一,也比你這樣惡化下去好。”
黃單說,“我想多陪陪他。”
陸母的耐心還在,“你現在的狀態是什麼樣,自己應該很清楚,能撐多久也不會不知道,繼續留在他的邊,只會拖累他。”
黃單說的比更直白,“在我死之前,我不會離開。”
陸母的雙眼睜大,的耐心瞬間消失幹淨,一把就將青年的手甩開了,“之前我覺得你天真,現在才知道你最厲害的地方是自私!你明知道自己活不長了,為什麼還要拖著他?”
說到後面,陸母不顧形象的呵斥,失態了,這個孩子的心看不,不是無私的嗎?不是只要對方過的好就可以了嗎?為什麼要著不放?
黃單在這個世界學會了依賴的同時,也學會了自私,純碎的自私。
他變了自己陌生的樣子,卻不能排斥,也不想去排斥。
“伯母,我不會放手的。”
陸母氣瘋了,抬起一只手就往青年臉上揮下去,被沖進來的陸匪給抓住了撥開。
陸匪不言語,也不咒罵,不發怒,只是看著他媽,用的是一種從未出現過的目。
陸母傷了心,頭也不回的摔門出去。
房裡安靜了下來。
黃單的神很差,他輕聲問道,“天黑了?”
陸匪看一眼窗外,明,他的頭滾,“嗯。”
黃單說,“布丁怎麼沒?它該吃晚飯了。”
陸匪他的頭發,“盤子裡有狗糧,它了就自己去吃的。”
黃單哦了聲,就慢慢的睡去,他從始至終都沒提陸匪爸媽的名字。
日子不多了,別人的事黃單不想去費心思,他就想在這個世界多待一天,就多跟男人說說話。
時間流逝的有多快呢,黃單只覺得下了幾場雨,刮了幾夜大風,他就有了要離開的預。
夜裡黃單說,“陸匪,我要走了。”
陸匪蹭著他的臉,“走哪兒?”
黃單說,“走了就是走了,你別找我,找不到的。”
陸匪猝然抬起頭,眼睛猩紅一片,“誰他媽的說要找你了?走吧,快點走!”
黃單難過的說,“我不想走的。”
陸匪趴在青年的心髒部位,聽著一下一下的心跳聲,“沒良心……季時玉你真沒良心……說不想走,為什麼就這麼輕易的放棄?”
他抓住青年的手放在邊,“我知道你堅持不下去了,我都知道的,季時玉,再堅持一下,算我求你了,求你了……”
黃單睡著了。
第二天,黃單一邊的子就沒了知覺。
雪後放晴,從外面看,城堡華麗而又壯觀,誰也不知裡面如同一座墳墓。
最嚴重的後果還是發生了。
黃單的不能,聽不見,看不見,說不了話,吞咽困難,他的意識是清醒著的。
陸匪的緒越來越暴戾,他把家裡砸的一片狼藉,而自己就蹲在那片狼藉裡面痛哭。
沒人罵他,他也就無所謂了。
柴犬都不敢從陸匪邊經過,老遠就繞開了。
小年夜那天,陸父陸母接到陳的電話,才知道出了大事,他們二老急忙從家裡趕了過來。
陳把事說了,無非就是有個生命沒了,
陸母好半天才反應過來,“陸匪呢?我兒子人呢?他在哪兒?”
陳說在樓上。
陸母跌跌撞撞的跑上樓,陸父在搖晃時及時扶住了,“慢一點。”
“老板不開門。”
跟過來的陳言又止,“他的樣子很不正常。”
陸母慌了神,“什麼不正常?”
陳回憶前不久的一幕幕,心底依舊發涼,帶著幾個醫生過來,到這兒時,人已經死了。
老板卻是說他懷裡的人沒死,還有氣,他大聲吼,當時那模樣,像極了瘋子。
做了次深呼吸,陳書描述了一下看到的形。
陸母聞言,整個人都炸了,扭頭看老伴,布滿皺紋的眼角潤。
“那孩子最初像模像樣的我給他一年時間,前段時間我讓他離開,他不肯,現在這算什麼?自己命薄不了福走了,為什麼還要禍害我們家?他到底是什麼居心?不行我要進去看看。”
陸母大力拍著門,氣的渾發抖,“陸匪,你給媽把門打開!”
陸父歎口氣,“人都已經不在了,還說這些幹什麼?”
“幹什麼?你說幹什麼?”
陸母瞪著他,“你沒聽陳說嗎?兒子連個人樣都沒有了!”
陸父抹把臉,幾次想開口都不知道說什麼。
那孩子就是再有什麼不是,也怪不上了。
人死如燈滅,生前的事,多說說都沒區別。
陸母在門外來回踱步,“老陸,我們雖然對他不滿意,可也沒有真的怎麼著他,這都是他的命。”
陸父開了口,“你的意思是說,這也是兒子的命?”
陸母一下子就失去了聲音。
三十而立的年紀才遇上一個喜歡的人,結果剛擁有就失去了,所有的憧憬跟規劃都變一堆浮泡影。
人都不在了,想再多又有什麼用?
這樣巨大的打擊,沒有人能承的住。
陸匪不吃不喝,也不辦後事,就那麼把自己跟一關在房間裡面。
陸父陸母哪兒都沒去,就在門外守著,不停對門裡的兒子說話,嗓子啞了,人暈過去,醒來了繼續喊。
第三天,房門開了。
不是陸匪從裡面打開的,是陸父終於指使了保鏢,讓對方跟另外兩人流將門踢開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嫁給暴君的男人
何箏穿成了暴君的炮灰男寵。 仗著美貌與可生子體質,自以為與暴君日久生情使勁作死,最終被暴君親手解決,死無全尸的那種。 最可怕的是,他正好穿到了被獻給暴君的那天晚上,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等著暴君的到來—— 何箏:救、命!! 很久之后,暴君立后從良,修身養性,一個更讓人皮緊的消息卻迅速蔓延: “你猜,這宮里誰最可怕?” “是何皇后。你若多看他一眼,陛下就會親手挖出你的眼睛。” 偏執陰狠占有欲爆棚攻X盛世美顏弱小可憐但能作受 一句話簡介:雖然害怕,但還是要作死。 *非典型宮廷甜文,狗血生子還鬧心,攻寵受先動心,感情為主劇情為輔。 *不要用現代人的三觀來要求攻,也不要用古人的三觀來要求受。 *考究黨注意,本文各種設定怎麼順手怎麼來,請勿代入歷史任何朝代。
27.5萬字8 10029 -
完結168 章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1. 顧元白穿成了耽美文中存在感稀薄的病弱皇帝,皇帝是個背景板,全文都在講著攝政王和京城第一美人的掌權史和相戀。 顧·野心勃勃·元白:我笑了。 他都是皇帝了,怎麼可以不掌權天下,不去開疆擴土名留青史呢? 2. 這一日,暗藏熊熊野心的當今大將軍之子、未來攝政王薛遠,頭次隨著父親進了宮。在人群之后抬頭一看,卻瞥見了這年輕天子的容顏。 天生反骨的薛遠唇角一勾,輕蔑地想,這小皇帝怎麼長得比娘們還漂亮? 身子病弱容顏太盛,這拿什麼治理大恒。 拿體弱嗎? 3. 薛遠冒犯了顧元白之后,被壓著帶到顧元白身前。 顧元白輕聲咳嗽著,大雪紛飛落滿了他的肩頭,薛遠面色陰沉。 “朕心情很不好,”顧元白輕瞥了一眼未來的攝政王,柔柔一笑,啞聲道,“別惹朕不開心,明白了嗎?” 薛遠像條瘋狗。 可顧元白什麼都不怕,他只怕不夠刺激。將瘋狗馴成忠臣,這恰好讓他以病弱之軀覺出來了另一種挑戰了。 可一不小心,好像馴得過了頭。 【甜爽文】 【cp薛遠,瘋狗攻,雷慎入】 【很多細節和原因在后文才會揭示,前文時稍安勿躁呀】 排雷: ①架空爽文,大亂燉,勿考究,有bug ②攻很狗,很討人厭! ③受強,野心勃勃,但身體病弱,萬人迷 ④原文攻受沒有愛情,彼此認為對方對皇帝心懷不軌 ⑤祝看文愉快,微博@晉江望三山s
55.9萬字8.18 5608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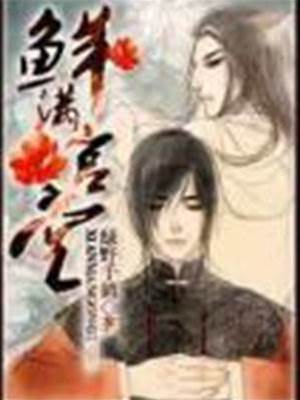
鮮滿宮堂
海鮮大廚莫名其妙穿到了古代, 說是出身貴族家大業大,家里最值錢的也就一頭灰毛驢…… 蘇譽無奈望天,為了養家糊口,只能重操舊業出去賣魚, 可皇家選妃不分男女,作為一個貴族破落戶還必須得參加…… 論題:論表演殺魚技能會不會被選中進宮 皇帝陛下甩甩尾巴:“喵嗚!”
35.5萬字8 7261 -
完結340 章

末日快樂
天才科學家阮閒昏迷數年,一睜眼腰不痛了,腿痊癒了,人也能蹦躂了。只可惜門外人工智能失控,人類末日早已降臨。 好在他的運氣沒用光,成功捕捉了一位生存力極強的求生搭檔。 唐亦步:咱倆這種古舊機型,特容易報廢。 唐亦步:記著點,保證安全的首要原則——千萬別和人類走得太近。 阮閒:……等等? ? ? 人工智障攻 × 盲目樂觀受 末世背景,最強人工智能及其創造者掙扎求生(?)的故事。 強強/HE;
100.2萬字8 60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