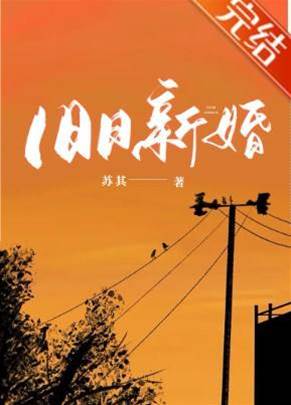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心跳陷阱》 第59章 第59章
這一晚林綿格外主, 仿佛要將所有回應都化為實質的擁有。
江聿仰著脖子,青筋暴起,滾燙的汗水沿著青筋往下淌, 滴進鎖骨亦或者順著奔涌往下匯聚。
燈的照下, 他上薄汗泛著一層薄,宛如雕塑般鬼斧神工的構造,完到無暇,腹部微微痙攣著。
他一只腳先踩到地上, 起伏的膛重重換了口氣。
薄汗匯聚在刀削般的下頜, 手心抹了一把汗,低頭去親人, 長臂拉開屜, 勾出一個盒子, 指尖去剝包裝袋。
床上的人聽見靜,潤的睫了又,他手一頓,停下來俯問:“我聽你的。”
他的意思很明顯,主權在。停就停。
林綿不用看也知道,的小獅子此刻有多神,像是狩獵很多天終于逮到了獵,眼底出的鋒芒, 危險卻又充滿了吸引力。
見不回答, 他手指勾著盒子準備放下。誰知道, 手腕突然被捉住,抬起漉漉第臉, 一雙漆黑眼眸如水洗過, 洇開瀲滟水汽, 瞧著他,飽滿的瓣揚起優雅弧度“你不想把錯過的三年都補起來嗎?”
江聿忽地勾,再也無所顧忌,暗自發誓就算著嗓子老公,他也絕不心。
沒有拍攝的日子,聞妃給林綿放了個假期。
小兩口從結婚之后,還沒正兒八經一起過,《逐云盛夏》開機前,計劃著要去山里玩,也一直沒兌現。
現在倒是有了空閑,江聿計劃著去山里住幾天,過幾天沒人打擾的日子。
林綿卻擔心他的公司。
會不會被他這麼三天兩頭不在公司玩垮了。
沒想到,傍晚林綿在財經節目看到了年輕有為的老公,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地跟主持人侃侃而談。
他從容自信,骨子里倨傲和矜冷,面對主持人拋來比較尖銳問題,拆解合理,回答得游刃有余,不疾不徐的態度讓主持人出了欣賞的表。
江聿進門時,正好看見林綿盯著電視里的自己發愣,他彎腰換鞋,掉外套,放在椅子上,走到林綿邊抱住,吻了下額頭。
“很帥。”林綿側過頭看他。
“哪天不帥?”
林綿他鬢角,“可是我喜歡你穿t恤工裝。”
“穿給你看。” 雖然老公西裝革履的樣子堪比男模,還經常上熱搜,但畢竟不是心里的樣子。
江聿咬住手指,舌尖掃過指尖,溫,的臉頰一下就紅了。
江聿理完公務,組織的山里小住也拿上行程。喻琛得知后也吵著要帶上黎漾。
江斂也跟著湊熱鬧,這件事不知怎麼的傳到了江玦未婚妻那邊,江玦未婚妻也表現出濃郁的興趣。
也不知道江玦是對往事耿耿于懷,還是對新未婚妻的無興趣,總之在對方提出來之后,他幾乎想也沒想就否決了。
出發前一天,喻琛又跟黎漾吵架了,喻琛懨懨的對山里行也沒那麼向往,他倚在車門,跟江聿借了火煙。
“黎漾怎麼還沒到?”
喻琛咬著煙搖頭:“不知道。”
多存在賭氣分,語氣有些重。
指尖煙霧裊繞,籠罩著眼前有些模糊,半瞇著眼眸,瞥見兩道人影緩緩走過來。
他摘了煙,冷不丁地盯著不遠,手拂開擋在眼前的煙霧,終于看清了兩人,火氣蹭的一下冒起來。
喻琛丟了煙,語氣不大不小,低罵了一句:“他來做什麼。”
江聿背對著他們,聽了喻琛的話,轉過去,黎漾和行年剛好走進,黎漾先開口:“不介意我多帶個朋友吧?”
喻琛惡狠狠盯著黎漾,眼神仿佛要吃人,要將上的一塊一塊撕下來嚼碎吞下。
黎漾卻仿若未聞,有說有笑跟江聿閑聊,過后介紹行年和江聿認識。
林綿聞聲下車,看到行年也意外了幾秒,禮貌地跟他頷首打招呼。
行年這人很高,上有種狂的氣質,與喻琛他們這些矜貴公子哥完全不同,所以他的迫也是從骨子里出來。
無形中與喻琛無聲較量。
喻琛面不虞,眸沉沉,盯著黎漾不快道:“家庭聚會,你沒提前打招呼,沒準備那麼多車。”
其實這話就有點假,江聿和喻琛放在車庫的存車誰不知道,他不過是不想給行年臺階。
行年面始終淡淡的,他可能還沒意識到自己于風暴中心,也不全無意識,所以他牽薄:“不用麻煩了,你們在前面帶路,我開車。”
鐵了心要摻一腳。
喻琛繃著下頜,面慍怒,深深看了一眼黎漾,便回了車里。
林綿跟江聿對視一眼,黎漾扶著林綿肩膀,把往車里推,林綿捉住的手低聲問:“你真的不會玩翻車嗎?”
黎漾眨眨眼睛,視線不經意往車瞥了一眼,湊到林綿耳邊說:“翻什麼車,喻琛又不是我什麼人。”
“你們不是?”不是嗎?林綿腦子里過了一遍,他們的關系好像比還復雜,很難界定。
“是什麼?炮//友嗎?”黎漾扯:“本來就是各自玩玩,誰當真誰是傻子。”
說完,將林綿塞車里,然后轉去到行年邊,“走吧。”
有了小曲,一路上車氣極低,江聿雙手扶著方向盤,舌尖頂著齒,沉默了幾息,打開了車載音樂。
“ a pool side bar/olf cart”
“你和我,日落時醉醺醺地在游泳池邊的酒吧里啜飲,在破舊的高爾夫球車里接吻“”
“told you that i loved youthe first 5 es ,if love pgit”
“告訴你我在前五分鐘遇見你便已經傾心,若是海洋,你我便縱而躍”
喻琛的臉并沒有因為音樂而好轉,靠在座椅上,雙目微闔,眉心蹙,周散發著冷冽氣息。
江聿也覺著黎漾上行年離譜,扯無聲笑了下。
好事多磨,睡覺喻琛這人平時缺德事做多了,走夜路撞鬼了吧。
車子進山,空氣就變得清新很多,沁的空氣里彌漫著植的香氣。
一個半小時候,他們抵達了喻琛家的度假山莊。
常年給經理打理,喻琛只有在每年年底才過來走一趟,多數時候他對下面這些管理者陌生。
經理得知大老板和朋友們要來玩,提前就吩咐準備,早早地候在大門口。
歐式的大噴泉鑲嵌在矮小的灌木叢中。
浮夸的雕塑,造型各異的植,七彎八繞的車道,遠遠能瞧見歐式城堡般的主樓,但車緩緩駛,四周植錯,仿佛進了一個植迷宮。
行年的車隨其后,高大越野車跟他的人一眼,充滿迫力,猶如一個巨型猛。
泊了車,經理領著人上樓,拿到了房卡。
本來是兩個人月,他們非要把事弄復雜,江聿不想再摻雜奇怪的三角關系,他現在很困,想要抱著香香的老婆溫存。
他懶散地跟喻琛打完招呼,拉著林綿直奔房間。
等到遠離三個人,林綿才低聲慨:“喻總好慘啊。”
江聿起倦怠的眼神看:“哪里慘?”
林綿扯:“不要生行年的氣,還要給行年提供住,不慘嗎?”
這就是還不夠了解喻琛,他是不會吃癟占下風的。江聿的手背,放低了聲音:“不許想別人。”
醋勁兒就是這麼大。
林綿牽住他的手指,不輕不重地著,回他:“沒想。”
兩個人回房間睡了一覺,醒來時,林綿穿著睡,盤坐在沙發上,頭發松垮地挽在腦后,可能因睡覺而松散,幾縷飄至脖頸勾纏著,襯得雪頸修長。
低了聲音講著電話,手指無意識摳著抱枕。
對方說了什麼,輕微彎,點頭連連“嗯”了兩聲,道謝。
江聿醒來時,旁不見人,他恍惚了幾秒,才記起是在度假山莊,耳邊傳來林綿輕聲細語,他重重吐了口氣,跌回被子里,閉上眼睛養神。
將醒未醒那一瞬,他以為又被夢魘住,回到三年前的那個昏暗的早晨,醒來懷里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
往后三年,他都沒過抱著人睡覺的溫度,卻每天睡醒都重復著失去的痛,心臟像被撕裂,痛那麼明晰。
后來,他便不敢輕易睡,害怕睡著醒來,再會一次失去。
也是林綿回到他邊,他的覺才慢慢回歸正常。
迷瞪了會兒,邊的床墊微微塌陷,林綿在床邊坐下,抓著他的雙臂晃了晃,“roy,還不起床嗎,我們要錯過晚餐了。”
綿綿的掌心在手臂上,毫無威懾力,反而像是小貓爪子一樣撓著,他故意不睜眼,假裝睡。
“我剛看到你醒了。別裝睡了。”林綿俯晃他。
離得近,氣息迫,他驀地睜開眼,對上水潤雙眸,手掌勾著的脖頸往下沉,薄尋到瓣,用力地上去。
須臾之間,便變換了位置,他手肘撐在邊,低弓著背接了個纏綿悱惻的吻。
“綿綿,別走了。”江聿脖頸垂下,灰白頹然地氣。
聲音很低,幾乎用氣聲吐出來,抑又無力。
林綿心口重重跳,被拉扯得酸發疼,急于抓住他,篤聲承諾:“我沒走,不會走。是不是做噩夢了?”
一滴淚悄無聲息的頸間。
半個小時后,喻琛打線電話,他們下去吃飯。
兩個人又磨蹭了會兒,才換服下樓。
三個人已經落座,氣氛古怪的很,林綿挨著黎漾坐下,在桌子上他手,用眼神流著。
黎漾一副心的不錯的樣子,打趣江聿:“小江總,眼睛這麼紅,是沒睡好?”
江聿往椅子上一靠,懶倦地垂著眼,不清不楚地“嗯”了一聲。
行年從口袋里拿出一盒薄荷糖,遞給江聿:“這個醒神效果不錯,試試。”
江聿意外挑眉,行年的眼神太過真誠,他不好拂了人家面子,接過來倒了一顆放進里。
冰涼頂的覺瞬間襲擊神經,他咬著牙齒,差點嘶出聲,冰涼的濃郁的薄荷氣息直沖天靈蓋。
他過了好幾秒才緩過神來,心想行年真變態,薄荷糖都吃高濃度的。
“怎麼樣?”行年見江聿面上沒什麼表,傾問了句。
江聿舌尖頂了頂口腔,才忍住那冰涼刺激,評價道:“夠勁兒。”
黎漾笑了一句:“他那個薄荷糖,真不是正常人能吃的。”
行年眼角有點疤,但不影響他帥氣的五,反倒一點疤痕顯得面部更加凌厲,廓分明朗。
他起眼皮看黎漾,目確是和的。
黎漾沒看他,視線從喻琛上飄過去,落到江聿那兒,開玩笑:“小江總,吃得慣?”
喻琛在桌上反扣手機,弄出不大不小的聲響,他沉沉視線看向黎漾,薄抿了一條直線。
江聿心不在焉,搖了搖頭。
一頓飯氣氛古怪,誰也沒主談的,飯后,林綿和江聿相約去運館打壁球,黎漾眼神瞟了一眼行年,行年淡聲開口:“我先回房間。”
黎漾也跟著起,勾著鏈條包起:“我去趟洗手間。”
上的香水味道清淡,經過喻琛時猶如攜來一陣溫香風,從四面八方纏住他的呼吸。
細的擺輕輕揚起,像是有意識般勾過他的,揚起又放下,擒故縱似的,消失在墻角。
喻琛眸轉深,靜靜坐了會兒,屈起手指在椅子扶手上無意識地敲著,隨著時間推移,去洗手間的人還沒回來,他的目一寸寸冷下去。
黎漾站在寬大明亮的鏡子前,慢條斯理地干骨節,看了眼時間,手機霎時響起。
行年打來的。
等待了幾秒,然后按下接聽,一手拿著手機,一手解開包包,取出口紅旋開蓋子。
蓋子一不小心蹦到地上,行年那邊低沉開口:“什麼靜?”
他的嗓音低而沉,猶如渾厚的紅酒,滲齒間,滿腔荷爾蒙游走,危險又人忍不住迷。
“口紅掉地上了。”黎漾揚起脖子,著鏡子去涂。
鮮艷的紅將的偏白的面容裝點的更濃烈,的五本就偏濃系,眉目深邃,富有攻擊,若是不涂口紅,氣場沒那麼強烈。
偏生紅,重紅,像一只帶刺的紅玫瑰。
可不是帶刺嗎,把喻琛扎得渾是傷口,他偏不怕,還要往眼前湊。
“掉了就不要了。再給你買。”行年強勢的做派,和他這麼多年經歷不可分。
黎漾揚起紅,口紅停在距離薄一厘米的地方,輕笑:“你倒是會哄人。”
行年低笑,“這不是你教的麼。”
黎漾放下角,抿得端直,隨手將口紅丟進垃圾桶,聽見行年說:“今晚我住下,明天一早就回去。”
也不知道是那句話讓黎漾不高興了,輕扯角:“隨你。”
黎漾掛了電話。
扣上包,就往外走,細長的高跟鞋剛踩上走廊的地面,一力道攬住肩膀,整個人都被推到了墻壁上。
后腦勺磕墻壁上發痛,肩膀上的大手力道大的驚人,像是要將碎了似的,越掙扎越疼。
男人黑沉沉的視線,如暴風雨前的凝聚的烏云,在上方不過氣來,黎漾陷在他廓里,顯得小無助,是一朵只要他想隨時可以掰碎的小白花 。
“你發什麼瘋啊。”黎漾烏眸瞪大,漂亮臉上薄怒,眼底蹙著一團怒火。
男人的雙臂如鉗,牢固而實,幾乎將鉗住不得彈,他扣著的腰,毫無還手之力就跌男人懷里。
一道聲線在頭頂落下:“你怎麼知道他的薄荷糖不是正常人吃的?你吃過?”
黎漾起眼皮,不敢置信看著喻琛,為了一盒薄荷糖至于嗎?
喻琛什麼時候這麼不理智。
認識喻琛可是拎得清,那得起放得下。
紅牽,挑著一抹笑,挑釁般地說:“沒吃過。”
喻琛著他腰的手松了幾分力氣,黎漾卻忽然不解氣,明知道他誤會了,還是故意說:“吻過。當然知道了。”
喻琛氣息一寸一寸近,繃著下頜,額頭青筋因為忍而鼓起,收手心力道的同時,灼熱兇狠地吻住。
薄怒在抵時達到了頂峰,又在丟盔棄甲時轉為和,余音被他吞嗓子里。放在腰間的手,微微松了力氣,緩緩放到的后背,著。
猜你喜歡
-
完結1223 章
爹地霸道,媽咪得寵著
(寧暖商北琛)七夕夜,她遭遇了人生中最混沌而旖旎的一夜,事後一顆種子在她肚子裡悄然發芽。八個月後,她當街早產上了本地新聞,生下的孩子卻被神秘男人帶走……外界傳聞,商北琛是冷血無情的商界新貴,就算仙女下凡也得圍著他轉,永遠都不可能反過來慣女人。卻不知背地裡,他親手把女人寵得睡覺有他哄,早餐有他喂,寵妻護妻,做錯了關起門來卑微的知道朝自己女人單膝下跪。【非無腦小白,1V1,男女主智商均在線。】
188.9萬字8.18 260884 -
完結54 章

長街
小姑娘向芋第一次遇見靳浮白她才剛剛失戀,蹲坐在角落裡獨自哭泣,靳浮白遞給她一件五位數的衣說:“墊著坐,地上涼”。第二次是在酒店裡,沒有多餘客房著急的向芋遇上穿著睡衣的靳浮白,他說“我住的是套房,你來麼?”她說“好呀,房費AA”。她以為兩人在也不會有第三次交集,可他竟查到她電話要請她吃飯,兩人曖昧纏綿卻不捅破那層關係,直到靳浮白說:“向芋你跟著我得了”。只是跟著,男女朋友都不是,這麼界限不清,向芋卻清醒的淪陷。
23.6萬字8.33 19707 -
連載1908 章

甜妻有喜:禁欲大佬寵上天
自家老婆太美太嬌太誘人,于是,是個男人都想覬覦。愛吃醋的二少為了把老婆藏起來,到處宣揚自己二傻子般的娶了一個丑八怪。結果,都這般宣揚了,還有男人找上門,“二少,把你老婆讓給我,條件你隨你開。”二少剛想拒絕,老婆大人沖上來,“你這般替我造搖,…
169.8萬字8 39263 -
完結672 章
昨夜星辰昨夜夢
新婚夜,素未謀面的他遞給她一份離婚協定書,只因他要相守一生的女人,不是她。 貌合神離多年之後,她最終選擇離開。 “你逃到哪我都要追回你。” 他為了另一個女人,讓她意外吃了四年的避孕藥,卻用十年才追回她。 若知當初會這樣愛你,我一定會對你一見鍾情。
121萬字8 48116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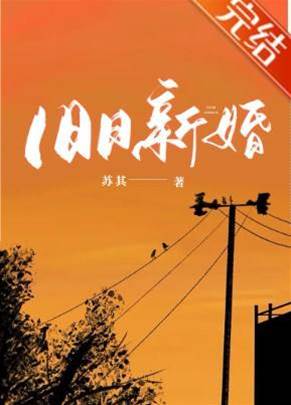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464 -
連載342 章

從校服到婚紗,可我不想嫁你了
雲檸愛了顧司禮七年,做了他隱身情人三年。 可換來的,卻是男人的輕視和羞辱。 他說,我這輩子都不可能愛上你這種惡毒的女人。 雲檸心如死灰,選擇離開。 後來,矜貴的男人跪在雨中,紅了眼:“雲檸,我錯了。” 雲檸眉目清冷:“你誰?”殺伐果斷的總裁低聲下氣:“老公或者情人兩個身份,隨便給一個就好,只要你別走。”
59.1萬字8 813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