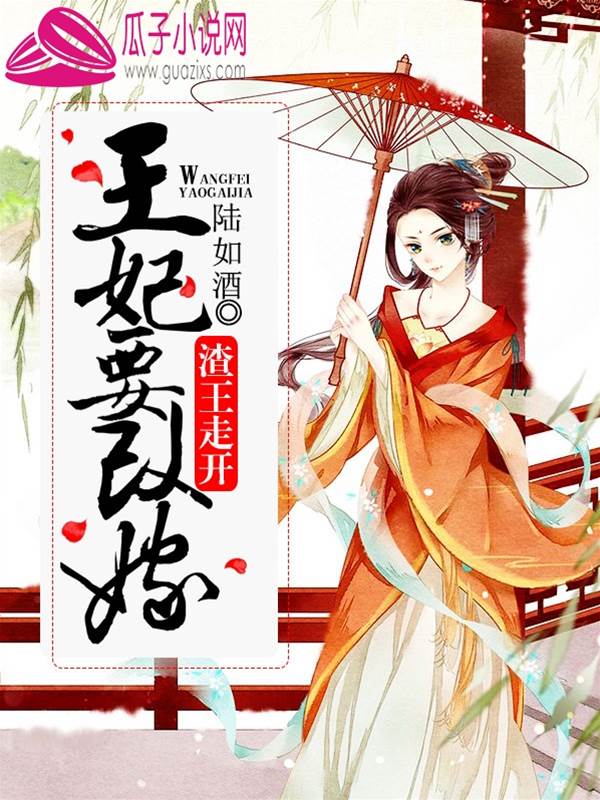《得罪未來帝王后》 第6章 第 6 章
謝彌愣了下,隨后下意識地揚了揚眉,這一臉刁相的老娘們兒居然要帶自己進宮?居然敢帶自己進宮?
忽然的,他心中似有所,目忽然一斜,正對上沈夷瞄的眼神。
沈夷也沒想到何媼居然提出這般放肆的要求,第一反應不是驚慌或是惱怒,而是心頭一跳,先去觀察謝彌的反應。
待謝彌發現,才‘嗖’地把眼睛轉開。
何媼見抿不語,還以為被自己唬住,于是嗓音放的更緩,臉上也帶了笑,兼施地道:“之前聽說太子在城外驚馬,德妃娘娘嚇得跟什麼似的,非要您進宮問個明白的,多虧太子攔著,娘娘才沒有當場發作,您可別讓太子難做了...”
沈夷心里冷笑了聲,江談哪里會管這些瑣事?蕭德妃執意要人,不過是為了給寶貝侄出氣,順帶削一削的面子罷了,被嚇唬兩句就把底下人推出去送死,以后哪個敢給他們沈府用心當差?的名聲還要不要了?
而且...這是個和謝彌修補關系的好時機。
想到這個,就有些坐不住了,截斷的話:“放肆!”
擺出一臉大義凜然:“那日的事我已經懲罰過謝部曲了,太子也點過承認是個意外,若是再繼續追究,豈不是要令太子落下個心狹窄的名聲?!娘娘是殿下生母,怎會不為太子考慮?定是你從中挑唆!”
說著說著也開始冒火,哪怕他們討要的人不是謝彌,而是邊的其他人,這也夠沒把放在眼里了,五歲便得封縣主,也是千萬寵長大的,豈能沒些小脾氣?
委實忍德妃久矣,再不愿把自己踩到泥地里,討好一個眼里沒自己的人了。
“何況...”冷哼了聲:“謝部曲是我的人,不著別人來置。”
見何媼怔愣片刻,還想再開口,不由厭煩道:“把給我攆將出去。”
蔣媼雖覺著不妥當,但絕不會違拗自家公子的命令,當即帶著仆婦把何媼給‘請’了出去。
屋里一時空下來,只剩下沈夷和謝彌兩人。
沈夷不得在謝彌那里把之前鞭打他的事揭過去,便下意識地側了側頭,就見謝彌若有所思地看著,神略有訝然。
——并沒有設想的加,激涕零等等表,這讓有點失落。
兩人目在一。
謝彌似乎在細細地審視著,神讓人琢磨不。
沈夷到底和他對視片刻,到底定力不如他,咬了咬下:“方才那何媼...你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就算不能恩戴德到甘為用,好歹謝一下啊,這什麼人呀!
謝彌又瞄了一眼,把的心思窺探了六七,故意說不想聽的,嘖了聲:“主人問得好,哪來的狗屁老虔婆,敢對老子指手畫腳的。”
沈夷實在頗為古怪,好像...莫名有點怕他,懼怕中又摻雜了惱委屈和郁憤。
還有...對他的好,好的有點太過頭了,好的就像是要完差事一般,急切地想要見到結果。
他一開始以為自己的份被猜疑,順著查了之后,發現并無暴的可能,再加上今早兩人的互相試探,他越發確定,沈夷并不知道他的真實份,否則早喚來羽林衛了。
謝彌仔細咂了下,這般態度,還真有點意思。
沈夷之前和他幾乎沒獨過,長這麼大,還沒哪個人敢在面前說這樣的鄙之語!
一口氣梗在口,臉也漲的通紅,半晌才惡狠狠地岔開話題:“除了這個,你還有別的想說嗎?!”
“哦,我還真有一件事想問。”謝彌雙手抱臂,指尖在手臂上輕敲了兩下。
盡管不知態度大變的緣故,但瞧在當日在江談面前辱他的份兒上...
他猛然拉近兩人的距離,雙手撐在側,奢華眉目在面前驟然放大,鼻尖幾乎著的鼻尖。
“我什麼時候了你的人?”他壞壞地笑:“主人。”
就這樣,狠狠地把欺負回來。
......
東宮里,一對兒清雅的仙鶴香爐正裊裊飄著龍涎。
江談立在窗邊,手執一管用久了的狼毫玉筆,上穿的是半舊的月白圓領常服,腰間勒著玉帶,雖不是新,仍襯得人長玉立,一副松枝掛月的好模樣。
他雖貴為太子,食住行卻并不奢侈,但也并不過分儉省,就連一支筆,一塊墨,都是按著儲君該有的份例,簡直規矩的過分。
他正低頭幫沈皇后抄著一卷經文,字清雋端正,可不知為何,落筆總帶了一浮躁,他又寫了幾筆,自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輕輕了下眉心,令侍把才抄好的一頁紙拿去燒了。他雖是年模樣,行事卻十足沉穩。
江談正要啜一口茶,就見何媼低頭走了進來,他不等何媼開口,便主問道:“東西都送到了?”
何媼忙點頭應了。
“...”江談遲疑了下,察覺到自己心緒為何浮躁,緩緩問道:“還好吧?”
那日的事令江談頗為不愉,不過他也沒心思總放在沈夷上,忙活了幾日,待心里的不悅散了,沈府又傳出沈夷這幾日子不適的消息,他這才慢慢地意識到,自己那日當著眾人斥,可能有些過了。
正好他給備的禮還沒送過去,他便遣了年長穩重的何媼去送東西,算是給個臺階下。
畢竟過了這幾日,一未主找他修好,二也未遞話進東宮,他也并不怎麼高興。
何媼一頓,吞吞吐吐地道:“老奴瞧著...郎心好像不大好,許是老奴說錯了話吧,郎竟派人將老奴攆了出去...”
深深叩首:“都是老奴的不是,讓您也失了面。”
上眼藥這等事兒早已爛于心,這樣掐頭去尾上綱上線,倒似沈夷還跟太子置氣,故意攆了他派去的人,好落他的臉一樣。
果然,江談皺了皺眉。
他倒也未全信,輕抬眸,手指點著桌案:“你和說了什麼?”
何媼心頭一跳,緩緩道:“回殿下,不是老奴,是娘娘...之前聽說您被私奴冒犯,一直記掛著此事,令老奴向郎討要那私奴,想要為您出氣,可誰知,可誰知...”
江談手指一頓,何媼小心窺探著他的神,慢慢道:“郎一聽老奴要人,登時便怒了,還,還說那私奴是的人...”
江談輕輕擰眉。
他那日當眾發作那私奴,倒也不全是因為蕭霽月的緣故,那私奴相貌實在太好,在人群中極為出挑,只是看人的目著邪氣。他離開不過半年,邊多了這麼個私奴,他竟是全然不知,也未給他寫信提過一字半句的,他心下自然不快。
當然,在他不快的時候,他也不會去想,自己在外時很主給寫信,偶爾書信多寫了幾頁,他便不耐多看,對那些小兒的撒話,他甚至懶得回上只言片語。
何媼見他臉上著一子冷意,心知自己這眼藥是上對了,心中暗喜,不免忘形,又小心道:“哎...近來長安蓄養男寵面首之風盛行,大公主就新添了兩個標致侍衛,趙國公府寡居的長媳也暗養了幾個伶人...沈郎,怕是也...”
晉朝才從一場綿延多年的大中平息,禮法規矩尚未重塑,有這些象也不稀奇。
話還未說完,江談的面已經冷的如同在寒冰里淬過似的,簡直滲人。
何媼尚未覺著大禍臨頭,江談已經面冷極,他拂袖轉,寒聲道:“把這污蔑未來太子妃的老婢拖出去,杖責三十。”
那私奴令他不快不假,但憑著潺潺對他的義,想來也不至于瞧上旁的男子,他對自己倒是頗有信心的。
這賤婢的話若傳揚開來,他的潺潺如何自?東宮面何存?
待何媼被慘著拖拽出去,江談才徐徐吐了口氣。
他想到一件事,有些不高興。
潺潺不止一次跟他提過何媼失禮,他并未放在心上,他還反過來令懂事些,對長輩送來的人理當敬讓,這不是因為他有多在意何媼,只是覺著子氣,小題大做也是有的,而作為太子妃,最該大度妥帖。
可眼下瞧來,這賤婢在他面前都敢口出狂言,胡編造,在潺潺面前只怕更為放肆。
他忽心頭一,或許...以往是真的委屈了,自己該主去沈府探?
江談沉片刻,喚來侍,正開口詢問,忽然蕭德妃邊一婢匆匆闖:“殿下,娘娘子不適,喚您去琳瑯閣一趟!”近來蕭霽月陪著蕭德妃住在琳瑯閣,蕭德妃便時時為兒子和親侄制造些機會。
江談難得躊躇,輕了下眉心,卻是看向侍,問:“自我回長安,夷可有遞話或者送什麼東西東宮?”
侍拿不準他的意思,只得照實說了:“回殿下,沈縣主并無什麼言語或者東西遞進來。”
頃刻間,江談的神便淡了幾分。
他默然片刻,起:“那便去琳瑯閣探母妃吧。”
反正,在他和沈夷之間,他永遠不必是先低頭的那個。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狂妃來襲:丑顏王爺我要了
殺手之王穿越而來,怎可繼續受盡屈辱!皇帝賜婚又怎樣,生父算計姨娘庶妹心狠又怎樣?淪為丑顏王爺未婚妻,她嗤笑:“夫君如此美如天仙,不知世人是被豬油蒙了眼嗎?”“女人,嫁于我之后,你還以為有能力逃離我嗎?”…
89.5萬字8 120828 -
完結905 章

空間娘子要馭夫
二十一世紀神醫門后人穿越到一個架空的年代。剛來第一天被浸豬籠……沒關系,她裝神弄鬼嚇死他們……又被打暈喂狼?沒關系,她拉下一個倒霉蛋……只是,這個倒霉蛋貌似很有性格,白天奴役她,晚上壓榨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年翻身得解釋。雙寶萌娃出世…
127.8萬字8 22083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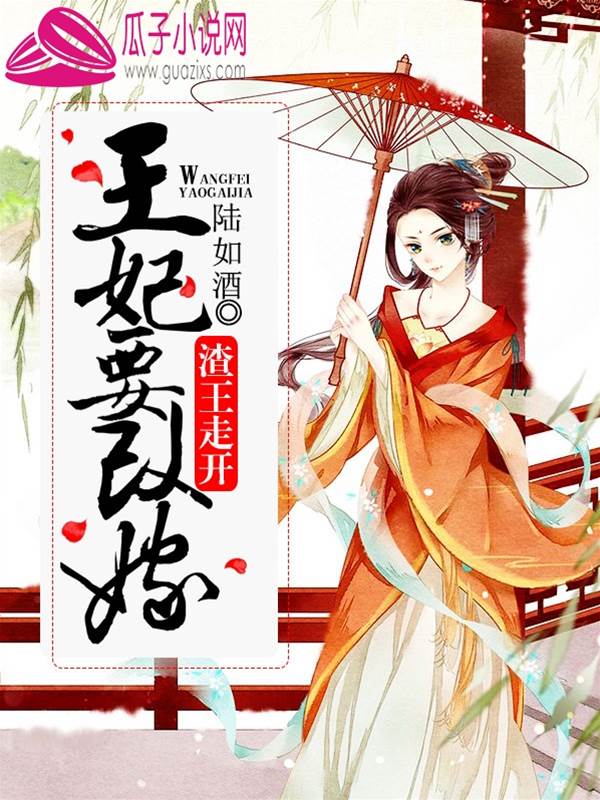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7 -
完結163 章

嫁三叔
顧長鈞發現,最近自家門口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年徘徊不去。一開始他以爲是政敵派來的細作。 後來,向來與他不對付的羅大將軍和昌平侯世子前後腳上門,給他作揖磕頭自稱“晚輩”,顧長鈞才恍然大悟。 原來後院住着的那個小姑娘,已經到了說親的年紀。 顧長鈞臉色黑沉,叫人喊了周鶯進來,想告誡她要安分守己別惹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卻在見到周鶯那瞬結巴了一下。 怎麼沒人告訴他,那個小哭包什麼時候出落得這般沉魚落雁了? 周鶯自幼失怙,被顧家收養後,纔算有個避風港。她使勁學習女紅廚藝,想討得顧家上下歡心,可不知爲何,那個便宜三叔總對她不假辭色。 直到有一天,三叔突然通知她:“收拾收拾,該成親了。” 周鶯愕然。 同時,她又聽說,三叔要娶三嬸了?不知是哪個倒黴蛋,要嫁給三叔那樣凶神惡煞的人。 後來,周鶯哭着發現,那個倒黴蛋就是她自己。 單純膽小小白兔女主vs陰晴不定蛇精病男主
25.4萬字8.18 163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