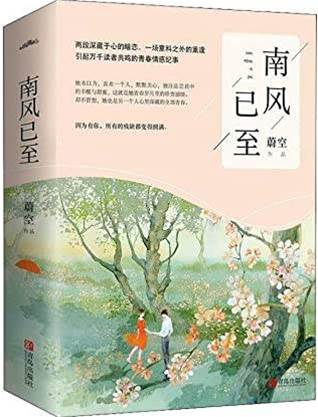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七十年代漂亮女配》 第117章 第117章
晚上, 如意酒樓宴會廳里。
杯盞相撞,歡聲如雷。
謝東洋喝紅了臉,笑咧了, 見誰都拍肩膀兄弟。
自從接手這個項目, 他這一年多以來上擔的所有的力,都在這一天煙消云散了。而且之前扛在上的力有多大,現在心里的底氣就有多足。
他們的溪洋房地產, 現在就是四九城的大拇指!
房子賣得這麼火這麼好, 阮溪自然也是很高興的。雖然沒有謝東洋那麼夸張,但也喝了不酒,同樣喝得臉蛋紅撲撲的, 角從頭到尾沒機會落下來過。
酒宴結束凌爻來接。
阮溪坐到車里, 靠在椅背上轉頭看向他, 醉暈暈笑著說:“我又大賺了一筆。”
凌爻傾過來幫系安全帶,“聽說了,一個小時就賣完了。”
阮溪順勢抬起手勾住他的脖子,不像在別人面前那麼正經沉穩,眼睛慢眨幾下,放縱心里的得意出來,看著凌爻問:“我是不是……很厲害?”
凌爻看著回:“嗯,非常厲害, 富婆。”
阮溪很開懷地笑起來,“富婆允許你親一下。”
凌爻角含著笑, 到上親一下,看還不松手, 眼睛里全是醉蒙蒙的霧氣, 便又多親了一會。車子停的地方比較蔽, 天又黑,倒也不怕別人看到。
片刻車燈亮起,車子啟上路。
阮溪有些困,靠在椅背上閉著眼睛休息,晃晃悠悠正要睡著的時候,車子突然停了下來。以為到家了,結果睜開眼睛發現還是在路上。
再轉個頭,看到車窗外面站兩個警。
警看著凌爻問:“喝酒沒?”
阮溪懵著愣了愣——嗯?這年代還有查酒駕的?
凌爻自然回:“沒有。”
警拿出酒檢測儀,“你吹一個。”
凌爻對著酒檢測儀吹一下。
警看一下儀:“喝了。”
凌爻:“不可能吧?”
警:“怎麼不可能,你這一車的酒味。”
阮溪這時在旁邊道:“他真的沒喝,我喝了。”
警:“我這儀也沒出病啊。”
說著不再糾纏,“罰款五十。”
阮溪還要再繼續爭辯,凌爻忽然想起什麼,便沒讓再跟警爭。
他從上掏出錢夾打開,手給警遞了五十塊錢。
車子開起來,阮溪看著他說:“肯定是他那儀壞了,罰五十塊錢這麼多,五十塊錢……都能買……都能買三十斤豬了!”
凌爻忍不住笑,“應該是沒有壞。”
阮溪:“你又沒喝酒。”
凌爻看一眼忽笑出來,“你喝了呀。”
什麼意思呢?
阮溪看著他木著眼睛想一會,因為酒的作用,大腦思考變得緩慢。然后一直等車子進了胡同快要到家的時候,才突然反應過來,“我……你……那個……”
造孽啊!
一年后。
初升的太爬上屋脊。
四合院門前的石獅子影被拉長。
紅的大門從里面打開,阮溪穿一襲剪裁簡單的襯衫款連,踩著高跟鞋過門檻出來,手里拎一款造型簡潔大方的小皮包,轉等著凌爻鎖院門。
鎖好門兩個人到車邊開門上車,開車出胡同。
阮溪看著前方胡同說:“又一對生娃就已達。”
和凌爻現在要去參加一場喜宴——謝東洋和溫曉家娃娃的滿月宴。
宴席的時間是定在中午,他們出門有點早,所以沒有立即去往辦宴的酒樓,而是開車先往謝東洋家去了一趟,先到他家里看一看孩子。
剛滿月的小寶寶包裹在襁褓里,一張小臉白皙彈,兩只小手也是白乎乎的。阮溪把他抱在懷里,每看他笑一下心里就跟著融化一下。
溫曉問:“你們還不打算要啊?”
阮溪看向笑著小聲道:“正在準備中。”
如今的時裝公司,生意已經完全做起來了,不管是薔薇閣還是盛放,在國都是知名品牌,定制服裝那一塊,也有了比較穩定的客源。
去年溪洋房地產公司又首戰告捷大賺了一筆,公司也已經步正軌。
事業上差不多都已經穩定下來了,剩下只是一步一步往下踏實走的事,而且和凌爻過二人世界也已經過了五六年了,也該改變一下家庭結構了。
騰出了心思來,自然就開始正經琢磨起這個事來了。
溫曉笑著說:“快點啊,正好和我們家兜兜一起玩。”
阮溪笑,“好。”
在謝東洋家逗兜兜玩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所有人一起去參加宴席。和謝東洋結婚的時候一樣,阮溪和他們家的親戚朋友都不認識,所以吃完飯寒暄寒暄便走了。
兩人開車在外面隨便轉了一圈,然后去阮翠芝家看阮志高和劉杏花。
陪阮志高和劉杏花說說話,晚上自然就留下吃飯了。
難得星期天沒事,阮長生和錢釧今天帶阮大寶出去玩了,阮翠芝便沒他們一家過來,同時也沒阮潔。傍晚的時候做好飯,便就坐下來吃了。
吃飯的時候阮翠芝跟阮溪說:“對了小溪,昨天你爺爺在家接到了老家那邊打過來的電話,說是山里要搬遷了,以后不讓住人,也不讓種地了。”
聽到這話,阮溪微微一愣,“搬遷?”
阮志高點頭應:“說是要建什麼大壩,所有村子都要遷。”
阮溪沒說話,阮翠芝又道:“山里那種地方,拆遷拿不到什麼錢,能房子換房子地換地已經很不錯了。我們在老家什麼也沒有,房子和地當時都給你二叔和二嬸了,所以我們就不打算回去了。但是老裁的房子,小溪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阮溪低眉想了想,片刻道:“那我回去看看吧。”
這次要是不回去的話,以后便想回也回不去了。那里的村落和人煙都會消失,他們在那里生活過的所有痕跡也都會消失在山林之中。
雖說自從來了北京以后就沒有想過再回去那里生活,但是聽到這樣的消息,心里還是控制不住悵然。畢竟是從小長大的地方,是他們心里的一。
要不是阮志高和劉杏花年事已高,實在無法再來回折騰,最想回去看一看其實是他們,畢竟他們一輩子生活在山里,原本還想著死了要埋回山里去呢。
回去看看吧,那里是此生開始的地方。
晚上回到家,梳洗完躺在床上。
阮溪神淡淡的,慢慢眨著眼睛說:“沒想到山里也會拆。”
凌爻看著說:“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阮溪側過頭來,“你有時間嗎?”
凌爻道:“最近院里不太忙,我可以請假。”
阮溪看著凌爻,想著他大概也是想回去看一看的,畢竟他從七六年離開鳴山回到城里以后,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既然他想去,阮溪沖他點點頭,“好。”
三天后,騰出了時間的阮溪和請到了假的凌爻,拎著行李箱坐上了回鳴山的火車。火車上喧鬧雜,兩個人在座位上,聊天看窗外的風景。
阮溪跟凌爻說:“很多年沒有回去了,不知道現在變什麼樣了。”
凌爻道:“我比你時間更長,懷念那時候的。”
阮溪看著他笑出來,“懷念我嗎?”
凌爻看著,點頭道:“確實大部分都是你,沒有你的時候好像沒什麼可懷念的。”
阮溪仍是笑著:“還好是在一起了,不然你不得懷念我一輩子?”
凌爻把的手進手心里,“嗯,還好又遇到了。”
火車一站一站往前走,到達天鎮的時候是傍晚時分。
坐火車太過折磨人,阮溪和凌爻自然沒有立即便往山里去。他倆去招待所放下行李梳洗一把,然后出來在鎮上逛了逛,看了看這個記憶中的小鎮子。
和十幾年前比起來,天鎮幾乎沒有什麼太大模樣上的變化,差不多還是原來的那個樣子,只是變得更為破舊了,而且街上的人變了。
人自然是因為這個年代外出打工了熱,年輕人在鄉下掙不到錢,所以全部都外出打工掙錢去了,留在家里的多是些老人和孩子。
小鎮不大,逛完一圈也用不了多久。
阮溪和凌爻逛完,最后在一個面攤上坐下來,點了兩碗擔擔面。
等著面攤老板上面的時候,阮溪笑著說:“還記得嗎?我們第一次來鎮上給師父打酒那一回,到了這里也是吃了一碗擔擔面,我還記得你說自己不能吃辣。”
凌爻記得比清楚,當時還掐了他的臉,說他死了。
也就是那時候,他說有機會帶去他家看一看。
現在想起來簡直恍如隔世,那時候他完全沒想過自己能離開鳴山回去城里,也沒有想過真能帶阮溪去他家看一看。
更沒想到后來世事變遷,做過的所有夢全都真了。
他回阮溪說:“現在已經很能吃辣了。”
而且是,無辣不歡。
兩人聊著天在面攤邊吃完面,本來打算回去招待所休息,結果又意外得知天中學的場上今晚放電影。于是兩人調轉了方向,去了天中學。
現在大家看電影的熱沒有七十年代那時候那麼足了,畢竟已經過去了十四五年,時代在發展,鎮上已經有人家買了電視機了。
阮溪和凌爻對電影本自然也沒有多的熱,只是懷念以前,于是站在人群后面湊熱鬧。看電影是次要的,看著電影在一起懷想過去才是主要的。
說起當時他們跑到鎮上那晚剛好上看電影,兩個人來晚了爬到后面的老槐樹上去看。阮溪因為走了兩天山路太累,直接抱著樹睡著了。
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阮溪看著凌爻問:“那晚是你一直在樹上扶著我,所以我才沒掉下去?你還把手一直墊在我的臉下面?”
凌爻沖點頭,發音輕:“嗯。”
阮溪看著他眨眨眼道:“哇,小小年紀就那麼暖,真是沒白疼你啊。”
凌爻笑出來,“謝謝姐姐那時候疼我。”
聽到這話,阮溪也忍不住笑出來,上說:“可你一天也沒把我當姐姐,是不是那時候就對我有什麼不單純的心思了,是不是?”
因為他是小孩模樣,當時年齡又實在小,所以從來都沒多想過。就把他當弟弟當朋友,手拉手肩靠肩的,也當是小孩子間最平常的行為。
但現在再回頭想一想的話,十三四歲的男生生,已經有那方面心思了。
凌爻看看,片刻道:“可以說是嗎?”
阮溪抿住忍笑一會,然后一把掐住他的胳膊,“我就知道!表面上一副乖寶寶的樣子,單純溫順又可,其實心里想法多得很!”
凌爻被掐得疼,笑著把的手拿下來住,接話道:“也沒有很多,就很簡單的一個想法,喜歡你,想每天都看到你,看到你就很開心。”
在一起那麼長時間了,現在聽到他毫不加修飾地說這些話,阮溪還是會覺得心里有種甜滋滋的覺。因為知道,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發自心的。
兩人這樣牽著手往前走,吹著小鎮的晚風,偶爾抬頭看看天上的星星。
阮溪和凌爻在鎮上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在鎮上吃了早飯,然后便拎著行李箱往山里去了。走上那條他們全都悉的山路,去往記憶中的金冠村。
這些年在城里一直忙學習忙工作,鍛煉的時間不多,所以一段山路走下來,阮溪覺比以前回來的時候要累,沒有以前爬山那麼輕松了。
跟凌爻說:“我是時間長沒爬山了,還是年齡上來了。”
凌爻看著笑笑,“我背你一段。”
阮溪直接沖他擺擺手,“那倒也不需要。”
說不需要,但是在累得吁吁氣的時候,凌爻還是背了幾段。
坐下來休息的時候,阮溪坐在石頭上一邊喝水一邊說:“不行,還是得鍛煉。”
就算沒有山可爬,回去也得堅持每晚跑跑步。
不過累歸累,但并沒有拖速度。
為了早點走到村子里,晚上夜籠罩下來以后仍舊繼續趕路。趕到夜深時分停下來休息,坐在石頭上看著頭頂的月亮,數一數天上的星星。
就在阮溪手撐石頭仰著頭看月亮緩氣的時候,凌爻忽說:“我記得,這里附近是不是有一個天然的溫泉?”
聽到這話,阮溪放下目左右看看。
也想起來了,看向凌爻道:“好像就是這里。”
說完這話,兩個人立刻就達了默契,立馬拎起行李箱找溫泉去。
順利找到水聲潺潺的溫泉旁邊,阮溪大松一口氣道:“我要下去洗個澡。”
說完二話不說,果斷了上的長袖外套,又把鞋和子下來放在一邊干燥的石頭上,然后直接穿著吊帶長下水,緩慢走進水中。
頭發半,轉看向凌爻,他:“下來啊。”
凌爻直接在石頭邊坐下來,看著阮溪:“你確定要一起洗?”
阮溪不跟他廢話,過來手一把把他拽水里,拉他跌進水里了全,抹一下眼睛上的水眨眨眼道:“走了那麼久的山路,我不相信你還能干嘛。”
凌爻一意站穩在面前,看發滴水渾,臉上也全是森森意。對視片刻,他沒再多說話,直接攬過的腰,托上的后腦,低下頭堵上的。
阮溪:“!!”
“你還真能,你還真敢。”
沐浴著清晨的霞,阮溪和凌爻手拉手繼續趕路去金冠村。
因為休息時間,兩人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的時候到達了金冠村。以前因為回村就是回家,所以每次回來都會格外欣喜,但這一次更多的覺是懷念。
這里已經沒有他們惦記的人,只有他們曾經共同生活過的場景。
阮溪沒有特意去見阮長貴和孫小慧,和凌爻留在金冠村,先去金冠村的大隊部找了王書記,和他確認了一下拆遷的事,并簽署了一份拆遷協議。
補償很,因為他們生活過的地方要歸還給山林,而不是用來規劃建設。
第二天阮溪和凌爻在山上轉了一整天,見到人便笑著打招呼寒暄上幾句。眼下山里的人已經搬走了一部分,再加上出去打工的那些年輕人,所以村里能見到的人已經不多了。
阮溪和凌爻拿相機拍了許多他們曾經生活過玩鬧過的地方——冒著炊煙的老房子、金黃的梯田、甩著尾的老水牛、放豬吃草的山坡、還有早已破舊飄搖的吊腳樓……
時間有限,阮溪和凌爻只在山里呆了一天,拍了照片看過了老裁和大咪。
次日離開的時候,阮溪在金冠村里請了兩個人幫抬東西下山。
帶走了裁鋪里的一個老件——老裁的那臺舊紉機。
跟著紉機沿著山路下山的時候,阮溪不時回頭往回看,腦子里一直出現一個畫面——
老裁坐在轎椅上被人抬著,優哉游哉地煙鍋子,而編著兩烏溜溜的大辮子,背著書包跟在轎椅旁邊,慢悠悠地走在山道上。
迎面若是著人,人家會笑著招呼一句:“小裁,跟著老裁去做裳呀?”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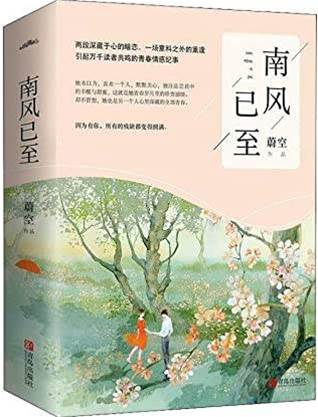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192 -
完結540 章
全球示愛少夫人
“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但愛情免談。” 蘇輕葉爽快答應,“成交。 “ 可他並沒有想到,婚後她對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 “靳先生,我想要離婚。” 男人把她抵在牆角,狠狠咬住她的唇,「想離婚? 不如先生個孩子。 ”
93.6萬字8 294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