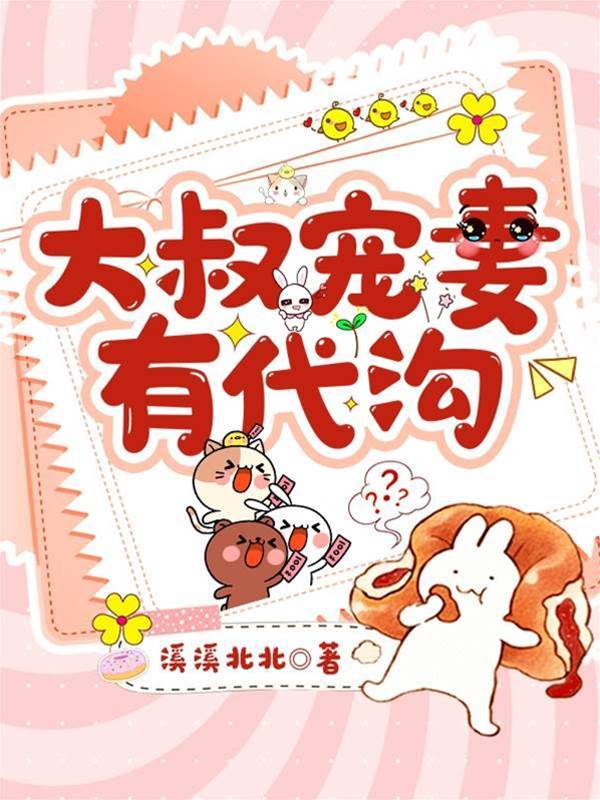《頂級平替》 第131章 源源不斷,生生不息
嶼輕輕笑了起來,“那你有沒有對我的襯衫、圍巾還有鞋子做什麼啊?”
“沒有。我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你都沒有用過。你喜歡穿衛,那件襯衫不屬于你喜歡的款式。
你喜歡穿板鞋、運鞋,就算出席活的皮鞋款式也很簡單,這種鏤空花樣,你心里肯定覺得太了,本不會穿出去。羊圍巾也是……一在柜里放了很久的味道。”顧蕭惟很認真地回答。
嶼歪著腦袋,在腦海中不斷回憶著和顧蕭惟相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們一起拍《反擊》的時候,你故意帶了一條本不屬于你風格的線衫給我試穿,還我不用穿打底衫……你是不是故意的啊,顧同學?”
“我們就要分別了,我喜歡你,所以……想留一件你穿過的服在邊,就像你還陪在我邊一樣。我從來都不想冒犯你,我只想給自己一點藉。”
“什麼做冒犯呢?”嶼輕輕撥開顧蕭惟額前的發,看進他的眼睛里,“你是否幻想過像歐俊韜那樣左右我的人生?還是像季柏年那樣,威脅利,甚至來一杯讓人失控的酒?你是否想象過未經我的允許干擾我的生活,比如趁我不在溜進我的家里,睡我睡過的床?”
嶼輕輕扯著顧蕭惟的領,帶著他一步一步后退。
“如果說你看到了我,畫下我的樣子就是冒犯,那麼被畫在紙上的小貓小狗、小花小草、道路行人都被冒犯了嗎?”
顧蕭惟看著嶼,萬千心緒都被那只手拖拽著一步一步向前。
“如果說你留下我落在現場的保溫杯和外套,不忍心我的簽名照被扔在垃圾桶里所以撿出來好好珍藏,這些算是冒犯……那撿起掉落在地上的銀杏葉是對那棵樹的冒犯嗎?鳥兒掠過天空你留下了一羽也是對那只鳥的冒犯嗎?”
顧蕭惟的目逐漸變得明亮徹,仿佛醞釀著無數的期待。
“如果說喜歡我,所以給我寫信做冒犯,那我不收的禮,更喜歡收到他們的信,是不是代表我特別喜歡被冒犯?”
嶼的聲音拉長,他的吻從顧蕭惟的眉心,沿著他的鼻梁而下,停留在他的鼻尖上。
“如果說慕我,所以想要留下我的味道做冒犯,那麼那些囤了一大堆龍涎香的人是對鯨魚的冒犯嗎?”
顧蕭惟頓了一下,繃的線緩慢地彎了起來。
而眼前的嶼,仿佛融合了人世間所有好的,是顧蕭惟靈魂歸于的自由,是回時間里無數次心形的,他臉上的薔薇花枝隨著他眼底的熱烈綻放開來,是獨屬于顧蕭惟的燦爛的告白。
“學長……”顧蕭惟側過臉,吻上他還沒有洗掉的薔薇刺青,順著藤蔓從他的耳后一直吻到他的眼睛下面。
“如果你因為喜歡我所以接近我算是冒犯,那全天下所有的慕都是對對方的冒犯。”
嶼退到了閣樓的盡頭,那是一個懶人沙發,很明顯不是顧蕭惟的風格,而是嶼喜歡的款式。
這棟別墅啊,明明是按照顧蕭惟的風格裝修的,可是無不在以嶼的喜好取悅他。
就連這個上鎖的閣樓也是。
嶼跌進了沙發里,深深陷了進去,他仰著頭輕聲對顧蕭惟說:“金魚花的花語可不是什麼七秒的記憶或者短暫的歡愉,而是‘源源不斷,生生不息’。就像你我,和我你一樣。”
顧蕭惟的眼淚很熱,掉落在嶼的臉上,像烙印一樣。
“你現在想冒犯我嗎?”嶼歪著腦袋問。
顧蕭惟的目深沉而熱烈,“從你用我沒有看過的樣子去吸引別人的時候,我就很想冒犯你。”
“打住。我只是去宣示對你的主權。我被你那麼認真地著,所以其他人的喜歡永遠不可能打我。”
顧蕭惟的吻落了下來,像是蟄伏在深夜已久的燈火,為了某個人將天地都點亮。
層層疊疊的畫框是從前世到今生的書,泛黃速寫本上的線條是故夢終于為現實。
嶼親吻顧蕭惟,吻荊棘叢生的過往,吻那些讓他們破碎的憾,吻顧蕭惟的義無反顧,吻他一如既往的沸騰與熱烈。
他很確定自己他,顧蕭惟是他的人間。
第二天的中午,嶼被手機的鈴聲吵醒,他手循著聲音過去,一才發現自己的像是被拆卸了重組一樣,連手指頭勾一勾都費力。
好不容易把手機拿到了耳邊,他的聲音嘶啞得差點把自己嚇到。
“喂?是嶼先生嗎?這里是xx警局xx分局,關于那個私生飯的案子,我們有了關鍵的進展。”
“什麼?”
天網恢恢疏而不,那個假私生飯收季柏年現金的時候,雖然監控的角度沒有拍到季柏年的正臉,但是有一輛車停在附近,車里的行車記錄儀正好拍到了。
嶼笑了一下,他很清楚,季柏年被他們抓到的把柄太多了,如果他對鐵窗生活太熱的話,江引川和顧蕭惟掌握的把柄足夠讓他一直待在里面,他應該不敢來了。
至于這個案子要怎麼判,給警方,江引川那邊會切關注,連通稿也會準備妥當。
嶼側過臉,才發現這里并不是閣樓,而是他們的臥室。
自己雖然都不了,但是上很干爽,他抬起手來,發現手臂上的薔薇紋也已經被洗掉了。
空氣里是很淡很清新的花香。
嶼費力地轉過頭來,看到了床頭桌上擺著的一大束白金魚花,還有一張小小的卡片:[我出去辦一點事,會盡快回來。砂鍋粥在廚房,了就起來吃。]
嶼拿起那張小小的卡片手指都在抖,“混蛋家伙,你覺得我還能爬起來……走下樓去吃砂鍋粥嗎!王八蛋!”
誰知道在卡片的背面寫的是:[實在起不來就等我回來。床頭桌上有糖。]
嶼愣了兩秒,笑出聲來。
看來這家伙對于自己干了什麼清楚得很嘛。
“老子連拿塊兒糖的力氣都沒了。”
都不知道該把糖剝好了放進我里再走嗎?
等等,嶼,這是你該思考的問題嗎?
你該想的難道不是為什麼顧蕭惟有力氣出去辦事,而你卻像是沒了半條命?
某種強烈的危機涌上了嶼的心頭。
顧蕭惟已經徹底嘗到了甜頭,該不會食髓知味……以后經常這樣吧?
嶼忽然覺得年輕的生命正走向凋零。
他并沒有哀嘆太久,顧蕭惟就回來了。
他把廚房里的粥盛了出來,一勺一勺地晾涼了,坐到嶼的邊。
“你這麼快就回來了?”嶼試著想要把自己撐起來,但腰以下完全使不上力,覺跟被大卡車碾過似的。
再仔細看看,顧蕭惟這穿著雖然低調,但卻很顯型氣質,就連頭發好像也吹過。
這是捯飭過了?什麼重要人值得顧蕭惟如此上心?
“嘶……我本來以為你是去見季柏年了,他這一次多半又得進去了,你去勸他洗心革面好好改造呢。可我看你捯飭的這般致,你是去試鏡了?”嶼一說話,就牽扯到自己的嗓子疼。
“我是去見季柏年了。只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問為什麼不是你。很顯然,他對我的興趣消散了。”
“怎麼,你該不會還覺得憾吧?”
“憾當時沒有揍在他的臉上?”顧蕭惟反問。
嶼嘆了口氣,“我本來是想讓他明白,我不是他想象中的小綿羊,因為乖、因為顯得弱和需要保護你才喜歡我的。但好像弄巧拙了?他是不是充滿了對我的報復啊?”
顧蕭惟沉默地看向嶼,然后嘆了口氣。
“你嘆氣做什麼?”
“為季柏年默哀。”
季柏年又什麼好值得哀嘆的……莫名其妙。
“那誰為我的腰默哀?”嶼了,用眼神示意顧蕭惟扶他起來。
顧蕭惟輕輕應了一聲,放下粥碗,單手就把嶼給撈了起來。
嶼的自尊心頓時到一萬點傷害,為什麼人和人之間的差距可以這麼大?
“你不用擔心季柏年會報復了。反倒是他提醒了我,該小心歐俊韜。”
“放心吧,歐俊韜太唯我獨尊,總想用流量稱王。當流量不好使之后,他的位置也做不久。”嶼安道。
上輩子,歐俊韜就是因為流量路線消耗大,回報率低,被帝俊傳的東們給請下去了嗎?
而現在何慕的流量提前失去價值,歐俊韜應該距離被請下董事長位置的時間不遠了。
也不知道是顧蕭惟這碗粥有什麼神奇的滋補療效,還是因為這年輕,嶼第二天早上就覺得自己神清氣爽,除了很輕微的不適之外,下樓走路都很正常。
而顧蕭惟就一直盯著他看,說了一句讓嶼十分警覺的話,“我以為你需要躺上三、四天,還擔心會耽誤進組,沒想到你的復原能力很強。”
嶼一聽,心想不好,立刻扶著自己的腰,皺著眉頭,“不……不是的,疼……嘶……估計腰勞損了……”
“是麼?”
顧蕭惟一步一步走上來,他剛要手去嶼,嶼就猛地后撤了一步。
“你……想干什麼?”
“扶你啊?”
“不用,我自己可以慢慢下去。”嶼倚著扶手一點一點挪下樓。
“學長,你的演技有點蹩腳。我也沒有你想象中那麼不知輕重。”顧蕭惟的聲音里帶著一點無奈的笑意。
聽到他的后半句話,嶼立刻原地復活。
腰也不疼了,也不算了,直了脊梁骨下樓去了。
顧蕭惟站在他的后,好笑地看著他“忽然又行了”的樣子。
《西窗手札》的拍攝地點在某影視城,他們的住宿也安排在影視城里。
這個影視城據說是新建的,嶼從網上搜了一下里面的亭臺樓閣,古風古,就連琉璃瓦一片一片都整整齊齊。而且這一次擔任武指導的還是嶼的老人陳峰,嶼心里別提多期待了。
上輩子沒能圓的武俠夢,這輩子總算能真了。
顧蕭惟本來要親自開車送嶼去醫院拍片和見主治醫生,就是想確認他的手是不是真的拍打戲沒問題。
嶼卻嫌棄顧蕭惟照顧他照顧得太了,連去看醫生都像是放風。
他指了指帽間說:“顧同學,麻煩幫學長把拍攝期間要帶的行李準備一下好嗎?不然,以你學長的品味很可能穿著老頭衫打著扇子……”
“老頭衫和扇子不行。”顧蕭惟的眉頭皺得的。
看他那樣子,就知道他在想象嶼穿著老頭衫坐在折疊椅上,愜意地一扇,老頭衫就吹起來,然后啥啥都給人看完了。
“那你陪我去醫院,還是幫我收拾行李?兩者只能選其一。”
“收拾行李。”顧蕭惟嘆了口氣,“反正崔姐也會陪你去,會萬分張地聽醫生的話。”
這一趟去醫院,主治醫生確認嶼的傷勢沒有大礙,但還是希他謹慎小心。
一旁的崔姐也松了一口氣,一邊開車一邊囑咐道:“在片場,刀劍無眼要特別小心。別仗著自己學了兩手功夫就瞎逞能。”
“姐夫可是制片人啊,我能不十二萬分地投?到時候人家說我是關系戶,給姐夫丟人。”
嶼左一句“姐夫”,右一句“姐夫”,把崔姐都喊臉紅了。
“好了,別套近乎了。等我們擺酒的時候,一定讓你來當伴郎。現在你趕回去收拾行李,要不我讓葉盛宜也去給你幫忙?”
“不用了,顧蕭惟給我收拾著呢。崔姐,我能問下你從前寄給我的信都放在哪里嗎?”
“工作室啊。有間專門的房間存放信件。我都懷疑明年那間房就不夠用了。”
“那過去的也在嗎?我指的是我在朱雀傳的那段時間?”嶼問。
“你過去的……哪有幾個給你寫信啊。加在一起也就兩個鞋盒那麼多,你那時候萎靡不振,收到過好幾次有黑偽裝寫信罵你,就再也不看那些信了。”
“難道……你都給理了?”嶼心頭一陣張。
“哪兒能啊?我放家里的儲間了,得找找。你怎麼忽然想起來了?”崔姐好奇地問。
“里面有顧蕭惟寫給我的信。”嶼看向窗外的日,恍若隔世,“我想知道那時候的他……對我說過什麼。”
崔姐微微一怔,沒有想到顧蕭惟竟然給嶼寫過信,那確實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行,我明白了。我這就找給你。”
當嶼回到那棟別墅的時候,手里拎著兩個鞋盒。
顧蕭惟還在為嶼收拾行李,聽見關門的聲音就走了出來,“醫生說你的手怎樣?你這是帶了什麼回來?”
“嘿嘿,讓你害的東西。”
嶼給顧蕭惟一個很有暗示意味的目,當顧蕭惟走到他的面前,他卻把鞋盒打開,發現里面是一捆一捆的信件。
“你……在找過去我寫給你的信?”顧蕭惟坐了下來。
“對啊。你用的是什麼名字?也是gxw嗎?”
顧蕭惟搖了搖頭,卻沒有說自己用的筆名是什麼。
嶼笑了一下,“你不說我也能找出來。首先呢,以顧同學的格,是不會使用帶有圖案和的信封、信紙的。”
“嗯。”顧蕭惟輕輕應了一聲,算是承認了。
“其次,紙短長,你給我寫信用的語氣會很溫,但不會長篇訴說你對我的喜歡,而是言簡意賅地鼓勵我或者給我建議。”
那聲“紙短長”讓顧蕭惟的神溫許多,“嗯。”
“還有,信封上的字跡會很工整,很認真,而且明顯是男的字跡。”
嶼抬頭看了顧蕭惟一眼,從鞋盒里找出了十幾封一模一樣的白信封,上面蓋著郵,只是存放太久,信封都泛黃了。而且到了后期,嶼已經沒有收到的信了,唯有白信封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寄過來。
“我要拆開了?”
“好。”
嶼深吸一口氣,把這些信按照郵的時間擺好,他握著小刀甚至不忍心將信封口破壞。
因為那不只是信而已,是顧蕭惟多年以來的心意。
打開第一封信,看到的兩個字就是“學長”。
嶼的眼睛頓時酸了,眼眶潤得看不清楚,他如果曾經拆開這些信,那麼當他聽到顧蕭惟他“學長”的時候,一定就能猜到他是曾經給自己寫信的人。
顧蕭惟老早就看出來薄文遠對嶼只是利用,勸說嶼要有自己的想法,趁著薄文遠還需要嶼會給他選擇權的時候,多演一些能證明自己演技的作品。要勇于拒絕,只有當嶼惜自己了,別人才會尊重他。
猜你喜歡
-
連載958 章
俏皮甜妻娶進門
被送給活死人做沖喜小妻子的夏安然,隻想裝蠢賣醜,熬死老公後跑路。可是,躺在床上的活死人老公,怎麼轉眼變成了冷酷毒辣、心狠手辣的的商業帝王?最最最關鍵的是……她之前才一不小心、趁火打劫,將他吃乾抹淨了!!!肚子裡揣著的那顆圓滾滾種子,就是她犯下滔天罪孽的鐵證!夏安然抱著肚子,卑微的在線求救:現在跑路,還來得及嗎?淩墨拖著試圖帶球跑的小妻子回家,一邊親,一邊逼她再生幾個崽崽……
88萬字8 61171 -
連載768 章

婚婚欲睡:陸少夫人要離婚
童心暖暗戀陸深多年,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給陸深,結果……新婚第一天,陸深的白月光帶著孩子回來了,新婚第二天,她的父親死了,自己被逼流產,新婚第三天,她簽下了離婚協議,原來陸深從未愛過她,所謂的深情都是她自以為是而已。
170.3萬字8 38332 -
完結5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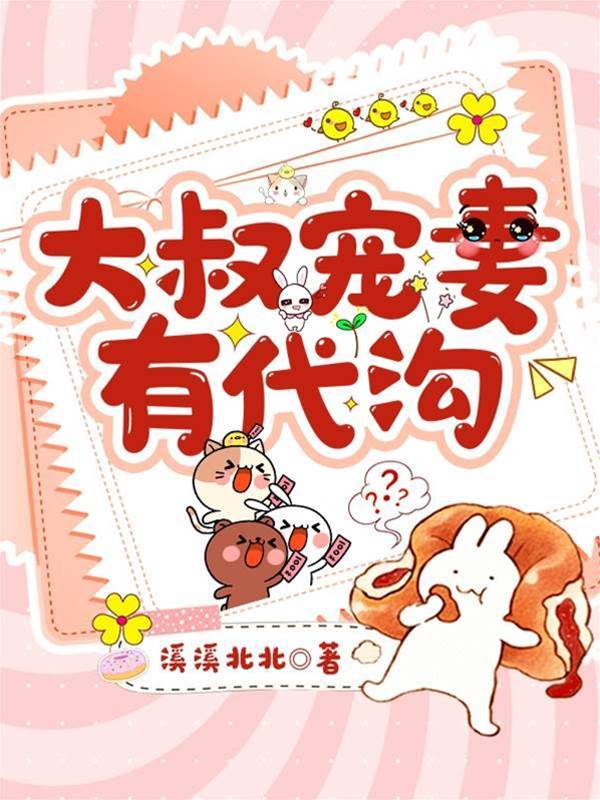
大叔寵妻有代溝
等了整整十年,心愛的女子終于長大。略施小計民政局領證結婚,開啟了寵妻之路。一路走下,解決了不少的麻煩。奈何兩人年紀相差十歲,三個代溝擺在眼前,寵妻倒成了代溝。安排好的事情不要,禮物也不喜歡,幫忙也不愿意… “蘇墨城,不是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怎麼現在搖身變成了公司的總裁。” “蘇墨城,不是說,以前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嗎,那你父親和我母親之間怎麼會是這種關系?”
55.3萬字8 51533 -
完結2072 章

幸孕六寶寵上天
一場陰謀,她被親爸賣了,還被人搶走孩子,險些喪命。五年后,她帶著四個孩子強勢回國尋找孩子,懲治兇手,沒想剛回來孩子就調包。發現孩子們親爹是帝都只手遮天活閻王顧三爺后,她驚喜交加,幾番掙扎后,她舔著臉緊抱他大腿,“大佬,只要你幫我收拾兇手,我再送你四個兒子!”三個月后,她懷了四胞胎,“顧南臣,你個混蛋!”“乖,你不是說再送我四個兒子嗎?”顧三爺笑的很無恥,逢人就夸,“我老婆溫柔體貼又能生!”她:滾!
198.5萬字8.18 525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