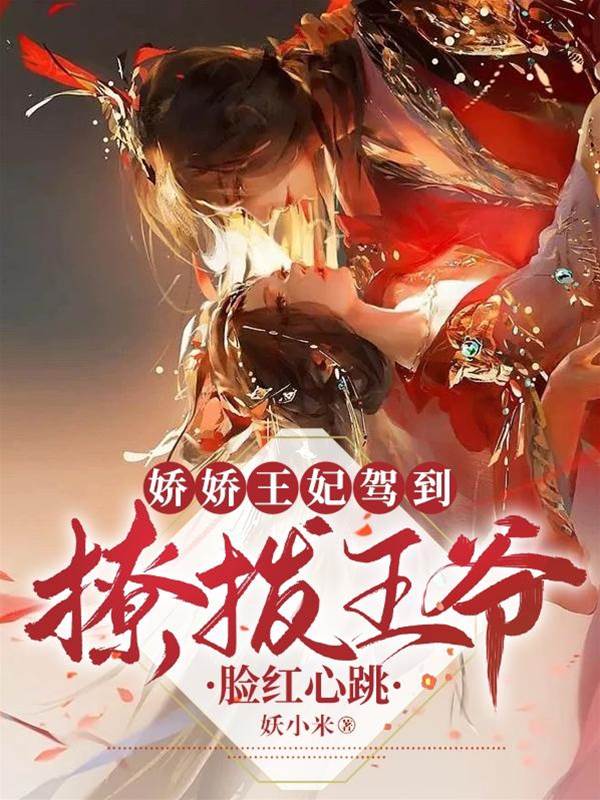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清冷世子追妻日常(重生)》 第123章 第一百二十三章
四月廿七子時, 淳熙帝薨。
雖自去歲元月起淳熙帝子便有些不好,后來有一長春道長侍奉在側,淳熙帝勉強可起理事,或因此, 于政務上已懈怠許多, 才于冬下旨命祈王監國, 然雖如此,東宮人選卻遲遲未定。
今春淳熙帝氣明顯好轉,雖仍是祈王監國, 但奏折上不時出現的批,以及對朝臣的頻頻召見, 令朝野上下均以為淳熙帝將重新理政,畢竟, 淳熙帝尚不足五旬,仍算得年富力強的時候。
也正因此,這一消息令人倍突兀, 且事發突然,淳熙帝并沒有留下關于冊立太子的詔,僅以口諭命祈王柩前即皇帝位,當時在場有閣徐首輔,錦衛指揮使許紹, 以及林貴妃和祈王、嘉、沁公主。
對這道口諭,朝中并非全無異議, 然徐首輔和許指揮使予以確認,兩位公主哀痛致病, 均未能面, 且口諭一出, 金吾衛指揮使提出質疑,卻被副指揮使裴瑾當場斬殺,此一舉殺儆猴,祈王迅速控制金吾衛、錦衛兩大天子近衛,將宮中防務盡握于手中,廿九,祈王即位,以日代月服孝二十七日,于六月初舉行登基大典。
于清詞而言,重生之后,許多事的走向已全然不同,在得知祈王即位后,最擔憂的便是顧紜,上一世,睿王是太子,顧紜早逝,這一世,睿王與顧紜兜兜轉轉仍在一起,卻失了太子之位。
寧夏王府風雨飄搖,紜兒此生能得安穩嗎?
心急如焚,但這樣的敏時刻,不能與顧紜通信,而長歡,亦不知被何事耽擱,至五月末也未歸來,且一應音信全無。這兩件事積于心頭,憂思難安,卻并不知,于自己而言,一生最大的危機已悄然來臨。
這日如尋常的每一日一般,掩下滿懷憂思,袖著書去尋謝山長解,待到了明思堂,卻得知山長被知府召去赴宴,至晚方回。
謝山長回來后便稱不慎染了風寒,恐染了他人,謝絕探視,然而,次日晚,清詞與知微二人剛剛歇下,便被輕輕的叩門聲驚醒。
清詞披坐起,知微咕噥了一句起開門,清詞聽到在門口與人對答,須臾之后,卻帶著人進了屋子,又忙不迭關上了門。
燈下,知微看似鎮定實則詫異,結結道:“玉姑姑說山長咳......咳得厲害,想問問姑娘上次咳嗽用的人參消毒散還有沒?我去尋尋。“”
清詞盯著那進屋之后仍戴著風帽且未發一言的子,形與謝山長旁的玉姑姑相仿,發髻舉止也是一模一樣,清詞心下一,喚了聲“山長。”
謝山長摘下風帽,抬眸道:“知微出去。”
面沉沉,但步履沉穩,聲音清潤,并不像染了風寒。
問:“嘉嘉,我有一事問你,此事關系重大,你需得直言相告。”
“你在京中,可與當今天子有過來往?”
清詞下意識地想到淳熙帝,然見淳熙帝只在宮宴上,隨著眾人請安,嚴格來說,連一句話都未說過,因此,第一反應是搖了搖頭。
“你再想想?皇上于潛邸之中可見過你?”謝山長看著的目難掩焦灼。
“是祈王殿下?”清詞驀然意識到淳熙帝已薨逝,想起出事的繡坊,那日莫名遇到的采選,想起許久之前,在祈王府,那個男子看的眼神,如窺伺獵,勢在必得,紅漸漸失了。
“我曾應祈王妃之邀過府聽戲,偶遇祈王。”皺眉回憶,心中不好的預卻越來越濃。
謝山長握住了的手:“嘉嘉,你聽我說。”
“昨日許知府尋我,是為一事,便是那旨采選。”語速極快,卻冷靜鎮定:"我這才知,采選之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蘇州城盤桓許久,是在靜待時機。”
“天子要讓你宮。”迎著清詞難以置信的眼神,告訴,語氣里不掩諷刺:"亦要掩住天下悠悠之口。”
察覺到清詞的手已冰涼,心下憐憫,卻仍一字一句將他們的籌謀細細告訴:“老許頂不住力,答應配合他們為你偽造戶籍,亦要我這邊設法讓你......”
"病亡。”
“他們要抹去你曾經孟家兒,定國公府世子夫人的痕跡,以一個全新的份宮,侍奉天子。”
“嘉嘉,若阿詡在,以他的手,能帶你遠走高飛。可如今他不知被何事絆住,遲遲未歸,我原想托病拖延,待到阿詡回來,可那邊等不及要手了。”
“嘉嘉,你走吧,去肅州,這天下,只有蕭臨簡能護住你,你雖與他決離,他對你仍有意。”
謝山長說得每句話都能聽得明白,可卻是再匪夷所思不過,不明白,一個已富有天下的人,為何會對這樣一個只見過兩三面的平凡子,生出這樣齷齪的心思?這把龍椅還未坐穩,便這般迫不及待了麼?
怔怔然道:“山長,我若走了,們定知道是您放走的,屆時您怎麼辦?”還有遠在青州的父母弟,正在京中為的師兄,懷繡和大,還有蕭珩......蕭家執西北兵權多年,是先帝重臣,卻難保不為新帝忌憚,蕭家愿意為對抗皇權麼?
從未懷疑過蕭珩的品行,可亦不想陷他于兩難之地,況且,非孑然一,有這麼多牽掛的人。
“不會拿我怎麼樣。”謝山長平靜道:“至多,將我從書院趕了出去,我便回謝家,也沒什麼。可你,你若是進了宮,侍奉這樣的君主,這輩子也便毀了,便是看在阿詡面上,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你落到如此境地。”
孟清詞眼圈紅了,與謝山長相識不長,可在心中,睿智而灑,亦師亦友,亦不想山長和書院因而卷糾紛。
“若命該如此,我避無可避。”清詞閉上眼,輕聲道。
命運待,如此殘酷,若當日隨蕭珩去肅州,一切會否有不同,不愿去想,拼盡全力為自己爭取的人生,如今看來,更像是一個笑話。
山長一生專于治學,于人世故一道,還是天真了。既籌謀已久,書院周圍必已布下天羅地網,若有長歡的手,許還有逃離的可能,可沒有。
“山長,幫我設法將知微送到肅州,那里有人等。”清詞道。“至于知宜,知道該怎麼做,杭州的繡坊和書肆只能照常開,明面上不能有什麼異常。”
“便按照那些人的安排來罷。”想,若世上沒有孟清詞,不過是如同前一世一樣,的人固然傷心,卻依然能夠好好地活著,這便足夠了。
“至于阿詡,若為他好,便不要告訴他真相。”
*
“知微,你瞧這漁舟數點,若了畫,可不是一幅歸舟唱晚圖?”清詞伏在窗邊,看暮下,點點白帆似要駛水面的殘里,不由起了作畫的興致。
“姑娘說的是。”后的婢恭聲回道。
清詞回眸,看小姑娘低眉順眼,又一次真真切切意識到,如今,是在蘇州至京城的運河上,世上已無孟清詞,便是連知微知宜,此后都不能再陪在邊了,現在的份,是許知府的遠親,這一條未知前途卻兇險萬分的路,只能一個人來走。
這妙筆丹青,于而言,也再無用了。
“許姑娘,您仔細著了涼。”名喚憐雪的婢是許知府為安排的,并不清楚孟清詞的來,可了許知府的囑托,知道和遴選的那九位人是有些不同的,所以,服侍得很是盡心。
孟清詞,沈清嘉,許清妍,連自己,都不知自己究竟是誰了。
清詞角微勾,滿腔的興致頓時被潑了一盆冷水,轉過頭,又看向窗外的景,夕猛地一跳,沉水下,夜降臨,水面泛著幽幽的銀。
想,若是這樣縱一躍,是否也算是得了解……
甲板上傳來孩子嘰嘰喳喳說話的聲音,和清脆如玲的笑聲。
憐雪服侍這位姑娘已經半個多個月了,也揣不出的脾。這姑娘生得纖瘦,讓人一瞧便心生憐惜,可眉目間,看向人的時候,是極冷淡的,仿佛挾著冰雪,從不說笑,大部分時間都是沉默的,一坐便是半日,若不然,便是執筆抄寫佛經,可又很好伺候,甚吩咐做事。
但許知府千叮嚀萬囑咐,千萬仔細服侍,不可怠慢,是以這一路小心翼翼,待發現這姑娘確實不是難為人的子,才漸漸放下心來。
“姑娘,船到徐州了,們在商量著請求大人上岸逛逛,您要不要也下去風?”憐雪建議道。
便見這位許姑娘依然呆呆地看著窗外,對的話恍如未聞。
嘆了口氣,不免為這位主子的前途憂慮,都知道是為曾是祈王的當今天子采選的人,韶齡自是懷著不憧憬,可這位主子,竟如在青燈古佛旁一般,半點上進的心思也無。
再一日,船終于到了通州,上岸后,便有車馬接著們,送往曾經的祈王府。天子雖已登基,可們如今還得學好規矩才能宮。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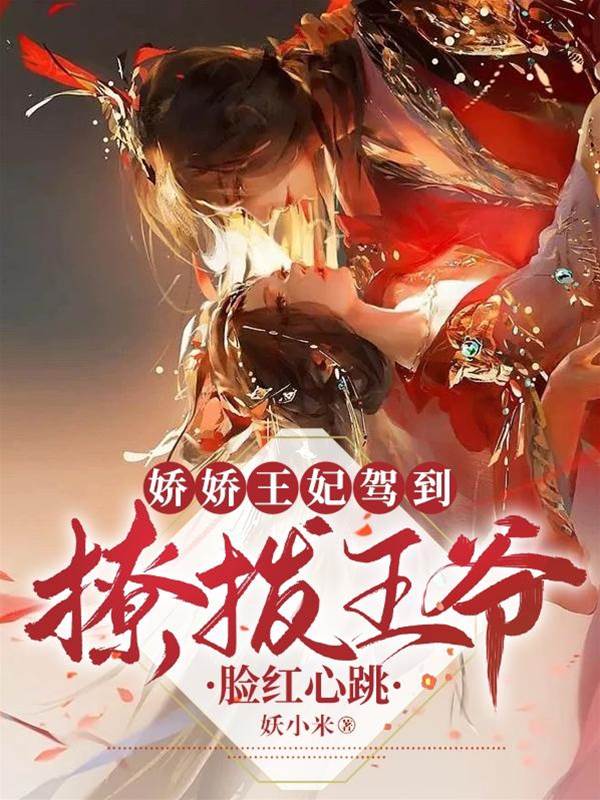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4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