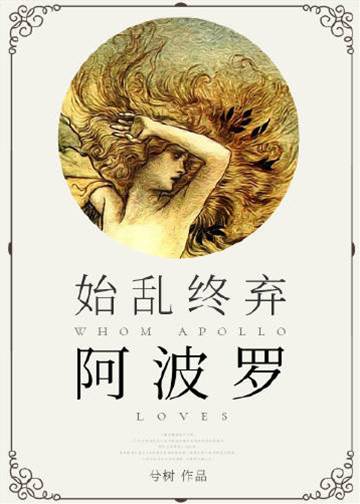《求生在動物世界[快穿]》 第391章 第 391 章【二合一補】
或早或晚都會出現挑戰者——
安瀾是這麼想的, 工作人員也是這麼想的。
但讓他們驚訝的是,一直到這個旱季的中晚期,到集群狩獵都開始變得困難的時候, 南部氏族還在盡心盡力地奉養著它們的王。
安瀾回過頭來,這才發現自己竟然已經建立起了如此龐大而穩固的政治同盟, 近臣們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協力維護著整個氏族的社群等級, 就好像一個失去了傳和制的車,靠著慣都能繼續向前滾很長一段距離。
況比原先預想得要好太多了。
在氏族員的配合下, 安瀾得到了更多時間門去保證政權的平穩過渡, 去保證一手建立起來的王朝能夠繼續存續, 走向繁榮昌盛, 而不是跟著這個注定要離開的掌舵者一起下墜、崩解。
南部氏族于是平穩地度過了旱季的尾梢。
這年的雨季來得格外早。
才不過九月功夫,滂沱大雨已經把整片草原都籠罩在了蒙蒙的水霧當中, 浮土被雨水浸,散發出一若有似無的腥味。
地勢較低的巢區再次變澤國, 今年新開辟的有一個塌了下去,母知道自己當時沒挖好, 只是埋頭給渾發抖的崽, 全然不敢對那些奉命過來幫忙刨坑的低位者擺臉。
壯壯帶著跳跳、橡樹子和其他聯盟員從不遠飛奔而過, 腳爪踏下去, 濺起大大小小的水珠, 半大崽們跟在后面踉踉蹌蹌地跑著, 沒跑兩步就有一只腳下絆蔥,再起時泥糊了一頭,草桿掛了一臉,張張就開始大聲哭嚎。
巢區里的一切好像都沒有變過一樣。
如果非要說和從前有什麼不同的話, 大概只有生活節奏變慢這檔事——不錯,南部氏族的生活節奏詭異地變慢了,這對斑鬣狗,乃至對大部分野生來說,都是相當罕見的現象。
斑鬣狗一生都在奔跑,有時是為了追逐獵,有時是為了驅逐對手,有時是為了躲避敵人,即使難得停歇下來,它們的心都還被困在權力的戰場上,永遠沒有可以徹底放松的時候,但為了照顧腳不便的王,南部氏族的行速度一慢再慢,即使是搶食環節都變得“慢條斯理”了起來。
核心員不是王的親,就是過王知遇、照拂、帶領上位的恩惠,幾個年輕后輩為了繼承權更是努力地表現自己,帕維卡帶著一些新朋友,帕莫嘉則和小落葉三個走得很近,一時間門,維護王權威的急先鋒隊伍空前膨脹,整個氏族的完食速度則不可避免地迎來了一次降低。
其他掠食者立刻注意到了這個異常現象。
它們中有的算不上什麼威脅,比如戰地記者胡狼,小小的三犬,以及南部氏族的老人領主花豹......但有的卻會給鬣狗帶來災禍。
聞風而的橫河獅群踩著點來搶過幾次食,越發南的北方獅群也常常在獵場附近游,雖然被獅子搶吃的不算什麼,后面也有很多機會可以“報復”回來,但至在被搶當天,有些低位者就要肚子,或者完雙倍乃至三倍的工作量。
安瀾不能坐視這種事持續發生。
于是在發現況不對后,迅速做出調整。以往都是等到呼號聲響起才會離開巢區,現在則是提早出,狩獵隊一出發就開始遙遙跟隨,一路跑跑停停,直到抵達現場,在加快進食速度的同時,還可以現場“督戰”,抓出尚不的后輩。
唯一的問題是......這麼做得冒一點風險。
如果按照早前的節奏,安瀾快到達狩獵現場時,鬣狗群不是已經基本集結完畢(防衛力量充足),就是已經被獅群沖散了(不用去);可是現在邊環繞著的只有盟臣和狩獵隊,而且還得等它們吃完飯才能抱團離開,可以說遇襲的窗口和可能都在變大。
為了防止悲劇發生,安瀾不得不默許部分高位者前后腳開始進食,甚至和肩并肩站在質最的地方共同進食。好在上述員不是看著長大的,就是長期效忠的、脈相連的、有繼承權卻力量積蓄不足的,暫時沒有一個會輕舉妄。
時間門就這樣慢慢走過。
一直關注著南部氏族的園區工作人員從最開始的擔憂到后來的驚訝,再到后來的自我說服,也只不過花了四個星期,在他們的注視當中,僅有的一點“反叛”苗頭也被鬣狗王迅速了下去。
事發生時在獵場里的是里德和凱恩。
兩名攝影師扛著□□短炮坐在鬣狗群邊上,一邊討論王痊愈的可能,一邊給幾名年長員拍攝近照,希記錄下盡可能多的瞬間門,將來它們要是不在了,還可以拿出來懷念。
那天距離巢區最近的狩獵隊是王室小團,正于壯年期的斑鬣狗們像風一樣掠過草場,頗技巧地拖倒并殺死了一頭年斑馬。
在獵垂死掙扎時,王室小團本來可以開始風卷殘云,但為首的斑鬣狗瑪姬圖顯得有些心不在焉,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遠方,只是稍微撕了兩口,吃飯還沒有呼號積極。
里德知道這只被稱為“巨人”的雌是下一任王的有力競爭者,而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門里都和阿米尼芙王形影不離,甚至可以說是被現任王照看著、教導著長大的,但無論拍攝多次,他都會為瑪姬圖表現出來的尊崇而震。
首領對聯盟員的影響力是立竿見影的。
在瑪姬圖不停眺的況下,其他雌也開始坐立不安,追隨者雄更是不敢越權上桌,大約三分鐘后,西邊的小土坡上浮現出十幾個影,它們才出半是敬畏、半是放松的復雜樣子。
從土坡上跑下來的是里德的“老人”幸運星,剛一跑近,它就高高興興地跟三腳架來了個近距離接;在幸運星后不遠跟著一步三回頭的壞孩;再往后是其他盟臣;接著是獾、狐貍和幾只走走停停的亞年。
墜在最后的是阿米尼芙王。
它走得很慢,而且在走時后背有些晃,伴恕加在一旁地跟隨著,因為型比雌小一號,看著倒像是一個十分合宜的“拐杖”。
到這里,一切都沒有什麼問題,凱恩掏出了筆記本在念念有詞,里德也做好了拍攝鬣狗群進食場面的準備——直到沖突忽然在獵邊發。
攝影師們完整看到了沖突發生的因:
瑪姬圖兩歲的兒在王進場時推搡了一下。
阿米尼芙王是傷了脊背,沒法快速奔跑,也不能長途奔襲,但又不是喪失了近距離作戰的本領,在到這樣蠻不講理的冒犯之后,它立刻用一個更加強橫的懲戒行還以。
年輕的斑鬣狗哪里見過這種陣仗。
不出半分鐘,它就被王鎖在了獵尸隔出來的狹小空間門當中,再往后退就要沒地方落腳,上掛著的都分不清是斑馬的還是它自己的。最讓人害怕的是,邊上站著的母親一直想往這里沖,但看那眼神完全不是想來搭把手的樣子。
事實也的確如此。
說瑪姬圖大驚失簡直是輕描淡寫,從里德的角度來看,這只雌好像沒想到自家兒竟然還能做出如此不敬的舉,在肢接發生時就下意識地就背起了耳朵,起了尾。
阿米尼芙王教訓完后輩,果然看向了它。
明明想好好表現、不想篡位也沒有那個能力去篡位的瑪姬圖真是有苦說不出,跟著兒吃了頓掛落;當天在場的其他亞年也統統被臺風尾掃到,經歷了一場由盟臣發的確認等級的洗禮。傍晚時分,巢區里還有咆哮聲和嘯聲在回響。
這次甚至都稱不上是“”的事件很快就被強權這雙手輕輕抹平,在那之后攝影師們也再沒有觀察到過類似況,南部氏族非常高效地運轉著,度過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在這段時間門里,安瀾把幾大聯盟差得團團轉。
于壯年期最有沖勁的王室被要求負擔起了狩獵的職責,箭標和壞孩像從前那樣肩并肩負擔起了巡邏并加強標記的職責,三角斑鬣狗、圓耳朵和新興力量們負擔起了保衛巢區的職責。
統治者聯盟,包括王室脈樹,所表現出來的忠誠和恭順是極染力的,即使況不佳,安瀾仍然能在盟臣的支持下繼續指引氏族。
可惜好景不長。
雨季走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或許是因為年歲到了,或許是因為磁場之間門的相互影響,氏族里忽然出現了一波離別,那些曾在氏族發展史上留下過獨特痕跡的雌開始一個接一個地遠行。
南部氏族首先失去的是三角斑鬣狗。
作為三朝元老,而且還是一個大型政治聯盟的前任首領,三角聯盟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端看現在有一條完整的強盛的脈樹是出自它手,就可以知道它的離去會對氏族造什麼影響。
其中到最大影響的就是箭標。
近年來它在跟小落葉的“斗爭“當中越發意識到了自己曾經的傲慢,也意識到了養育一個和自己對著干的兒究竟有多困難。在午夜夢回時,它會想起母親皮的溫度,想起母親的言傳教,想起母親看著它投向王時的無奈和縱容。
箭標完全沒有準備好接母親的離去。
而它也不是唯一一只陷這種境的斑鬣狗。
就在三角斑鬣狗離去后的第三周,已經無數次突破東非草原野生斑鬣狗壽命記錄的王太后也在一個雨夜里闔上了雙眼。
安瀾直到很久之后都記得清清楚楚:那天早上,母親久違地給了。因為年老衰,它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渾濁了,有些發明明已經被平了,卻還要倒過來再一遍。
著著,有三、四只高位后裔從邊上跑過,它們像是在追逐彼此的尾,沒頭沒腦地到撞,險些就撞到了坐在一旁的圓耳朵。
看到這群亞年過來,母親下意識地往側面避讓,然后才反應過來自己沒有必要后退,于是重新坐下來,稍顯吃力地勻了勻呼吸。
母親總是如此。
舊時低位者份留下的影子似乎很難被抹去。
即使在安瀾為王之后,它也活得像個低調的形者,滿足于有、有地方睡、不打攪的生活,偶然出手教導教導直系后輩,還是怕它們給家里最的兒帶來麻煩。
可就是這樣的母親,永遠響應著安瀾的呼喚:在希波侵巢區時,它和黑鬃王一起站出來和對手搏斗;在和獅群的沖突中,它加了其中一支隊伍,并因此重傷;在此后數年的王儲之爭里,最有資格發表見解的它卻保持了沉默。
就是這樣的母親,在上豪擲了全部的籌碼。
那天晚上下著雨,空氣很冷,巢區里到都是崽細細的哭啼聲,安瀾從睡夢中驚醒,察覺一側有些寒涼。下意識地往邊上了,就和小時候一樣,但在那時,和依偎著進夢鄉的母親已經走過了夢的奇境,踏了長眠的國度。
那曾經哺育過的逐漸變得僵,等太升起來時,安瀾拖著不太靈的后,在小時候住過的巢邊挖了一個。
母親的故去已然是一個不可接的損失。
就好像嫌還不夠打擊一樣,在三角斑鬣狗和母親接連離開之后,本就渾舊傷的壞孩也開始況惡化,很快就陷了走困難的境地。
安瀾想著讓它過得舒服一點,又怕它不愿意接其他氏族員的投喂,便強打神,像過去給黑鬃王帶飯時那樣,親自給它帶食回來吃。奇怪的是,以往休養過許多次的壞孩這一次拒絕了投喂,沒有領。
它的骨子里還有那狠勁。
那是一燃燒著的烈焰,從出生開始就支撐著壞孩和所有擋在前方的敵人戰斗,推著它朝著最耀眼的地方奔跑。可是如今,擋在前方的不是敵人,而是它自己的/,這把燃燒在靈魂里的火無法向外升騰,吞噬敵人的,便只能向消磨,吞噬這/的生命力。
壞孩太想證明自己了。
在南部氏族的下一次狩獵中,步行困難的它遲遲不肯放棄,幾乎是一瘸一拐地跟上了大部隊,每走一步,它就會不控制地輕輕地哀嚎一聲,然后又因為強烈的自尊心而閉。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無法對那種痛苦冷靜以待。
安瀾實在看不下去,只好以王的份要求壞孩留在巢區里,不指它能夠恢復如初,至把后來幾次狩獵的傷養好,以免在追逐中耗盡力,倒在草原深某個不知名的角落里。
事后想來,這個完全出于意和保護的舉,或許正是垮駱駝的最后一稻草。
從安瀾把它留在巢區的那一天起,壞孩就不再站起來嘗試奔跑了,事實上,它連走都幾乎不怎麼走,每天只是坐在空地邊緣,眼睛瞇著,耳朵耷拉著,得像在拉風箱。
所有斑鬣狗都能嗅到從它傷口中傳來的不詳的腐臭味,也都能意識到它的生命已經開始不可避免地朝著死亡的影落。
被留在巢區休養的壞孩努力支撐了兩周。
兩周后的某個清晨,安瀾正跟在預備趕往中部獵場的王室小團后離開巢區,余忽然看到一個消瘦的影從側面追上了大部隊。
這天的壞孩格外堅定,無論幾只較為親近的后輩怎樣勸說,它都不肯留在后方等待獵被殺死,而是竭盡全力地追上了狩獵隊。
它仿佛仔細清理過自己的皮,那因為衰老而緩慢褪的發在晨曦底下顯得格外順服,連帶著它自己的氣神看著都好了不。
一步,兩步,三步。
壞孩試探地小跑了兩步,然后撒奔跑起來。
這天晚些時候,它在狂奔的水牛群里貢獻出了自己一生當中最完的演出,那幾乎是毫無保留的,是炫技的,是不可復制的,以至于后輩們只能敬畏地旁觀,看著那不知道從何發出來的磅礴力量將獵死死鎖在原地,看著那牛犢哀嚎著倒下,看著那紅的鮮漫天潑灑,澆在壞孩的頭上上,仿佛是它被母親娩下時帶出來的一層胎,是它殺死同胞姐妹時得以被同類也被人類窺見的環,是它發出的一聲震耳聾的宣告——
猜你喜歡
-
完結492 章

特工皇妃:皇上我要廢了你
“跟我走,我娶你為妻。”女子緩慢里拉開頭發,露出魔鬼似的半臉,淡淡的道:“這樣,你還要我跟你走嗎?”她是帝國家喻戶曉的丑女,廢物。卻一言驚天下,王子,不嫁。王妃,我不稀罕。金麟豈是池中物,一遇風云變化龍。誰知道如此的廢物身后卻是那驚才絕艷的…
89.3萬字8 46465 -
完結1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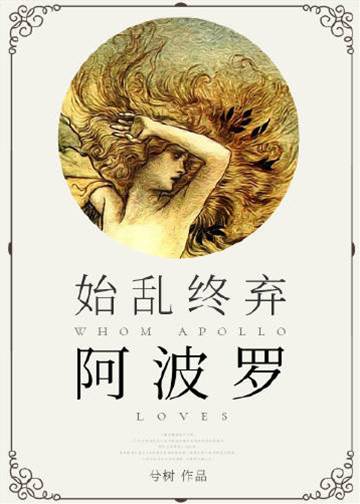
始亂終棄阿波羅后[希臘神話]
卡珊卓遭遇意外身故,一個自稱愛神的家伙說只要她愿意幫他懲戒傲慢的阿波羅,就可以獲得第二次生命。具體要怎麼懲戒?當然是騙走奧林波斯第一美男子的心再無情將其踐踏,讓他體會求而不得的痛苦,對愛的力量低頭。卡珊卓:怎麼看都是我賺了,好耶!…
30.2萬字8 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