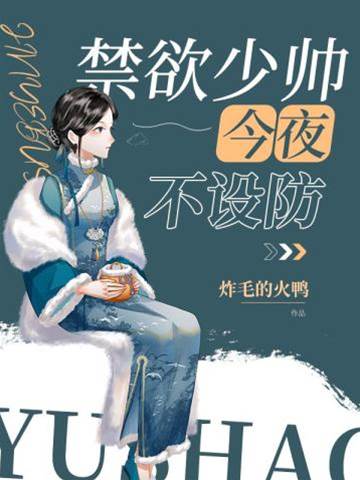《他的小撩精》 第53章 第53撩(一更)
“咔噠。”
門突然打開,鹿笙始料不及,的重量帶著直接往里栽,眼看就要栽地上,南懷璟條件反地手將撈住。
撈是撈住了,不過鹿笙的側臉就這麼直接在了他那不知是故意還是沒來及扣上紐扣的小腹上。
他腰腹上還有水,順著腹的紋路往下。
覺到臉上的意和不算滾燙的滾燙,鹿笙側著的臉轉正,剛剛好,他的腹和人魚線不偏不倚地扎進眼底。
有張力。
這是鹿笙的第一反應。
的重量,還有一半在南懷璟的兩條手臂上,忘了站起來,視線從那條人魚線一點點往上,腹、口、結,最后目定在他的下上。
因為仰著臉,南懷璟下的那滴晶瑩剔的水珠就這麼堂而皇之地砸了下來。
浴室里還有嘩嘩作響的水聲,可鹿笙卻清清楚楚的聽見了“啪嗒”一聲響。
水滴砸在了的鼻尖上,鹿笙的眼睫也跟著眨了一下。
不知該說大膽,還是整個人都是懵的,就這麼明目張膽地看著他,直到臉上燒灼的溫度燙的心里一咯噔。
猛地從他懷里彈開,睡的黑和他的白,形了強烈的反差,像一把勾子,勾得視線止不住地往那黑白界瞄。
其實不止臉紅,南懷璟也被看的眼睫。
明明想著的,結果被看的,南懷璟下意識就手將睡往中間攏。
也因為他的作,讓鹿笙徹底回了神,眉心一皺,就差拿手指他了:“你、你、你開門怎麼也不說一聲!”
這帶著控訴的腔調,讓南懷璟失笑:“我哪知道你在門口。”
這話頓時提醒了鹿笙。
是在聽,可卻‘惡人先告狀’。
立馬轉,背過去。
不過很快,就找到了理由:“我、我那是看你、看你洗了這麼長的時間,想看看你是不是、是不是在里面出了什麼意外。”雖然結結的,可聲調卻揚著,聽著很是虛張聲勢。
浴室里繚繞的水汽在往外鉆,鹿笙后知后覺花灑的水還沒有關,不心虛了,轉過來,語氣兇:“既然你都洗完了,干嘛不把水關掉!”
南懷璟往浴室里看了眼,“我怕冷,所以想著洗完再關。”他眼波平靜的看不出一丁點的心虛,好像只是在陳述事實一般。
可他越是這樣鎮定,越顯得鹿笙心虛。
又惱又的,眉心一擰,“這麼怕冷,那你還穿這麼!”說著,又瞥了眼他前,可惜只能看見他v型領口出的皮。
因為的視線,南懷璟也不由得低頭看了眼自己。
其實在來之前,他以為‘□□’不了的,沒想到……
他悄悄彎了點角,漫不經心地把紐扣扣上,扣完紐扣,他才去浴室把水閥關了。
鹿笙站在門邊,表依舊別別扭扭:“很晚了,我要睡覺了。”
這是在變相地趕他走呢!
南懷璟雖然表看不出一樣,可也心虛著,走到邊的時候,他站住腳,低頭看。
鹿笙兩手擰著睡兩側的擺,目垂著,見他站著不,這才仰頭看他。
目對上,兩人都能覺到彼此眼底的灼熱。
心臟又開始突突直跳,鹿笙抿了抿,左腳往旁邊挪了一點,又挪一點,挪到第三下的時候,一個轉,就在南懷璟準備手去拉手的時候,快速逃離了他的邊,溜進了自己的房間。
只聽“砰”的一聲,房間的門關上了。
南懷璟出的手落了空,他怔在原地,看著三米遠不到的房門,呆了好一會兒沒回過神。
他準備了好些的話還沒來得及跟說,就這麼逃了。
南懷璟低頭看著空落落的手心,驀地,他突然笑了聲。
能逃,說明他的“”對真的有用。
房間里,鹿笙后背抵著門,一直等到外面傳來了關門聲,的心跳才漸漸平復下來。
第二天上午,鹿笙醒的晚,昨晚很晚才睡,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里全是他的腹和人魚線。
一直到凌晨兩點,困意才泛上來,失眠的兩個多小時,別的沒想通,但想通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肯定是打著借用衛生間的幌子,故意來擾心神不寧的!
以至于眼皮在打架的時候,腦子里一直盤旋著三個字:心機男。
想到這,鹿笙又看了眼天花板,“心機男”三個字經過一夜的沉淀,消失殆盡,反倒是那六塊腹和那條人魚線又開始往腦海里涌。
也沒見他健過,腹和人魚線都是從哪兒來的?
難道每晚睡覺前在房間里練的?
越想心里越燥,把被子拉到頭頂,悶了一會兒,心里更燥了,又一把掀開被子。
從枕頭下到手機,給白薇薇打了個電話。
白薇薇在上班,所以聲音悄咪咪的:“怎麼啦?”
鹿笙嘆口氣:“好煩。”
“煩什麼呀?煩你家南教授還是煩你自己啊?”
又嘆氣:“我。”
白薇薇笑著打趣:“煩你自己放不下他,開始心,開始搖擺不定,恨不得馬上投他的懷抱啊?”
不然呢?
難道煩他的腹和人魚線嗎?
鹿笙岔開話題:“我想英寶了。”
“哎喲,”白薇薇咂:“你還能想起英寶啊?”
鹿笙眼皮耷拉著,在揪被子:“你說,要是他知道是我把英寶藏起來的,會不會生氣?”
“他生氣?”白薇薇撇:“他生哪門子的氣,是他先把英寶藏起來的好嗎?”
鹿笙沒說話。
這回,到白薇薇嘆氣了:“你說你,就你這不堅定的立場,估計早就被他看出你那故意端著的小心思了!”
這要是擱昨晚之前,鹿笙絕對要反駁,可昨晚那面紅耳赤的模樣,估計傻子都看出來了。
真是令智昏。
電話那頭,白薇薇突然低聲音:“不說了,主任來了。”
鹿笙知趣地把電話掛斷。
看了眼時間,已經十點多了,沉沉地吐出一口氣,掀開被子下了床。
今天天氣不錯,南懷璟出門的時候,頭頂彤云朵朵。
昨晚他睡的也遲,但他早上還是很早就起來了,在簡士那吃完早飯,他八點就去了健房,昨晚回到三樓后,他在衛生間里照了鏡子,以前他鍛煉就只是單純為了鍛煉,卻沒想到這副材竟在關鍵時刻派上了用場。
在健房練了不到兩小時,他就去了商場。
昨天南孝宇跟他說的那些哄孩的方法,當時他還嗤之以鼻,結果‘功’,所以他想著,‘包包鞋子服’或許也是一種攻破方法。
不過他沒去買包包鞋子服,他去了一樓的化妝品專柜。
一大早第一單生意,加上又是一個男人,還是長的這樣好看的男人,店員很熱:“請問需要什麼?”
他抬頭,禮貌笑笑,說:“我自己先看看。”
專柜是方形,轉到第三面的時候,他指著其中一款:“這款給我拿一套。”
南懷璟昨晚在鹿笙那看到的那一套護品,不是鹿笙自己買的,是白薇薇的客戶送的,白薇薇自己留了一套,給了鹿笙一套。
店員沒有立即開單:“我們店滿八千會送一套價值一千的面,不知您還有沒有其他需要的。”
南懷璟不是一個會為了滿減送就會湊單的人,他剛想說不用了——
“我們店還有男士護,和剛剛您買的是一個系列,都是補水保的,很適合秋冬。”
他猶豫了兩秒,也就兩秒,他說:“那給我也拿一套吧。”
店員就喜歡做男顧客的生意,特別是這種一看就很爽快的男顧客:“您稍等,我來給您開單。”
其實在來商場的路上,南懷璟沒打算買別的,可都走到商場門口了,他又折了回來。
二樓是裝,三樓是男裝,南懷璟去了四樓,轉悠了一圈,逛了四家店,手里多了六個袋子。
回到知南街,他坐在車里給簡士打電話:“媽,鹿笙在家嗎?”
簡士說不在,剛剛出去了。
他“哦”了聲,剛想再問一句去哪了,話到邊,又咽了回去。
買的東西都在副駕駛,他拎著東西下車,走到巷口的時候,他歪了點子,往咖啡店里瞄了眼。
進了院子,簡士正在樓檐下曬太,見他大包小包的,忙迎上去:“都買的什麼呀?”
南懷璟把其中一個黑的紙袋給:“我先上去了。”
簡士低著頭,從袋子里撈出一個麻灰的圍巾。
這什麼眼神啊,都五十好幾的人了,還給買這麼暗的,這不顯得更老?
就說生兒子不如生兒,這要是個兒,鐵定給買個鮮艷的!
到了中午吃飯的點,鹿笙還沒有回來,南懷璟手里的水杯已經續到了第三杯,簡士從樓檐下出來,走到院子里剛轉抬頭,就看見南懷璟端著個水杯,在看……
簡士回頭看了眼,這是在看什麼?
不管在看什麼,反正在簡士看來,他那副站直不的模樣,簡直就是一妻石。
現在知道妻了,早干嘛去了。
這要不是自己的兒子,簡士都想罵一句‘賤骨頭’。
簡士沒先喊他,喊:“孝宇,吃飯了。”
飄忽的思緒收回來,南懷璟低頭看了眼時間,都十二點十分了,為什麼還沒回來?
是去哪了呢?
想發短信問問,可又覺得那樣做像是監視似的,別說他們現在還不是男朋友的關系,就算是了,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私人空間……
南懷璟皺了皺眉,腦海里盤旋著這四個字。
他在想,這私人空間的界限是什麼,默了會兒,他思緒又飄到另一個問題上,如果他們以后了男朋友,他是管著還是慣著……
想到自己比大好幾歲,好像,就算管著也沒什麼不對。
可是如果管多了,會不會煩?
想到這,他攤開的眉心又擰一塊去了,過了會兒,又攤開。
不行,那就慣著吧。
想到這,他突然失笑,真的,他有點想象不出來自己慣著一個人會是什麼樣。
就這麼笑著笑著,視線落到樓下,角的笑就這麼突然僵住了。
樓下,簡士正抱著胳膊,仰著頭,好整以暇地盯著他看,旁邊還站著他弟南孝宇。
兩人意味深長的表讓南懷璟驟然尷尬,別別扭扭的一張臉,轉也不是,繼續站著也不是的。
簡士拖著調子:“鹿笙沒回來,你要不要問問在哪啊?”
他沒說話,轉往樓梯口去。
一直到下午一點,鹿笙才回來,進了院子,沒有像往常一樣抬頭看三樓,一步步走到石桌前,攥著包帶的手緩緩松開,魂不守舍地坐下。
樓上,南懷璟就坐在客廳里,聽見門聲,他起出門。
鹿笙背對著臺,坐在那里一不的。
明明看不見的臉,可南懷璟卻依舊覺到了的異常。
二十分鐘后,鹿笙從石凳上起,南懷璟還站在臺上,鹿笙依舊沒有抬頭。
樓上,南懷璟看得出步子的重緩。
眉心蹙了蹙,他遲疑了好一會兒的功夫才穿過臺,上了四樓,到了平階那兒,他又頓住腳,要不是他在門把上掛了東西,他早就下樓去找了。
而鹿笙,走到門口,掏出鑰匙,掀開門簾的時候,目頓住。
門把上掛著一個紙袋,袋上的英文字母認得,是現在在用的護品的牌子,往臺那頭看去,過了許久,才緩緩收回目。
南懷璟背靠墻,聽見關門聲,他眼波頓了一下。
自從裝了門簾后,鹿笙鮮會鎖門,可剛剛那聲門響,他清清楚楚聽見了落鎖的聲音。
不對,緒不對。
出去了一趟,是遇到什麼事了嗎?
距離新年還有六天的時間,老家不在這里,那是不是要回去過年?
如果回去的話,什麼時候走,又什麼時候回來?
把他的影子投的筆直,他踩著自己的影子,低頭看著腳尖,猶豫許久,他從口袋里掏出手機,給鹿笙發了一條短信:【中午吃飯了嗎?】
他沒上樓,就站在原地等,可惜等了十幾分鐘,鹿笙的短信還是沒有回過來。
平時耐心很好的一人,這會兒,心里頭焦灼的厲害,他想在回老家之前把哄好,不想這一去一回中間再有什麼變故,可依照目前況來看,他這進度條明顯慢了,所以他要不要再做些什麼……
可是他還能做些什麼呢?
他扭頭看向臺外的半截天空,驀地,他突然腳步一轉,快速上了樓。
南懷璟的衛生間里有一個浴缸,冰涼的水柱流了許久,他雙手著洗漱臺面,抬頭看著鏡子里的自己,看了半晌,他啞然失笑。
若說他不夠君子,倒也算得上坦,如今呢,苦計的伎倆都被他用上了。
他輕嘆一口氣,垂頭失笑。
所以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眼看浴缸里的水已經過了大半,他邊解著服的扣子,邊走過去,關了水閥,他攪了攪浴缸里的冰涼的冷水,眼看扣子就剩一顆,他手里的作突然頓住。
萬一他真因為泡了冷水澡生了病,這一病,就不他控制了,若是再病的重了,連床都下不了的話,那他豈不是連追都追不上了?
他站在浴缸邊,眼波流轉了幾圈后,他看向鏡子。
猜你喜歡
-
完結2999 章
億萬爹地天天寵
十八歲那年,葉薇薇被父母逼迫,頂替孿生姐姐入獄,在獄中生下一對龍鳳胎。五年後,她攜女出獄,鬥心機女白蓮花,順便救了一隻軟萌的小包子。從此,她不再是刑滿釋放人員,而是被蕭景寒寵到腿軟的蕭太太。“爸比,有個影後欺負媽咪。”小包子氣紅了臉。某BOSS立即打了一個電話,“敢欺負我的女人,全球封殺!”“爸比,有個帥帥的叔叔送媽咪花。”小蘿莉滿眼星星。某BOSS磨刀霍霍,“讓他破產!”
268.9萬字8.18 225760 -
完結65 章

步步淪陷
唐晚20歲那年遇到傅津南。那天是R大70周年校慶,一大排嘉賓中,唐晚一眼瞧見角落的傅津南。 那排屬他最年輕,也屬他最格格不入。 只一眼,唐晚就迷上了這位花名遠揚的傅公子。 副校長難堪之際,她上前解圍,問他:“可以簽個名嗎?” 他憋著笑,眼帶戲謔說:“簽唄。” 他寫了一手好字,瘦金體,筆鋒瀟灑有力,平時應該沒少練。 可就這麼一個簽名,讓她鬼迷了心竅。 后來,高樓起、高樓塌,不過欷吁間。 狼狽倉促之際,傅津南問:“滿滿,你跟我說句實話,你真愛過我嗎?” “沒有。從來沒有。” *京圈大佬vs心機女學生 *一場“你情我愿”的游戲。 *結局he
24.2萬字8 8035 -
完結532 章

顧先生相思已入骨
一條留言,引她步步踏入深淵。 親眼目睹父親葬身火海,母親精神失常,寶寶猝死腹中,結婚三年的丈夫勾結他人處心積慮逼她至死。 許是上天憐憫,她不甘的靈魂重生在一個剛出道的小明星身上,一醒來卻發現深陷重重危機,前世今生的仇敵齊聚一堂,等著將她推入地獄! 簡寧發誓,這一輩子,哪怕活得再卑微再不擇手段,哪怕遭受萬千唾棄和謾罵,那些欠了她的人,一個都別想逃! 所有的仇恨她都會連本帶利一一向他們討回來! 從此,三線小明星步步蛻變為娛樂圈的緋聞女王、頂級天後,綻放出無人匹敵的璀璨光芒,她身邊的男伴換了一個又一個,甚至揚言,天下的豪門都跟她有一腿……
96.9萬字8 6363 -
完結10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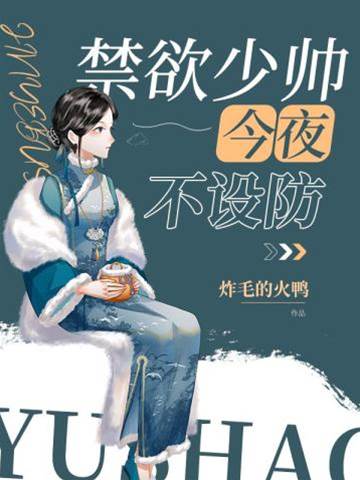
禁欲少帥今夜不設防
一朝身死,她被家人斷開屍骨,抽幹鮮血,還被用符紙鎮壓,無法投胎轉世。她原以為自己會一直作為魂魄遊蕩下去,沒想到她曾經最害怕的男人會將她屍骨挖出,小心珍藏。他散盡家財保她屍身不腐;他與她拜堂成親日日相對;直到有一天,他誤信讒言,剔骨削肉,為她而死。……所幸老天待她不薄,她重活一世,卷土而來,與鬼崽崽結下血契,得到了斬天滅地的力量。她奪家產、鬥惡母、賺大錢,還要保護那個對她至死不渝的愛人。而那個上輩子手段狠戾,殺伐果決的少帥,現在卻夜夜將她摟在懷中,低聲呢喃:“太太救了我,我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了。”
193.2萬字8 20524 -
完結339 章

醉酒后,我拿下了人間最香小狼狗
深夜買醉,褚柔直接睡到了人間巔峰!感情糾纏,墨小少爺出面擺平。公司業績,墨小少爺出面擺平。家庭瑣事,墨小少爺出面擺平。褚柔靠在墨池懷里,感激道“寶寶,謝謝你幫了我這麼多!”墨池翻身而上,“姐姐嘴上說感謝太敷衍,還是給我生個寶寶實際點。”年輕力壯,龍精虎猛,精力旺盛、血氣方剛,褚柔想說弟弟真香!
59.5萬字8.18 31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