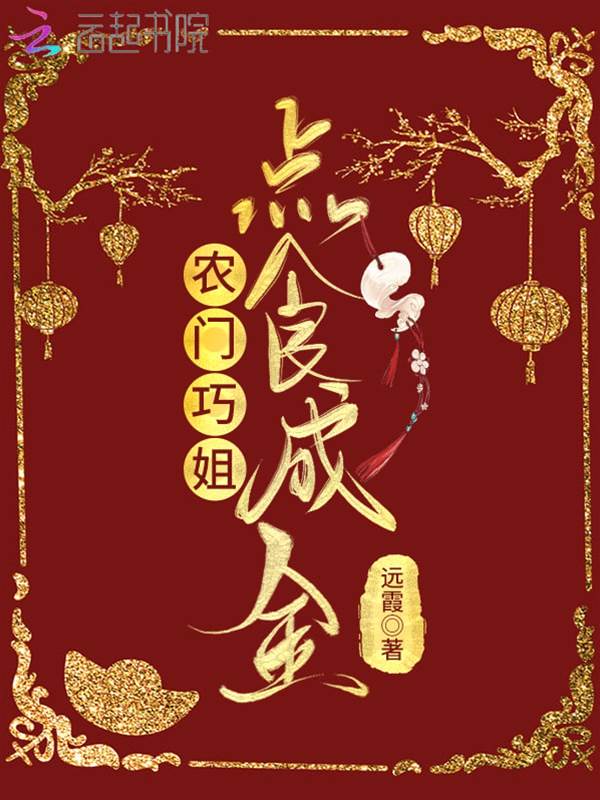《棄婦覺醒后(雙重生)》 第95章 太子蘭因看著眼前這個孩子,莫名覺得……
“你說什麼?!”
趙乾本就臉『』蒼,一聽這話,他頓時掙扎著起來,可手剛掀開被子,人才起來便又摔了回去。
康禮連忙手扶住他。
龐牧面『』關切,“陛,您事吧?”
“不用管我,你繼續說。”趙乾沙啞著嗓音坐在龍床上,他臉『』慘且凝重,雙手握拳抵在膝上,目一眨不眨地看著龐牧,沉聲問人,“到底怎麼回事?太子出什麼事了?”
龐牧不敢瞞,連忙答道:“屬接到龍影衛派人送來的口信,來人說有人查到太子還存活于世的消息,并且追查到了長先生那邊……”
他越往說,趙乾的臉『』便越發難看,“然后呢?”
龐牧垂首沉聲,“長先生察覺到不對之后便立刻讓影衛護送太子離開,至于先生……”
趙乾約覺不好,忙問,“先生怎麼了?”
“先生他……”能做到龍影衛首領的人,手里沾染的人命自然不計其數,按理說龐牧早就能淡然面對同伴的生死了,就連他自,縱使被人拿刀子抵著脖子,只怕不會眨一眼,可想到自聽到的那個消息,他的聲音還是不自啞了。他雙手攥拳,聲音都在抖,“先生他被杜賊的人以族人威脅,與賊人周旋之際,一把火燒死了族人,自……跟著赴死了。”
“噗——”
“陛!”康禮他噴,立刻變了臉『』,他去請太醫,卻被趙乾握住手。
鮮在趙乾的明黃寢服上化作點點紅梅,他卻無暇去顧,他雙眼潤,面『』蒼,聲音都在發抖,“是朕害了先生……是朕害了先生!”
康禮勸道:“這怎麼能怪您?怪該怪那些賊人!”
龐牧連忙跟著說道:“康公公說的對,這和您無關,臣聽來人回稟,先生及其族人是甘愿赴死的,就連先生最小的孫兒面對死亡都有哭鬧。”
登上帝位注定殺機重重。
當初他坐上這個位置不犧牲了許人?趙乾相信長先生是心甘愿赴死,可他怎麼能如此坦然地接這一大子的犧牲?如果當初不是他實在找不到人,先生原本是能安晚年的,何至于到了這把年紀還落到這樣的結局,甚至連一個族人未能留,一想到龐牧那句“最小的孫兒都有哭鬧”,趙乾的眼睛就更加紅了。
“杜、誠、之!”
他一字一頓,心中如有千萬火把一并燃燒,外面雷電加,閃電在窗外劈過,照亮趙乾怒火滔天的臉,暫且心中的震怒,他問龐牧,“太子呢?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太子……”
龐牧的臉『』卻愈發難看了,“太子擔心先生一出事又地折回,被杜賊的人發現蹤跡,影衛的人折損了十幾名兄弟把太子帶,但……現在屬聯系不到跟在太子邊的影衛了,只知道杜賊那邊還在追查太子的蹤跡,想來太子還未被他們捉住。”
對于這個結果,殿中三人的臉『』都不算好看。
尤其是趙乾。
他把自這個兒子保護了十年,就是想把杜誠之解決掉之后接他回京,讓他可以平平安安榮登大寶,怕人發現他還存活于世的消息,他十年不敢他一面,只能通過畫像和先生的書信知曉他如今過如何,想到他藏這麼匿,竟然還是被杜誠之找到了!現在太子不蹤影,先生一又慘死……趙乾一溫和的臉『』徹底變鷙來。
他起在殿中踱步。
腳步聲被外面的雨水蓋過,趙乾了許久方才和龐牧發話,“你親自派人去找太子的蹤跡,若找到,直接迎進皇宮。”原本藏著非池是怕他遇到危險,可如今,顯然是把他放在邊最好,杜誠之就算膽子大,還敢明目張膽弒君不?
龐牧立刻領命告退。
等他后,趙乾又到書桌前,他親自提筆書寫了一封信,又從暗匣中出一張畫像,給康禮,“找人送到齊豫的手中。”
康禮心一驚,“您這是……”
趙乾默然片刻方說,“杜誠之靜鬧那麼大顯然是想讓太子活著回京,龐牧雖然是影衛,但杜誠之人老謀深算,想必早就知道龐牧此人,他這番離京只怕被人盯著不好行,正好齊豫在江南,讓他在江南搜查,若找到太子便帶在邊。”他說著到窗邊,窗子被他推開,外頭的雨一子全部被澆灌了進來,一眨眼的功夫,趙乾的寢服就被雨水澆。
康禮勸他離開。
趙乾卻未理會,他沉默地握著拳頭看著窗外,任雨水潑面,蒼的一張一合,喃喃說道:“非池不能有事。”
不僅僅因他是他和相宜唯一的孩子,更因他是大周的希。
如果真的讓他的次子趙衍登基,以他的心『』絕對會杜誠之的傀儡,屆時整個大周都將是杜的囊中之!
……
西寧王府。
同樣一個雷電加的夜里,杜厲、杜恪兄弟倆齊齊跪在地上。
杜誠之坐在主位,上依舊是一件樸素的褐『』道服,他看著底的兄弟倆沉默不語。
外面的雷聲愈發襯出屋中的安靜,沉默間,杜恪率先說道:“父親,這事和大哥有關系,是我做事做干凈,讓人提前知道了消息,這才讓人跑了。”
杜厲本以發生這樣大的事,他這庶弟必定父親告狀,想到他竟把所有的過錯都攬到了自的上,驚詫之余,他忍不住扭頭朝邊的杜恪看了一眼,一時搞不懂他這庶弟肚子里賣什麼『藥』。他自然不相信他會這麼好心,雖說這些年他這庶弟韜養晦,每次看到他是恭敬有加,可年輕時他可在他手上吃虧。
“這事和你關系。”杜誠之終于開口了,“怪就怪這個孽障!”
不同和杜恪說起話時的平靜,面對杜厲,他難掩怒容,大掌重拍邊茶幾,厲聲喝道:“你個孽障,你可知道你做錯了什麼?”
杜厲知道這次自犯了大錯。
誰想到那個自出娘胎就斷氣的小孩竟然還活著。
他當然知道那個人的存在對他們杜有怎麼樣的威脅,原本天子就二皇子一個孩子,二皇子出自杜,是他的外甥,以后等天子駕崩,毫無疑問是他的小外甥登基,屆時,整個大周不都是他們杜說了算?可偏偏還有一個孩子,那個孩子是元后所生,論份地位,比他的小外甥還尊貴。
可以想想,等那個孩子回京,朝堂會掀起什麼樣的風波。
可知道歸知道,被自親爹當著他最厭惡的那個庶弟教訓,杜厲自然臉『』難看,他忍不住嘀咕,“您若早些時候告訴我,我怎麼會跟上去,又怎麼會打草驚蛇?”
“你!”
杜誠之這次是真的被他氣急了,他想訓斥,張口卻是一陣咳嗽,老仆連忙遞了茶盞過去,杜恪面『』關切,“父親,您事吧?”
杜厲同樣心生擔憂,“爹,您事吧?”
杜誠之說話,他咳了好一會才消停來,看著那對兄弟,他頭疼不已,理會杜厲,他和杜恪說道:“恪兒,你拿著我的令牌繼續去搜查那人的蹤跡,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人回京。”
杜恪忙應聲答應。
“爹,我呢?”杜厲不肯杜恪搶了所有功勞。
可杜誠之冷著一張臉看著他,好氣道:“你還嫌自錯不夠?這陣子,你給我好好待在府中,哪里不準去!”
“爹!”
“出去!”
杜厲的臉一會青一會紅,最后還是起拂袖離開,的時候,他還地看了一眼邊還跪著的杜恪,重重哼了一聲。
杜恪卻從始至終都有什麼變化。
“這個逆子……”杜誠之對自這個嫡子又氣又惱卻無可奈何,搖了搖頭,他和杜恪說,“你起來吧,事急,你收拾就立刻出發。”
杜恪應聲起。
的時候,他還說道:“兒子這一,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秋天涼雨水又,請父親務必注意子。”說完還地叮嚀老仆,“我不在的這陣子,勞寧伯辛苦些。”
老仆忙道:“爺放心。”
杜恪這才起離開。
他后,杜誠之忽然嘆氣,“就厲兒那個心『』,我怎麼放心把杜給他?”
老仆說,“大爺是赤子之心,何況,還有二爺輔佐呢。”
杜誠之冷嗤,“你真以這次是厲兒的錯?”
老仆驚訝,“您懷疑……”
“就老二那個玲瓏心思,你真以他不知道厲兒跟蹤他?他故意當做發現,不過是篤定厲兒那個『』子一定會鬧出事,只可惜,他想到宋立這麼固執,寧可全赴死不肯『』太子的行蹤。”
“那您怎麼還肯把這事給他?”
“不給他又能給誰?厲兒是這麼個『』子,其余杜子孫更是一個中用的!”權勢滔天到讓當今天子都敬畏的西寧王此時卻重重嘆了口氣,他凝窗外風雨,沉聲,“懷明和長林,我原本都是厲兒做準備,就算等我百年歸去,有這二人輔佐厲兒,我可以放心。”
“想到這次竟然都被那姓齊的小兒拿。”
他面『』鷙。
金『』閃電在窗外劈過,此時的杜誠之無平的溫和,那眉眼之間全是嗜的殺『』。
“若老二能用,那固然最好,若不能用,在我離開之前……”后面半句話被掩在風雨雷電之中,卻還是被站在窗外的杜恪聽一清二楚。
他面『』慘。
指骨一點點收。
*
九月初十是蘭因外祖父的生忌。
了幾天的雨,今總算放晴,蘭因陪著王老夫人去靈谷寺祭拜外祖父。
靈谷寺雖然不比鳴寺、大報恩寺有名,但因位于紫金山,環境怡人,王老夫人從前便常來此。同行的有蘭因還有三位舅母以及大表哥、小表弟還有小舅舅,一行人從烏巷出發至寺廟已是中午,先用了午膳,又聽住持念了佛經,至傍晚,其余人先行離開,蘭因陪著外祖母繼續留在寺廟,打算在這住上幾天。
外祖母和外祖父年夫妻,甚篤,可惜天妒英才,外祖父未足四十便離世。
每年這個時候,外祖母的緒都十分低落,蘭因從前在金陵的時候會陪著外祖母在這小住幾。
倒不算無聊。
每陪著外祖母上早課,余后抄寫佛經,閑來無事便在寺中逛逛。
靈谷寺的桂花格外好聞。
蘭因還地挑了一天摘了花,曬干之后做了一個香囊讓松岳托程鏢頭送去臨安。
這一個月,他們雖然有面,但書信卻不斷,知道齊豫如今暫且擔任臨安知府,等陛派委任的人過來才能離開,雖想他,卻知道公事重,不過上回信中,他曾所言,應該不就可以來金陵了。
……
又過了兩三天。
在鄉試即將放榜前,蘭因終于陪著外祖母山了。
來接人的是蘭因的大表哥。
依舊是往來時的路,只是這回路過一個村莊,蘭因卻聽到外面傳來一陣打鬧聲。
“表哥,外面怎麼了?”外祖母還在小睡,蘭因著嗓音問王則。
王則看了一眼,與蘭因說,“是幾個小孩在欺負一個孩子。”
蘭因蹙眉,打簾一看,果然如此。
幾個穿著半新不舊裳的小孩正在踢踹一個蓬頭垢發的男孩,那男孩量很高,不知天有洗澡了,上臟兮兮的,頭發『』的不行,遮住大半張臉,只有『』出的一只眼睛清亮干凈。
他手里握著一只臟了的包子,就像小狼崽子護食一般握著,子蜷起拿后背對他們。
“怎麼了?”外面的靜太大,王老夫人醒了。
蘭因與回了話。
王老夫人蹙眉,與王則待,“阿則,你讓人去問問怎麼回事,好好的孩子可別被打死了。”
“是。”
片刻功夫后,王的護衛帶著那個孩子過來。
離近,蘭因發現那孩子竟生很高,看不清臟污的臉,但看五能覺出他的容貌不差了,只是防備心極重,仿佛初涉人間的小狼帶著極度的防備打量四周的人。
“問清楚了,這個孩子了他們的包子才會被那群小孩欺負,現在那群小孩已經離開了。”護衛在外回話,才說完,那個小孩便立刻反駁,“我有,我給了東西!”
不知道幾天喝水了,他的聲音沙啞的不行。
可卻還是執拗地握著那個包子反駁道:“我東西,我不會東西的。”
外面的人相顧無言。
王老夫人大約是覺他可憐,不道:“可憐的,玉萊,給他一點吃的和喝的,給點銀子。”
玉萊輕輕應了一聲。
男孩接過吃的和喝的,卻接銀子。
玉萊詫異,蘭因想起他那雙干凈的眼睛和執拗的『』,心中猜測這孩子大概是里出事才會如此,沉默一瞬開口,“拿著吧,不管發生什麼事,活去才是最重的。”
話音剛落,原本埋頭不語的男孩忽然抬頭。
四目相對,蘭因看著這雙眼睛,不知何,一時間竟覺有些悉。但還不等回過來,男孩便又低頭,他接過銀子,嗓音啞地道了一聲謝。
這事對他們而言只是隨手的舉。
等給完,他們便打算繼續離開,可馬車啟程了一會,外面忽然傳來王則的聲音,“祖母,那孩子還跟著我們。”
“難不是訛上我們了?”有丫鬟嘀咕道。
蘭因正反駁,王老夫人卻說,“看著不像。”一般的乞兒絕不會是那副樣子,看了一眼邊的蘭因,握著簾子往外頭看,又想到先前說的那番話,不想起小時候的樣子。略作沉『』后,與外面的王則說,“去問問那個孩子是個什麼況。”
“是。”
馬蹄聲遠去。
蘭因有些驚訝外祖母的舉,正開口,卻聽外祖母笑著與說,“你邊伺候的人不,如果那個孩子問題又愿意的話就讓他跟著你。”
蘭因雖做善事,卻有撿人的習慣。
可或許是那個孩子的那雙眼睛,亦或是他上『』出來的那子覺,像極了小時候初到王時的樣子,戒備、不敢相信人……沉默一瞬,還是點了點頭。
猜你喜歡
-
完結1620 章

神醫娘親她又美又颯
九千歲獨孤鶩因疾被迫娶退婚女鳳白泠,滿朝轟動。 皇子們紛紛前來「恭賀」 : 鳳白泠雖貌丑無能又家道中落,可她不懼你克妻不舉之名,還順帶讓你當了便宜爹, 可喜可賀。 獨孤鶩想想無才無貌無德的某女,冷冷一句:一年之後,必休妻。 一年後,獨孤鶩包下天下最大的酒樓,呼朋喚友,準備和離。 哪知酒樓老闆直接免費三天,說是要歡慶離婚, 正和各路豪強稱兄道弟的第一美女打了個酒嗝:「你們以為我圖他的身子,我是饞他的帝王氣運」 九千歲被休后, 第一月,滿城疫病橫行,醫佛現世,竟是鳳白泠。 第二月, 全國飢荒遍地,首富賑災,又是鳳白泠。 第三月,九朝聯軍圍城,萬獸禦敵,還是鳳白泠。 第某個月,九千歲追妻踏遍九州八荒:祖宗,求入贅。 兩小萌神齊聲:父王,你得排號!
284.6萬字8.18 32482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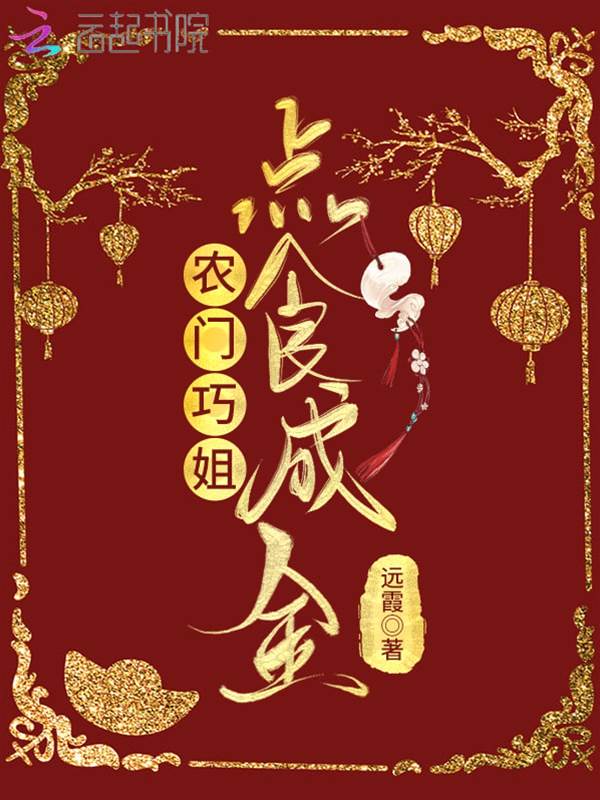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4327 -
完結506 章

爺快跪下,夫人又來退親了
中醫世家的天才女醫生一朝穿越,成了左相府最不受寵的庶女。 她小娘早逝,嫡母苛待,受盡長姐欺負不說,還要和下人丫鬟同吃同住。 路只有一條,晏梨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鬥嫡母踹長姐,只是這個便宜未婚夫卻怎麼甩都甩不掉。 “你不是說我的臉每一處長得都讓你倒胃口?” 某人雲淡風輕,「胃口是會變的」。 “ ”我臉皮比城牆還厚?” 某人面不改色,「其實我說的是我自己,你若不信,不如親自量量? “ ”寧願娶條狗也不娶我?” 某人再也繃不住,將晏梨壓在牆上,湊近她,“當時有眼不識娘子,別記仇了行不行? 晏梨笑著眯眼,一腳踢過去。 抱歉,得罪過她的人,都拿小本記著呢,有仇必報!
90.4萬字8 291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