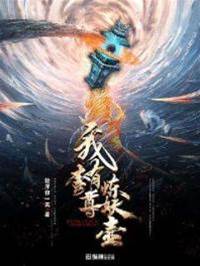《道兄又造孽了》 第1章 熟練的找死技能(1)
元月初的一天,寒風夾帶著雪花呼嘯而過,偌大的天地,被渲染得一片蒼茫蕭瑟。
淩波城裏,穿著破爛的任一,揣著手蜷在一個角落裏,努力把自己團一個球。
無邊的疼痛向他襲來,無力反抗的他,隻能咬牙忍耐。
他的周圍站著五六個大漢,對著他就是劈裏啪啦,稀裏嘩啦一通打,直把他打得鼻涕眼淚橫飛,恨不能立馬投胎去。
“他大爺的,有本事打死我吧,反正賤命一條,拉你們陪葬,不虧!”
“我發誓,你們要是打不死我,我還,到你們破產為止!”
“來呀!繼續呀!”
……
他肆無忌憚地挑釁著,這樣的話說得賊溜,仿佛演練了千百遍,隨口就來。
事實上,他每天都是在挨打和挑釁中度過的,找死技能早就練得爐火純青。
“呸!狗東西,每次都這幾句,說的倒輕巧,爺爺命金貴著呢!打不死你,打殘也行!”
“冥頑不靈的廢,就該廢了,我讓你囂張,讓你狂……”
“讓爺爺教你好好做人,你個孫子!”
……
大漢們越說越起勁,越發賣力的踢打起來。寒冬臘月的,隻見他們的頭上居然升騰起一層白霧,卻是汗水都打出來了。
任一就像一坨死一樣,待對方夠了後,被棄在牆腳旮旯裏。
隨著時辰的流逝,天空飄起了茫茫白雪,四野再無行人,世間沒人去關心那積雪之下,覆蓋了什麽。
天地間,是那樣的白淨亮,看不到一汙垢的存在。
一直到更夫的梆子聲響起,任一才終於睜開了被冰雪糊住的眼睛,甩甩有些發昏的頭,他茫然的看了下周圍,一陣冷風吹過,忍不住打了個寒。
此時已然是半夜三更,自己有些腫脹的,他歎了口氣,“都這樣了,還是死不掉啊,賊老天真是瞎了眼。”
他哆哆嗦嗦的掏出袖子裏的一坨生,因為天冷,早就凍得有些僵了,看著一點食都沒有。
但是,腸轆轆的他還是毫不猶豫的塞進裏大嚼特嚼。
這是他費盡千辛萬苦,才從那個豬攤上盜來的。流浪的生活,讓他早就習慣了吃生食。
想起年的時候,他曾經也是來手飯來張口的大爺,何曾飽過這樣的人世辛酸?他不由得唏噓不已。
那還是他剛滿月的一天,有個遊方的道士突然上門討酒水喝,看了他的麵相後,酒盞碎裂,一屁坐到地上,驚慌失的大道:“掃把星,居然是掃把星出世!丟掉,快把他丟掉!”
他的樣子是那樣的張惶,把任一的家人嚇到了。
不過,任一畢竟是個男丁,是家族裏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年輕的父母有些舍不得,選擇瞞道人的占卜之言,把他將養在邊。
這之後,果然有異事頻繁發生,先是家族的生意慢慢萎,生活維艱起來。再然後,原本人丁興旺的大家族也變得子嗣艱難,沒有後繼之人。
等他勉強長到七歲的時候,短短三個月,家中德高重的長輩,莫名其妙的相續離世。
他是掃把星的傳言再也捂不住,所有一切的罪過,都被拉出來,強行套在他頭上,剝奪姓名後就被掃地出門。
年的他一下子從天堂來到地獄,飽人間滄桑。
好不容易艱難的熬到十八歲,恰逢神靈宗開山收徒,他一路乞討而去,了三天三夜,測試的結果是,他是個絕靈之,這輩子沒有修行的資格。
生而無,不如歸去!
絕的他,選擇了很多種死法:
上吊?繩子似乎承不起他,快落氣的時候總有意外發生,要麽房梁斷了,要麽樹杈斷了,要麽繩子斷了。
總之,什麽都斷了,就是人斷不了氣就對了。
溺水?他的花樣狗刨還可以,出於本能總要撲騰兩下,想要被嗆死,沒有外力幫助的話真的很難。
毒藥?那不是他一個乞丐能接到的東西,被家死死地管控著。就算他再饞也隻能幹瞪眼,誰讓他寒酸得,連藥鋪大門都進不去。
火燒?他窮得連打火石都有不起,渾上下拿去當了,也不值一文錢。
死?他換了很多荒涼沒人煙的地方,靜靜的等死,卻總有食因為各種原因送上門。
有過路的客商,富態的達貴人,善良麗的千金小姐,總能在崎角旮旯裏和他來個不期待的偶遇。
吃還是不吃,這樣的折磨太煎熬,他咬咬牙選擇了大快朵頤。
……
如是多次,就差千刀萬剮,五馬分的殘暴死法,他不敢去嚐試,別的都已經不抱希,就這麽茍且生活著吧!
飽腹的覺,讓他欣的歎了一口濁氣,慢吞吞的挪著,準備找個暖和的地方貓一晚上。
“別跑!給我站住!”
寂靜的夜裏,一聲怒吼驚到了他。
打眼看去,卻是一群黑人追著一個苗條的人影向著他趕過來。對方手裏都有明晃晃的武,一看就不是善茬。
“嘶~~~我的娘哎~~~”
他倒一口涼氣,一瘸一拐的朝前跑去。
奈何殘軀拖累,很快就被苗條人影追上來,順手拉扯過他,把他當個破沙包一樣的拋向黑人。
“啊~~啊啊啊~~救命啊!”
快速的行嚇壞了他,忍不住發出了驚天地的鬼聲。
苗條人影的手還不錯,任一就這麽直的撞到了兩個黑人上。
他雖然不胖,但架不住材高大,兩個黑人很倒黴的,一個被他的頭撞倒,鼻狂飆,一個被他屁撞倒,牙齒磕飛了兩顆。
兩人還沒來得及發飆,就見自己的肚腹齊刷刷的冒出一把刀鋒,僵愣了一息後,立時斃命當場。
卻是他們在停頓的那一霎那,後麵趕上來的人反應不及時,刀子就這麽直接捅進兩個人的。
“嘿喲,他大爺的!”
意識到自己攤上大事了,任一折就想跑。
他是不想活了,但是對這種淋淋的死法敬謝不敏。
黑人剩餘的兩個同夥,把怒火轉移到他上,惡狠狠地怒斥道:“混蛋!去死吧!”
即使天黑,對方手裏明晃晃的大刀在雪地的反下,刺得任一瞇上了眼,心裏直哀嚎,“吾命休矣!”
卻是在這電火石的一剎那,“嗖、嗖……”聲不絕於耳,卻是沉悶的破空聲連續傳來。
隻聽得“噗嗤”兩聲,兩把大刀相續落地,斜在雪地裏,隨即傳來黑人的怒吼聲,“誰?誰幹的?”
“我!”
路邊的黑影裏走出一個麵帶薄紗的人影,卻是剛才跑遠的苗條人影,不知何時又潛伏了回來。
聲音清脆悅耳,猶如黃鶯啼鳴,卻是個妙齡的覺。
猜你喜歡
-
完結641 章

快穿之女主是個小呆寶
男人捧著她的臉:“你是我的小媳婦,隻可以我親你,記住了嗎?” 阿禪軟萌萌歪頭,小媳婦兒? “哦。”阿禪呆呆點頭,識海裡問統統,小媳婦兒是什麼意思捏? 殊不見,男人眸光微黯,俯首湊近… 係統驟然炸起:呆寶!不可以!狗男人想占你便宜,打死他……次奧,居然把它遮蔽了!! 狗男人,欺負一個智商低的小呆子,簡直喪心病狂! -- 瑤光仙君養了三千年才堪堪開智的小花骨朵,有點呆。 一朝被送進三千小世界,仙君隻有一句交代——護她活到最後。 係統:誓死完成任務! 嗬護她,保佑她,不求她聰明絕頂,但求她長命百歲,想做啥都滿足她。 哪怕她要去找仙君之外的男人… 仙君:……嗬嗬!
58.2萬字8 13096 -
完結18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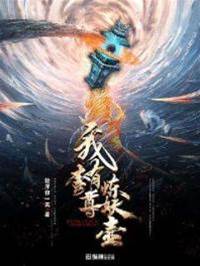
我有一尊煉妖壺
天地為爐,陰陽為碳。 一個破夜壺,誰能想到,竟是傳說中的上古神器「煉妖壺! 剛剛穿越異世,還沒吃上一口香噴噴的軟飯,宅男韓風就不得不手掌煉妖壺,醉臥美人膝,開啟自己寂寞如雪的新人生……
401萬字8 49157 -
完結375 章

女兒大鬧修仙界,我仙帝身份曝光
【無敵 女兒 女帝 爽文】陸銘穿越到修仙界,因無法修煉就跟青梅竹馬結婚,選擇做一個普通人。然,青梅竹馬為他生下一個女兒後。對方突然說自己是仙帝轉世,有太多因果需要解決,飄然離去。在老婆離開後,沒想到簽到係統突然激活。依靠簽到獎勵,在短短六年的時間陸銘修為就提升到仙帝境。小棉襖也在他恐怖資源的培養下也成為恐怖存在。某天,陸銘在衝擊真神境時,小棉襖卻跑出了村子。從此修仙界炸了……聖地聖主:兇殘,太特麽兇殘了,這是誰家的熊孩子,把我聖地當菜園?妖族妖帝:哪來的熊孩子啊,追著我要獸奶喝?有沒有人管管啊!!!禁區之主:啊,該死的小崽子,老夫守了十萬年的先天白蓮,你拿去當燉肉配料?直到某天,小棉襖遇到打不過的存在,當即大喊一聲:“爹爹,女兒扛不住了。”陸銘當場出關:“誰特麽敢動我小棉襖?”修仙界再次炸鍋,我你那個杯的仙……仙帝大佬!??……境界:妖獸/練氣境、玄妖/築基境、 地妖/金丹境、天妖/元嬰境 、妖皇/化神境、妖尊/合體境、妖聖/大乘境 、妖帝/至聖境、妖祖/帝尊境、偽仙獸/劫境...
65.8萬字8.18 93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