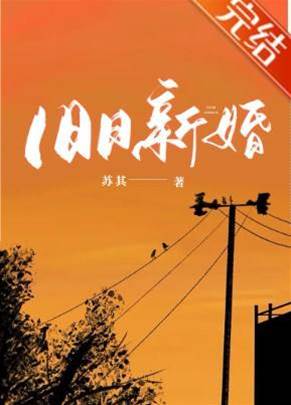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想把你和時間藏起來》 11、第十一幕
第十一章
沈千盞的腦回路簡單又暴。
季清和重復過兩遍“希沈制片日后沒有需要求上門的時候”,這話第一次說的時候,沈千盞姑且當他是男人自尊心作祟,為了挽回面放得狠話。
老實說,第一次聽的時候,的確沒當一回事。
畢竟上到資方爸爸,下到藝人經紀,平均每月都會如期發生一次,風雨無阻,從不缺席。
投資方有為了堅持藝審的,有為了后宮佳麗的,還有為了滿足自己掌控的,理由千奇百怪,應有盡有。
通常放完狠話最常見的作就是撤資。
沈千盞也很干脆,違反合同的,告;塞了后宮的,踢;想掌控劇組架空的,干。
對待金主爸爸尚還游刃有余,藝人經紀就更別提了。
前兩天剛放完狠話,雙方都默契地決定老死不相往來了。過兩天,等沈千盞畫完餅,對方跟失憶了一樣,地帶著藝人履歷又來了。
能怎麼辦呢,只能假裝重歸于好,繼續拉黑啊。
季清和的況與上面兩例稍有不同,他第二次提起這句話時,沈千盞認真了。
這狗男人,皮相好,功夫深,行力也非一般的果決。
一句話能讓他重復兩遍,顯然是魘了。這可能跟氣多深人有多爽一個道理?
沈千盞琢磨著,季清和八是記了“嫖資”梗的仇,又篤定符合要求的鐘表修復師除他以外再沒合適人選,無論怎麼翻筋斗云始終翻不出他掌心的兩座大山。
季清和猜得沒錯。
投資方可以再找,符合條件的鐘表修復師眼下的確只有他一人。
可真讓放下段去求季清和,做不到。
人該的地方從來不是尊嚴和底線。
這也是為何這麼抵和季清和合作的原因之一,鬼知道真合作了,會不會又鬼迷心竅饞他子。
而且朝夕對著個有過水緣的男人假裝無事,還要對對方的視若無睹,做坐懷不盞上惠……要不是迫于前勢無可心的人選,看沈千盞做不做這麼虧本的生意。
——
季清和抬眸,目略帶審視地落在沈千盞的臉上。
從他認識沈千盞的那天起,這個人就像時刻保持致的花瓶,二十四小時都在維持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的觀賞。
今天顯然更甚。
季清和從深邃大地落日余暉的眼妝往下,留意到特意顯擺的新指甲,最后停留在的上。
微笑著,三分挑釁,七分看戲。
明顯,是來砸場鬧事的。
他一哂,眸深深地看了一眼,不置可否地拿起了那塊兒手表。
手表表盤是銀邊圓形的普通材質,框底印著米妮,兩指針一長一短全停留在了十二點。
季清和翻轉手表,打量了眼底蓋:“難為你去找這麼有年代的手表了。”他問:“二十年前的?”
沈千盞點了點下,“上一年級,我媽給我的禮。”
季清和了然,他拉過一張皮革墊,隨手一裹,直接扔進工作臺的柜子里,表冷漠,聲音冷淡:“修不了,你隨便去孟忘舟那重新拿一塊。”
他笑,一字一句擲地有聲:“我賠你。”
沈千盞:“……”這他媽是個狠人啊,還帶這麼耍賴的?
正爭辯,只聽他“噓”了聲,神不耐,擺明了一副“你再胡鬧我就收拾你了”的妖孽表。
沈千盞安靜了片刻。
拿修表惡心季清和的計劃……稚得像是蘇暫這種兒園級別的對手出的餿主意。
突覺荊州已失,戰事已敗,本不是季清和的對手。
季清和解開袖扣,漫不經心問:“今天是修表,明天呢,修鐘?”
“或者你什麼計劃都沒有,走一步看一步,只要能針對我就行?”他挽好袖子,鼻梁上的金框眼鏡在窗外的余暉下閃過幾縷冷厲的暗。
他神倦懶地推開鏡框,了鼻梁,眼眸微閉:“我看過沈制片的履歷,本以為沈制片的商業手腕頗雷霆,現在看來……”他睜眼,似笑非笑:“不過爾爾。”
“還行吧。”沈千盞跟沒聽見他后半句話一樣,沉著淡定:“這不是沒想到季總這麼狗?”
兜里手機輕震。
沈千盞猜是蘇暫坐不住了,來問況,邊看微信邊隨口問季清和:“吃飯嗎?今晚我請。”
季清和拒絕之前,施施然,又補充一句:“不是好奇我有什麼商業手腕嗎,給個機會?”
——
前宴。
一家做滿漢全席出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京幫菜。
沈千盞上午十點電話預約,下午才排上包廂。
座后,蘇暫包攬點菜,沈千盞負責酒水。等開胃涼菜一盤盤端上來后,十分有儀式的沈制片這才正式開場,為季清和介紹向淺淺。
季清和沒剛斟的酒,轉而端起清茶,潤了潤嗓子。自然,也無視了向淺淺剛舉起酒杯試圖敬酒的行為。
他喝完茶,瞥了眼沈千盞,一句話意味不明夾槍帶棒:“商業手腕?是商業的。”
向淺淺尷尬。
轉頭看了眼蘇暫,見后者神自若,見怪不怪,這才稍被安。
蘇暫,習慣季總和他盞姐這互懟模式的相。
畢竟這兩人在大佬面前都不帶收斂的,他們只是一群蘿卜,更無足輕重了。
沈千盞笑笑,沒直接正面鋒:“季總前兩天不是說,剛在北京定居嗎,我這也是好心啊。北京這麼大,來往都需人……”
季清和打斷:“不終歲的頂級客戶有千上萬。”
沈千盞微笑。
狗男人,一句不懟就不舒坦是吧?
一手提刀,一手拿酒,直接敬孟忘舟:“孟老板這些年不容易的吧?”
突然被cue的孟忘舟放下在微信群的八卦直播,端起酒杯回敬了一淺杯:“清和可能和沈制片平時打道的生意人不太一樣,他醉心鐘表修復,有些迂腐。人雖腹黑,但不怎麼記仇……”
孟忘舟越說越覺得自己在偏離本意,他立刻咬舌止損,生地強行圓了一波:“等認識久了,沈制片自然知道。”
迂腐?
恐怕不見得。
瞧季清和新的,總不能是無師自通吧。
沈千盞嘖了聲,拉回思緒。
目前連編劇班子都還沒拉起來,項目籌備狀態除了百分之一的劇本創意,一切都還沒開始。
孟忘舟那番話給提了醒,和季清和這麼杠著不止沒用,可能還會適得其反。
這是睡了一覺,連商都睡沒了。以前哄金主爸爸的手段一個都沒往外掏,就想摁頭季清和合作,憑啥啊?
沈千盞轉過彎來,計從心起。
起,端起酒杯,大丈夫能屈能,給季清和賠了杯酒:“季總別跟我一般計較,我今天請這頓飯,一是為了忘舟兄弟昨晚的款待,二是想給季總道個歉。”
再斟一杯,手都不見抖一下,穩如老狗:“怪我仗著季總和我的幾分……,言語間多有冒犯。”
沈千盞仰頭,面不改地一杯喝盡。
眼里有水,角酒漬晶瑩,瞧著已經有幾分醉態了。
滿屋寂靜,誰也不敢出聲。
蘇暫更是目瞪口呆,這是哪一出?出發之前不是還一口一句狗男人,甚至大放虎狼之詞,說不想被季清和頂撞,只想頂撞季清和的嗎?
這他娘的,現實魔幻啊。
沈千盞斟上第三杯酒時,季清和的表終于變了變。
他眼神依舊冷靜,只有眼底涌進燈時,才能看清那偶然迸現的一清明和克制。
他微微抿,似想看還能再說些什麼,漫不經心里還有幾分隨心所。
沈千盞在自己的中華文庫里挖了挖,說:“季總喜靜,我數次打擾,行為不端,多有抱歉。”酒杯到,見季清和似坐直了些,又補充了句:“罰完三杯,一笑泯恩仇?”
不等季清和回答。
揚手舉杯,剛啟,還未嗅到酒香,被一只修長的手扣住手腕,沒用多大勁就牢牢地桎梏住。
季清和聲音低沉,語氣無奈:“沈千盞,在我這不興灌人喝酒,議論對錯。”
沈千盞空腹喝了兩杯,面上微醺:“那我白喝了?”
問得直接,言辭間還有幾分錯愕,這下意識的反應意外地比世故清醒時的沈千盞招人多了。
季清和勾了勾,說:“對,白喝了。”
沈千盞:“……”
靠,取悅季清和簡直比睡服他還難。
猜你喜歡
-
連載1471 章
盛少,情深不晚
年輕幼稚的周沫被爸爸算計,稀裡糊塗睡了高冷男神盛南平,陰差陽錯生了兒子。 盛南平恨透周沫 三年後,為了救兒子,他必須和周沫再生一個孩子。 周沫是有些怕盛南平的,婚後,她發現盛南平更可怕。 “你,你要乾什麼?” “乾該乾的事兒,當年你費儘心機爬上我的床,為的不就是今天?” “……” 傳聞,京都財神爺盛南平是禁慾係男神,周沫表示,騙人滴! 終於熬到協議到期,周沫爆發:“我要離婚!我要翻身!” 但盛南平是什麼人,他能把你寵上天,也能殺你不眨眼......
357.7萬字8 15339 -
完結1203 章

五年後,龍鳳雙寶攜她炸了大佬集團
夏梵音被繼妹陷害懷孕,被迫假死逃出國。 五年後,她帶著萌寶們回國複仇,竟意外收穫了個模範老公。 安城裡的人都知道紀三爺性情殘暴冷血,可卻日日苦纏全城知名的“狐貍精”。 夏梵音掙紮:“三爺,麻煩你自重!” 紀爵寒抱起龍鳳胎:“孩子都生了,你說什麼自重?”
214萬字8.18 85495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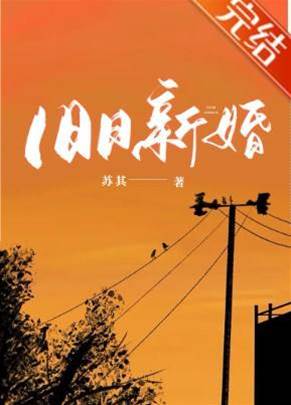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037 -
連載959 章

賀總夫人又來蹭氣運了
姜糖天生缺錢命,被師父哄下山找有緣人。 本以為是個騙局,沒想到一下山就遇到了個金大腿,站他旁邊功德就蹭蹭漲,拉一下手功德翻倍,能花的錢也越來越多,姜糖立馬決定,賴上他不走了! 眾人發現,冷漠無情的賀三爺身邊忽然出現了一個軟乎乎的小姑娘,會算命畫符看風水,最重要的是,總是對賀三爺動手動腳,誰不知道賀三爺不近女色啊,正當眾人等著她手被折斷的時候,卻見賀三爺溫柔地牽住她的手。 “嫁給我,讓你蹭一輩子氣運。”
174.2萬字8.18 12742 -
連載295 章

避孕失敗!沈小姐帶崽獨美,厲總慌了
十年深愛,四年婚姻,沈瀟瀟畫地為牢,將自己困死其中,哪怕他恨她,她也甘之如飴。直到一場綁架案中,他在白月光和懷孕的她之間選擇放棄她,間接害得父親離世。她終於心死,起訴離婚,遠走國外。三年後再見,她攜夫帶子歸國。厲行淵將她困在身下,“沈瀟瀟,誰準你嫁給別人的?”沈瀟瀟嬌笑,“厲先生,一個合格的前夫應該像死了一樣,嗯?”男人眼眶猩紅,嗓音顫抖,“瀟瀟,我錯了,求你,你再看看我……”
50.1萬字8.18 492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