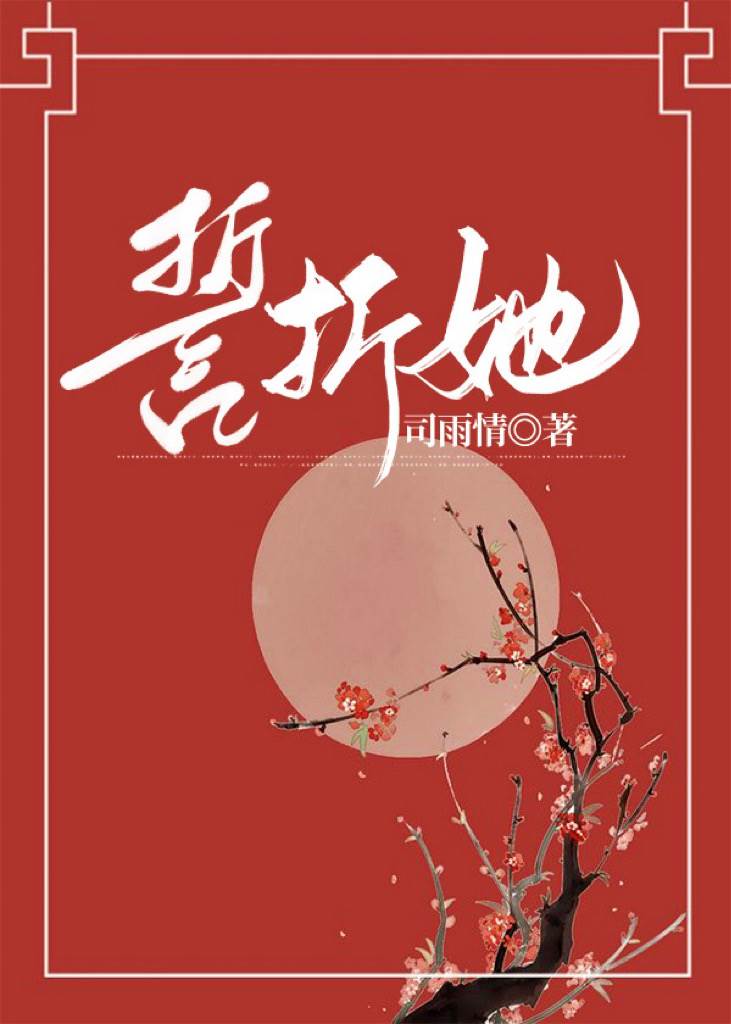《長寧將軍》 第 24 章 第 24 章
王府的門房知攝政王今夜將會宿在宮中,天黑,等到王妃歸來,府里的知事和侍衛等人也全部歸了位,便閉了大門。不料晚些,有人叩門,本以為是什麼不上道的訪客,這幾日,他這里,就拒了不知多的投來的想拜將軍王妃的帖子,出去一看,竟是攝政王的馬車停在門外。他從宮中回府了。
門房趕忙開門迎人。
“王妃回了嗎?”束慎徽一進門開口便問。
“稟殿下,回了,回了有一會兒了。”
束慎徽便徑直去往繁祉堂。
這個時間還不算很晚,戌時兩刻鐘的樣子,姜含元還沒睡。晚間回了房后,先是整理這些日收來的要替士兵們捎回去的行李,多為冬和鞋,整理完畢,還不想睡覺,又去這院中的書房,取了筆墨紙硯,再挑字帖,想在睡前臨上幾頁。
雖然從小在軍營生活,但早年,姜祖其實一直還抱著兒長大后能回歸的念頭,所以,并沒有因在軍營而放任不管。除了安排最好的弓馬師傅教自己學的武功,經書也沒丟下,姜祖讓邊有個出于五經博士的長史去教。天資聰慧,繼承了姜祖的軍事天分,學武學兵法極有靈氣,能舉一反三,但的字,實話說,從小到大,一直寫得不怎麼樣。
這是需要花費時間去換取的。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興趣可以分給自己去練字,所以多年來,也就是陸陸續續在軍中的閑暇空檔里想起來去劃拉幾下而已。早年也無所謂,但最近幾年,隨著在軍中職位的不斷提升,經手的文書越來越多,那永不服輸的好勝之心也開始促使重視起了自己的字。奈何職位提升便意味著軍務繁忙,更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留給練了。正好現在,吃飽了沒事干,做這個最好不過。
的字寫得不怎樣,但鑒賞力還是有幾分的,那曾教讀書的長史便是個書法好手,把教出來后,就了俗稱的眼高手低。
這個用作新房的繁祉院,都著一子新開墾的味道,書房也是如此。一看就是新置出來的,書也都很新,但種類倒算齊全,也有想要的帖。
看中了一幅碑帖,容看著像是為一位德高重的去世的員作的墓志銘,沒有署名,不知何來,但字是鐵畫銀鉤,筆勢飄逸,越看越是喜歡,于是取了,帶回到寢堂,將案上的燭臺燃得亮的,專心致志臨帖。許久沒握筆了,手凝,握這三寸筆桿,竟比握刀不知要艱難了多。慢慢寫了兩頁,好容易剛有點進狀態,自覺出來的字也仿得不錯了,頗為滿意,正欣賞著,忽然聽到有人在外叩門。
以為是侍要來問宵夜,喊:“不,不必替我準備宵夜——”
叩門聲停了,但很快,又響了起來。
“是我。”一道男子的聲音傳耳中。
姜含元停住,扭臉向門的方向,頗覺掃興,片刻前的心全都沒了。
是他?
他怎麼突然回來了?不是說明早大朝議,今夜要在皇宮過夜嗎?
只好起,看了眼桌案,又回來,飛快地先收了字帖等,拿冊別的書給擋了,這才過去開門。
束慎徽了房,關門,慢慢地轉過了。
姜含元也沒問他怎突然回了,只點了點頭,說了句我去睡了,便要朝那人榻走去,卻聽他住了自己:“姜氏!”
姜含元停了下來,過去。
他朝走了幾步過來,卻又仿佛猶疑了下,停住了。
“適才我進來,聽張寶說,今日你的信全都送完了?”他道,是搭訕的語氣。
姜含元嗯了聲。
“實在是辛苦你了。青木營里的兵卒,想必對你十分擁戴。”
“殿下若是有話,直說便是。”
用不著顧左右而言他,給送戴高帽。
他微微咳了一聲,“是這樣的……再過些天,便是賢王老王妃的壽日,到時候,賢王府會替老王妃辦個壽宴,以表慶賀。我知你不喜應酬,別的關系不去也罷,但賢王是皇伯父,老王妃也一向親厚,所以到時候你若能去,最好去一趟。”
“明白了。”姜含元答,“到時候我會去。”
他朝出笑容:“多謝諒。”
姜含元頷首,轉要去。
“姜氏!”他又住了。
他終于好似下了決心,“你知溫節溫家嗎?”他問。
姜含元看著他,沒有應答,既不點頭,也不搖頭。
他自己繼續說道,“溫節是我從前的太傅。他有一,名溫婠。今日的兄長尋到了我的面前,溫家遇到些麻煩,希我能予以幫。”
“溫家兒婚事阻,是不是?”姜含元直接說了出來。
他一怔,“你都知道了?”
“張寶之言。”
他點了點頭,“是。我因太傅之故,和溫家確實有些淵源,年時,有過頗多往來。如今太傅雖已去了,但此事既求到了我的面前,于于理,我都不能坐視不理。今晚回來,便想先將此事告知于你。”
他頓了一頓,觀察著的神,語氣放緩,似在斟酌著言辭。
“……我知外頭至今仍有關于我和溫家兒的傳言,你或也有所耳聞,實際皆為夸大之詞,你勿信。既娶了你,你便為我妻。此次我相幫,雖是出于私心,但絕非出于異心,更非對你不敬,你莫要誤會……”
姜含元打斷了他。
“我有何誤會?溫家人既求到了你的面前,那便是走投無路了,你保護,是理所當然!這你若都不管,你算什麼人!在我這里解釋什麼?還不快去!溫家孩已夠不容易了,難道是要等再出大事,那樣的一個子被徹底毀掉一生?”
束慎徽大約沒想到會是如此的反應,起先略略訝異,很快,他看了出來,這話絕非矯詞。
對溫家兒非但毫無芥,言下似還頗多回護好。
束慎徽雖不明所以,但這一刻,他如釋重負,點頭:“多謝你理解,如此我便去了。”
他轉,匆匆要走。姜含元目送著他的背影,忽然住了他,“等一下。”
束慎徽轉頭。
“殿下你打算如何幫?”
“溫家與我非親,涉及婚姻之事,實話說,我也不便直接手。不過,我知大長公主那兒子過去犯了不事。去年在先帝國喪期間,便就私闖皇林行獵,當時有史參奏,可大可小,我不多事,便了下去。這就去人把舊事翻出來追究治罪,大長公主自然也就有數了。”
姜含元道:“這個法子是不錯,不過,我也有個想法,可供殿下參考。”
“你說。”
“殿下可否想過以為側妃?如此,往后再無麻煩。你放心,我此言絕非試探,而是真心實意。溫家兒若來,我絕不計較。”
束慎徽一怔,看了一眼,斷然搖頭,“我無此意。此路也非最好歸宿!”
當放便放,何況早就時過境遷,如今他又豈會為了彌補便無事生非做出這等蠢事?便是當真如所言,不計較,落外人眼中,和辱新婦有何區別?
他說完,見瞧著自己,神間似見同,忍不住皺眉:“姜氏,你如此看我作甚?莫非你是不信?”
姜含元收了目,繼續道,“那我還有另外一策。賢王王妃應當不懼大長公主。何不請王妃認溫家兒做個干,如此,王妃主婚,理所當然,大長公主自然也就知難而退了。不但如此,溫家兒有了這層份,往后便也如有了護符,在這京中再不至于如同棄子,人輕視,忍氣吞聲。”
束慎徽聽完這話,一時定住了。
實話說,年之時,他確曾對溫家兒懷有好。那樣一個宛如花的溫子,誰會不喜。然而,人若一旦將國認作是家,肩擔江山,便就別無選擇,必然是要拋棄與之相悖的一切私。他知溫家或一直是將兒寄希在他上的,怕誤了對方,便借那年探病之機,委婉私言太傅,將來婠娘若是大喜,他必以兄長之禮嫁之。自那之后,于他,溫家人是徹底淡出了他的世界,但他沒有想到,婠娘卻依然一直誤了下去。
那日在護國寺,時隔多年之后,他和時玩伴的那一番坦誠對話,固然是出于疚而攬責安,為保全誤蹉跎了年華的面,然而,也何嘗不是他對自己年時的一切自由和率的徹底埋葬。
以婚姻為易,來換取軍隊的絕對支持,固然可鄙,但他不會后悔。像他這樣出又自己選擇了國的人,必要之時,便是他的命,也可拿出來作為秤砣,何況區區婚姻之事。
但是這刻,當他聽到他因這婚姻得來的妻,姜家的將軍,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他的心下,還是慢慢地生出了些驚詫和,甚至,還有些微的激。
巧的很,其實他原本想到的第一個法子,恰就如所言。不管他是否曾經有所提醒,但確實是因自己而誤的,這一點他無可推責。如此的安排,也算是對溫家的一點彌補。不過,這個念頭很快就被他否決了。
他實是有些顧忌,擔心若是過于抬舉了溫婠,會惹姜不快,所以退而求其次,另想了個方法。
他實是沒有想到,會和自己想到了一去,如此肯為溫家兒著想。
他注目了片刻,一言不發。
姜含元見他看著不說話,神略顯古怪,道:“你看我做甚?這法子你若覺妥,便去辦。”
束慎徽陡然回了神,轉頭,開門匆匆而去。
姜含元著他去了的背影,在原地立著,漸漸愣怔,忽然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又搖了搖頭,仿佛搖去一切擾的雜念,撿回了剛才那被打斷的心,回到案后再次坐下,取出剛才藏起來的紙和筆,繼續刻苦臨起的帖。
剛寫了兩個字,突然,伴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還沒來得及反應,就見門被推開,束慎徽一腳了進來,左右一看,瞧見了,轉快步向走來。
姜含元嚇了一跳,可不愿讓他看見自己的字,一把將紙給住,站了起來。
“你怎又回來了?作甚?”
不大高興的樣子。
他的視線掠了一眼案上的東西,隨即向,“無事,就是想起來,方才我還未曾向你言謝。”
“姜氏,多謝你了!”
他鄭重地道了一句,眼角風又瞄了眼桌上的紙筆,丟下去了。
姜含元心還在撲騰撲騰跳,盯著他出去,卻見他走到門口,仿佛又想起什麼,回頭看了自己一眼,再次回來。
“殿下你還有事?”姜含元擔心自己的字,真的有點不耐煩了。
“姜氏,”他了眼人榻,用商量的語氣道,“要不,還是你睡里頭去?我堂堂一男子,豈能讓你睡在外,傳出去了,別人如何看我?或者,我若是不在,你一個人睡進去,豈不也是一樣……”
他說著說著,見始終不予反應,只用含了不屑似的目盯著自己,打住了。
“罷了罷了,我也就一說,隨你意吧!我走了!”
他拂了拂手,略帶了幾分悻悻然,轉去了。
姜含元跟到門外,看著他的影消失在了院門外,這回是真的去了,關門,順便上了門閂。
猜你喜歡
-
完結282 章
傲嬌醫妃
她是醫學界的天才,異世重生。兇險萬分的神秘空間,低調纔是王道,她選擇扮豬吃老虎翻身逆襲。他評價她:“你看起來人畜無害,實則骨子裡盡是毀滅因子!”她無辜地眨著澄澈流光的眸子,“謝王爺誇獎,只是小女子我素來安分守己,王爺可莫要聽信了讒言毀妾身清譽!”錯惹未婚夫,情招多情王爺,闊氣太子與帥氣將軍黏上來……美男雲集,
74.4萬字8 78133 -
完結539 章

世子爺他不可能懼內
顧淮之救駕遇刺,死裡脫險後染上惡疾。夢中有女子的嗓音怯怯喚著淮郎。此等魔怔之事愈發頻繁。 顧淮之的臉也一天比一天黑。 直到花朝節上,阮家姑娘不慎將墨汁灑在他的外袍上,闖禍後小臉煞白,戰戰兢兢:“請世子安。” 嬌柔的嗓音,與夢境如出一轍。 他神色一怔,夜夜聲音帶來的煩躁在此刻終於找到突破口,他捏起女子白如玉的下巴,冷淡一笑:“阮姑娘?” ……
89.2萬字8.18 15272 -
完結105 章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幾年,與哥哥走散,被賣進定國公府給詹五爺做妾。詹司柏詹五爺只有一妻,伉儷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無子嗣,只能讓俞姝這個盲妾生子。他極為嚴厲,令俞姝謹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連每晚事后,都讓俞姝當即離去,不可停留。這樣也沒什…
49.6萬字8 28752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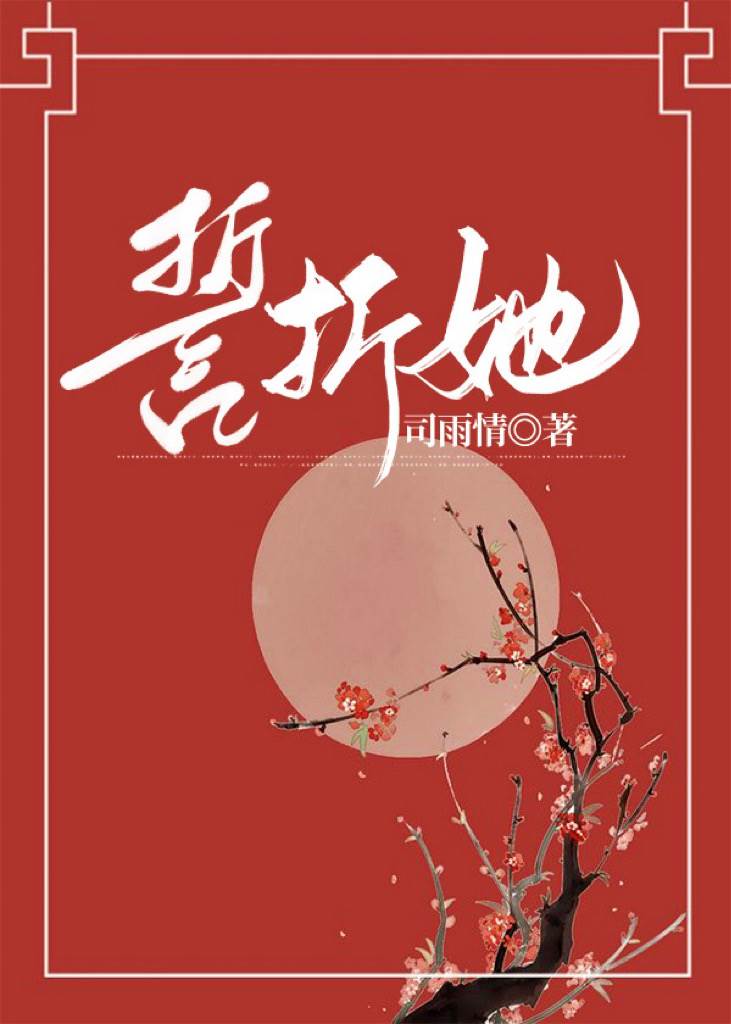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460 -
完結587 章

戰神重生,王妃帶著醫術炸翻王府
堂堂大夏國掌政帝姬,重生到相府不受寵的嫡長女身上。被逼著嫁給一個瘸腿不受寵的王爺,想要不動聲色除了她?姐姐一門心思的想要弄死她?很好,她難不成是小白兔,任由這群人欺負嗎?想要弄死她,那也得看看有多大的本事。本想逃離王府,計劃復仇,卻沒想到,被那瘸了雙腿的夫君抱起,苦苦追求,愛她入骨。她要報仇,他為妻善后。她要殺人,他為妻磨刀。她要打胎,他雙眼含淚,跪在地上祈求不要!
103.1萬字8 34595 -
完結339 章

王爺每日一問,小妾今天宅鬥了嗎(九重錦)
宅鬥,非雙潔被壓製了十幾年的庶女,一朝被重新安排了命運,入了王府,助長了她的野心。生父的漠視,任由嫡母欺淩她們母女半生,從不庇護半分。嫡姐以為,她是個空有美貌的草包美人,想利用她的美色為自己固寵。卻不曾想,她脫離了所有人的掌控。為了往上爬,她也用盡手段,沉浮在虛虛實實的感情裏,直到她徹底認清現實,這一切的人和事都在教她如何做一個立於不敗之地的女人。
60.8萬字8 218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