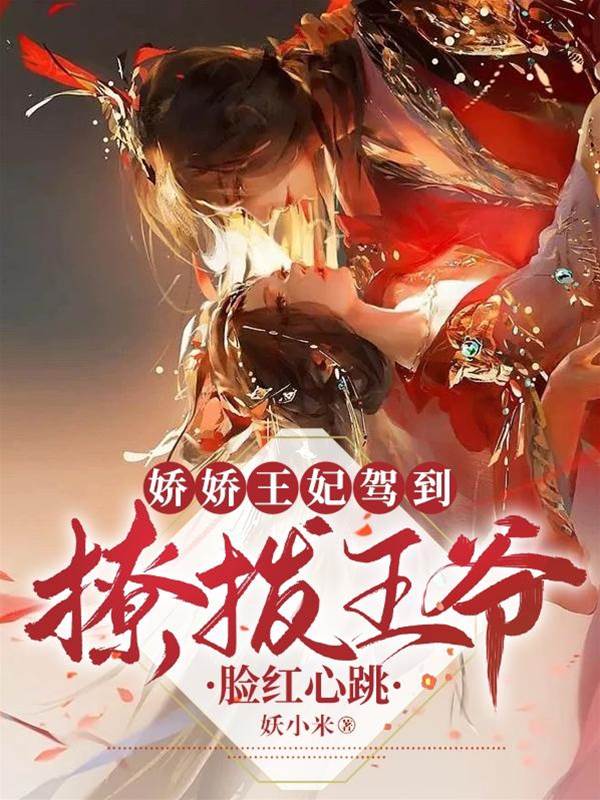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賣油娘與豆腐郎》 第 130 章 光陰轉動如參商
日月窗間過馬,一眨眼,四年過去了。
十四歲的慧哥兒即將要參加科舉考試,本來,前兩年他就想去試一試,但明盛一直著他。
按照明盛的說法,一年過縣試,再一年過府試,再熬兩年過院試,熬得人心頭發焦。
況且,年紀小必定閱曆差,去考試就算勉強過了,怕是名次也不太好。
最重要的一點明盛沒說出來,兄長一直做著縣丞,若是外甥的縣試名次吊著尾,說不得外頭就有閑言碎語,說這縣試不幹淨。讀書人民聲最要的,要是沾上了這些閑言碎語,一輩子都被人詬病。
索不如多讀兩年,人更沉穩一些,曆練也多,做的文章也更紮實,去考試不說名次好一些,就算考不上,心裏也能得住。
多年英才,早早名,後來一蹶不振,不外乎還是年紀太小,習慣了風頭無兩,乍然挫,要麽知恥而後勇,要麽從此泯滅於眾人矣。
今年,縣裏麵又有縣試,明盛覺得外甥被自己打磨的差不多了,可以下場一試。
梅香已經三十一歲了,比前兩年略微胖了一點點。但這胖並不是膩的那種,而是勻稱有度,平添了幾分中年婦人的風韻。
這幾年的安然生活,讓梅香的氣韻也越發從容平和。整日臉上帶著笑,仿佛世間再沒有什麽讓為難的事。
也確實如此,外麵的事有黃茂林心,家裏有一群下人,隻需皮子就好。慧哥兒和青蓮整日出去讀書,泰和也不在像小時候那般調皮。去年,黃茂林也把他送到學堂去了,梅香的日子越發清靜安然。
這幾年間,黃茂林卻一直忙碌著。
縣城裏的產業他一直抓在自己手裏,糧店在全城的份額越來越大,到了去年,他和明朗一人一年分了有上千兩銀子。
家裏有錢,黃茂林就喜歡置辦家業。前兩年,他自己單獨看上了個田莊,把家裏的銀子幾乎掏空了,吃下了約三百畝地。
家裏有了近五百畝地,總算有了可以傳承給孩子們的基業。
至於水玉坊那邊,仍舊占著全城最大的份額。黃茂林已經不大管水玉坊的事,他隻偶爾去看一看,小事都給了小柱打理。
是的,現在小柱是水玉坊的大掌櫃。
前兩年大福的合同期限滿了,黃茂林看得出他想單幹,也沒留他,給了些盤纏打發他回家去了。
但黃炎夏年紀大了,管不了太多瑣碎的事,黃茂林親自去請了小柱過來。
當時,小柱在家裏開了個小小的作坊,帶著妻兒過著熱乎的小日子。師傅來訪,他喜從天降。
小柱先抱著黃茂林痛哭了一場,又準備了好酒好菜招待黃茂林。
黃茂林把他家裏看了看,直截了當的問小柱,“我在縣城開了個作坊,如今缺個大掌櫃,你願不願意去給我幫忙?”
小柱也不太了解黃茂林這幾年的況,但師傅誠心相邀,他也不能直接拒絕。
黃茂林也不瞞他,把自己的況略微說了說,“你自己想好,若是願意過著熱乎的小日子,我也不能強求你。去我那邊,定然比現在忙碌,好就是能多掙些銀子,不用整日風裏來雨裏去的賣豆腐。”
黃茂林吃了頓飯就走了,過了幾日,小柱自己找上了門,“師傅,我願意跟著您幹。”
小柱是個忠厚之人,黃茂林把他給黃炎夏,沒多長時間,小柱憑著自己的本事和黃茂林的信任,了水玉坊的大掌櫃。
黃茂林心裏清楚,過幾年孩子們都大了,先後都要參加科舉,自己不能再整日與這些事打道,必須要盡快把他們全部到合夥人手裏。
一旦黃茂林撒手不管,他必須要提高合夥人的分。
今年,眼見著慧哥兒要參加科舉,黃茂林覺得時候到了。
正月的一個晚上,黃茂林把泰和打發走,和梅香坐在燈下說話,“如今家裏也有了五百畝地,各產業一年也能進不銀子。這些年,不管是豆腐坊、油坊還是老家的產業,我一樣都沒丟。但抓的這樣多,一來幹的不細,二來像是個賣雜貨的。我準備隻留下糧店和豆腐坊,其餘的全部出去,以後每年隻得些分,你看可行?”
梅香點點頭,“是該都出去了,我眼見著你整日忙碌,又幫不上什麽忙。如今家裏不說富貴,日子也還過得去。你把糧店留下,這個每年來錢最多。其餘幾樣東西,都給他們打理,咱們一年分些錢就是了。”
黃茂林了梅香的臉,“這一年可不銀子呢,出去你舍得?”
梅香拍下他的手,“多錢也不如你的子骨重要,你年的時候整日挑著擔子賣豆腐,風裏來雨裏去,吃了那麽多苦,這些年又一直忙忙碌碌,也掙下了不家業,也該歇一歇了。有這些東西傳給他們兄弟,可著整個榮定縣,也不算丟人。”
黃茂林想了想,“我既然準備撒手不管,各家的契約書就要重新簽。”
梅香問他,“你預備怎麽分?”
黃茂林也說不好,“我先去打聽打聽外麵別人家的例,再說也不遲。”
梅香也不反對,“盡量不要傷了親戚分。”
黃茂林出去打聽了幾天,先回了平安鎮,找了葉家人和張發財。
如意坊那邊,葉厚則回家去了,這邊給了葉思賢和曹大郎,一個是梅香的表兄,一個是黃茂林的表弟,二人還算和睦相。
黃茂林有些頭疼,自己若不管了,如意坊這邊到底給誰來主事呢。
他先去找了張發財,把自己的想法一一說給他聽。
張發財置辦了一桌酒席招待黃茂林,一邊喝酒一邊拍他的肩膀,“兄弟,這幾年我幫你看著迎賓樓,說是二八分,加上你一年給我的紅包,都快趕上四六了。你不用心,以後你什麽都不用管,咱們還照著以前的規矩。”
黃茂林也喝得有些醉,“那怎麽能,發財哥日辛苦,我既然不管了,隻能算二東家。”
兩個人互相謙虛,最後決定,以後五五分,除非是牽扯到迎賓樓存亡,其餘的事,黃茂林什麽都不管了。二人重新簽訂了契約書,黃茂林又去了如意坊。
葉思賢和曹大郎一起招待了他,葉思賢是葉厚則一手帶起來的,他本就明強幹的很。曹大郎是黃炎夏帶的,但黃炎夏沒帶他多久就去了縣城。如意坊這邊,曹大郎漸漸被後來的葉思賢了一頭。
這也是避免不了的事,當日葉厚則和黃炎夏共事,二人旗鼓相當,但黃炎夏是黃茂林的親爹,葉厚則能幹,他隻有更高興的。
如今葉曹兩人的關係就完全不一樣了,一旦有人冒頭,另一個就要為輔。
黃茂林先說出來自己不想再管事的想法,葉曹二人都有些心。
為了不使他們起紛爭,黃茂林想了個法子,貨倉歸一人管,門臉兒歸一人管,兩人抓鬮,看老天爺的意思。
最後,葉思賢抓到了貨倉,曹大郎分得了門臉兒。
黃茂林索把他們二人分開,各自簽了協議,也按照五五分。
簽協議的途中,黃茂林再三囑托他們,“你們雖然各自管了一塊,但如意坊是個整,萬萬不可裏頭先打了起來。貨倉和門臉兒誰也離不開誰,一家好另一家也能好。”
葉思賢向黃茂林保證,“妹夫放心,我們靠著你得了這個飯碗,怎麽會幹自己砸飯碗的事。外人又不知道我們裏麵的事,若是我們自己人先打了起來,誰都得不到好。再者,我和曹兄弟一向也好的很,生意歸生意,我們的也不是假的。”
曹大郎也連忙拍脯,“表哥不用擔心,我自知能力比不上葉大哥,以後好生跟著他幹,就算協議是分開簽的,我們也不會隻管自己一畝三分地,還是一起使勁,才能把如意坊管好。”
黃茂林理完了平安鎮的事,火速返回縣城。
水玉坊那邊就不一樣了,黃茂林暫時給小柱管,每個月給他分了不錢,但並沒有完全給他。
至於油坊那裏,黃茂林直接甩給了韓明輝兄弟,連協議都沒簽。韓明輝給黃茂林送銀子,黃茂林把銀子一分為二,自己留一半,送給葉氏一半。
葉氏也不拒絕,油坊對於來說意義深厚。這些錢如今在這裏不算個什麽,但因為出自油坊,葉氏總覺得好像韓敬平還活著似的。
理完了外頭的產業,黃茂林把更多的時間都放到了家裏。
慧哥兒要參加縣試,黃茂林忽然變得異常張,仿佛要考試的人是他自己似的。
一天,黃茂林又愁的在屋裏轉圈,梅香笑話他,“幹脆你去考算了。”
黃茂林也不知道自己為何這樣張,“兒子考試,我也幫不上忙,隻能幹著急。”
梅香又勸他,“天下父母心,大多不過如此。但我們著急也沒用,還是得靠他自己。你若真急,明兒給他準備考籃的事給你算了。”
黃茂林坐到梅香邊,“我哪裏會這個,你帶著我一起做吧。”
梅香果真帶著黃茂林一起給兒子準備考試的東西,筆墨紙硯,裳鞋,一樣都不能錯。
不慧哥兒要考試,長俊更是早就到了考試的年紀。
剛過完年沒多久,李先生忽然向葉氏請辭。
葉氏大驚,“先生如何說要走的話?長俊要考試,我著人送他回去,不是說報名的事家裏都已經預備妥當了,如何先生還要自己回去?考場那邊都是男人,先生去了也不便。”
李先生笑著看向葉氏,“這些年承蒙太太厚,收留我們母子,長俊得韓二爺教導,我也有兩個好學生,一年還能賺不束脩。這幾年的日子,是我這輩子最平和的。但千裏搭長棚,天底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我與太太的緣分,怕是也到了,故而來向太太辭行。”
葉氏有些擔憂,“先生此去,可有去?有無外人欺辱?先生一個人帶著孩子不容易。”
李先生搖頭,“多謝太太關心,不瞞太太,我原也出生在書香門第之家,父親做過三品侍郎。先夫早逝,我帶著孩子在夫家守寡。後來娘家敗落,族中有黑心豺狼意謀害我們母子,我才帶著孩子出來了。我兄弟今年起複,做了六品道臺,我也有靠山了。長俊今年十五,我們該回去了,他不要考試,還要說親事呢。”
葉氏這才放心,“恭喜先生,守得雲開見日出。等長俊有了功名,再娶個賢良的兒媳婦,先生的好日子就來了。”
李先生笑瞇瞇的看向葉氏,“可不就是,我跟太太一樣,都是先苦後甜。”
葉氏憐憫一個人帶孩子不容易,送了厚厚的儀程。
聽說李先生要走,青蓮頓時驚呆了。
哭著跑回家跟梅香哭訴,“阿娘,李先生要走了,我怎麽辦?”
梅香把兒摟在懷裏安,“李先生本就不是榮定縣人,長俊要科舉,早晚他們都要走的。你反過來想一想,能得李先生教導這麽多年,也是你們師徒之間的緣分。不管李先生去了哪裏,你們的師徒名分一輩子都在。若是來日還能再見,再續這分。你看看小柱,當日一別,我與你阿爹還以為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現在不又是天天見麵。”
青蓮了眼淚,“阿娘,您替我買些好料子,我給先生和長俊哥做一裳。”
梅香點頭,“你放心,阿娘年前還剩下一些好料子,等會子開了箱子你自己去挑,想要什麽樣的都行。”
青蓮點頭,“多謝阿娘。”說完,又哭了起來。李先生於青蓮來說,如同半母,教導學識和許多為人事的規矩。長俊也是一樣,經常陪一起讀書寫字,還跟一起到花園裏摘花,比慧哥兒還照顧。
梅香和李先生各有千秋,二人教導青蓮的地方也不一樣,卻恰好能互補。
這些年相下來,李先生的風趣和善,長俊溫和有耐,母子二人早就贏得了青蓮的心。忽然說要走,十一歲的青蓮頓時有些不住。
不青蓮難過,慧哥兒心裏也不大舒坦。這幾年間,他和長俊整日同進同出,一起讀書一起玩耍。他時常去舅舅家和長俊睡在一起,長俊也時長來黃家和慧哥兒同吃同睡。
忽然間長俊要走,且這一走山高水遠,還不知此生能不能再見。慧哥兒頓時覺得茶飯不香,眼見著要考試,黃茂林和梅香憂心不已。
李先生豁達,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分都是有限的,如今到了該分開的時候,並沒有太多傷。
但李先生雖然表麵上風輕雲淡,其實心細如發。從說出要走的那一天開始,就發現兒子的不對勁。
李先生親自勸兒子,“長俊,你是不是舍不得這裏?”
長俊抬眼看向李先生,“阿娘,咱們在這裏住了這麽多年,兒子舍不得也是常理。”
李先生不錯眼的盯著兒子,“你舍不得韓家?舍不得慧哥兒?”
長俊低下了頭,“都有。”
李先生瞇起了眼睛,忽然間發問,“還是說,你舍不得青蓮?”
長俊忽然像被針刺了屁一樣,一下子跳了起來,連忙擺手,“沒有沒有,阿娘不要說。”
李先生何等明,兒子的那些小心思哪裏能瞞得過,“你老實說,到底是有還是沒有?你要說有,我就另行安排,你要說沒有,那咱們就早些走。”
長俊呆住了,怯怯的看了李先生一眼,“阿娘有什麽安排?”
李先生撲哧笑了,“我的安排就是帶著你走快些,上沒有功名,你狗屁不算,我拿什麽去提親。”
長俊忽然間變得結結,“提,提親?”
李先生自己給自己倒了杯茶,“你都十五了,難道不該給你說媳婦?還是說你想打?你要是想打那就算了,反正又不是我有兒子養老送終了。”
長俊頓時雙臉通紅,“阿娘真是的,打趣兒子作甚。”
李先生喝了口茶,“你倒是說有還是沒有?”
長俊又坐下了,雙手不停的撥弄著擺,“阿娘,青蓮還小呢。”
李先生笑罵他,“呸,你還知道小。我就奇怪了,整日和清溪形影不離,你眼裏怎麽就看不見清溪?按理說清溪還大一些,不是應該和你更說得來。”
長俊扭了扭手指頭,“阿娘,黃家叔父和嬸子關係特別好。”
李先生忽然就懂了,兒子自小沒了親爹,忽然間見到這樣和睦隨的一家子,心生癡。怪不得他喜歡往黃家去,怕是喜歡那種其樂融融的大家庭氛圍。
清溪的父母雖然關係也好,但韓縣丞夫婦二人之間有時候禮儀較多,比不上黃家夫婦之間那種毫無拘束的相之道。
李先生心裏有些發酸,了比自己還高的兒子的頭,“你要是真喜歡,等你今年考完了試,要是能有所斬獲,阿娘再回來給你提親,好不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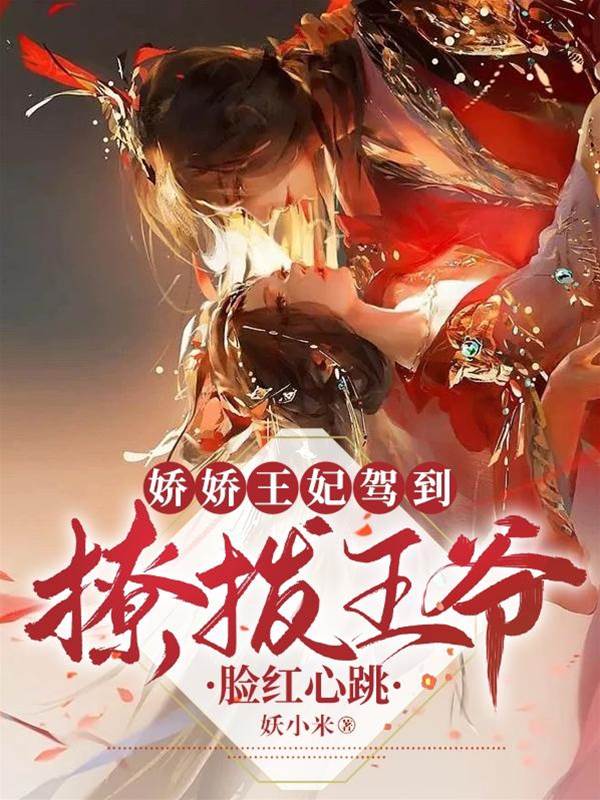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4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