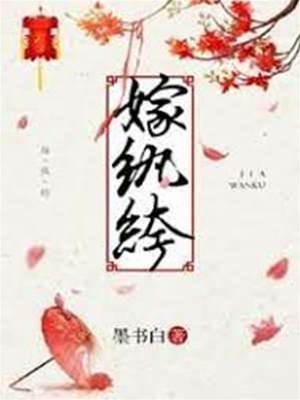《替身王妃帶球跑路了》 第130章 不能原諒
夷阿豸像條瀕死的魚一樣在地上仰頭撲騰著,語無倫次地用著穆清葭聽不懂的語言高聲咒罵著,恨不得將眼前之人拆骨腹,生嚼的。
穆清葭漠然地看著他無能狂怒的模樣。
“我從前總以為,一國朝堂的斗都只該止于國境之,不危及邊疆,不傷到百姓。直到見到了你們這群瘋子,我才算是開了眼界。”
諷刺道:“你們大通的那位年輕的帝王目短淺,你們也同他一樣目短淺。五年前北境的那場戰役還沒將你們打明白嗎?你們怎麼敢在割地賠償之后還這般妄自尊大,認為我大鄴朝廷和我大鄴江山,都能為你們的掌中之,隨你們圓扁?”
“你放屁!”夷阿豸滿污,青筋曝地反駁道,“我們圣主是被上蒼欽定的社稷主宰,得雪山之神庇佑,終有一天要一統天下!你們注定了只會為圣主腳下的螻蟻,又怎麼能懂圣主的雄心抱負!而我們能為了大義獻,歷史會記住我們,我們死而無憾!”
“笑話。”穆清葭嗤了一聲,“雄心抱負?明明就是滿足他個人的虛榮心罷了。”
說道:“你們的那位圣主若真是一位明君,豈會不考慮邊境數萬百姓的生死,豈能忍心用將士們的之軀去填他的壑,豈敢在打碎了兩國的友好邦之后,還大言不慚地說,他是在奉行上天的旨意?”
“還是你們真以為,我大鄴盡是弱可欺之輩,明知賊人跑進家門搗了,還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忍氣吞聲,打落牙齒和吞,忍下了此次的損傷?難道你們認為,我們不會用更加狠毒的方式報復回去,認為我們不會發戰爭,打進你們大通國境之去嗎?”
夷阿豸瞪向穆清葭:“你們敢撕毀和平盟約!”
“撕毀盟約的不是我們大鄴,而是你們大通。”穆清葭冷道,“和平來之不易,可但凡有之人,就不會允許有人踩上腦袋來挑釁,辱我山河,傷我百姓。北境戰事一起,無數生靈涂炭。只是不知你們大通邊境線上的那些無辜百姓,是否也同我大鄴子民一樣,知道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犧牲的。”
一字一頓地同夷阿豸強調,語氣里帶著深濃的冰冷的惡意:“你們注定不能在青史上留名了。倘若歷史真的會記錄下你們,也定然只會寫你們是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的小人,將你們釘在恥辱柱上,讓你們臭萬年!”
夷阿豸暴怒的神隨著穆清葭的話而平復下來。
他揚起的頭顱又往后倒了回去,怔愣地著天空。興許是被灼烈的照得眼睛刺痛了吧,穆清葭看到有晶瑩的亮在他眼眶里涌。
失去了神支柱的老者,驟然間顯出了枯朽的氣息來。
夷阿豸想象著穆清葭所說的生靈涂炭,想象著在戰爭的瘡痍后,大通和大鄴邊境線附近的哀鴻遍野浮尸千里,想象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苦痛,想象著找不到家的孩子的哭聲……
他忽然有些搖,今時今日再回想起他這些年來走過的路,拋卻那些自認高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一時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為了得到什麼。
臭萬年……呵……
他扯了扯角,茫然地呢喃道:“可我們做這一切的初衷,本沒有錯啊……”
他歲數大了,所以清楚地記得三十年前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三十年前,他們這支被從族譜上除名的旁系所犯的大罪,不過就是拒絕讓族中的去番邦和親罷了。
每個人生來就是雪原上的雄鷹,有自己的人生。他們以為,如果兩國之間的和平是要建立在無數為此獻出青春、自由乃至生命的基礎上的,那倒不如讓他們這些兒郎拿起刀戈,去戰場上面拼殺一場。
只是那個時候,夷阿氏的大族長和其他宗老不這樣想。
西北狼族時時侵擾,大通當時國力弱,怎經得起戰爭帶來的消耗?若能用不傷一兵一卒的方式換得太平,若只要舍棄一人就能挽救千萬人,他們夷阿氏作為大通的第一大氏族,就該首當其沖。
于是政見不合,他們這一支系在族譜上被除去了名。自此他們不再有姓,如孤魂野鬼一般,舉族遷移到了水草稀缺的苦寒之地,度過了極為艱難的十五年。
只是慢慢的,當初堅持要與氏族割席的那幾位宗老首領相繼離世,剩余的族人想要重新得到歸屬,想要回到繁華的王都里去。
正好當時圣主選妃,夷阿氏卻因常年和親已經找不到適齡子。故而他們為了與家族重修于好,將族中最優秀的三位過繼給了夷阿正系。
或許是雪山之神庇佑,其中一位被圣主選中為妃,誕下了皇子,甚至這位皇子還為了如今的大通皇帝。
只是大概是時隔太久了吧,讓他們都忘了當初的決絕與堅守是為了什麼。
他們忘記了當初為了守護住心中的正義,為了弱小者,他們做出過怎樣慘烈的抗爭。
以至于曾經為了讓每一個男老都能為自由的雄鷹而憤慨過、反抗過、放棄了來路份的他們,如今竟為了重新獲得份尊榮,了將這些普通的男老推進戰爭火坑的劊子手。
屠龍的勇士,最終為了那條惡龍。
何其荒唐?
然而最初,他們選擇這條奔赴異鄉的路時,只是為了讓他們顯得有些價值,只是為了可以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他們所求的,不過是讓族人能活得有尊嚴、有人樣罷了。
讓他們族中那些老弱能有個安穩的棲地,讓那些新出生的孩子們能看到更高更遠的天地。
他們不過是為了他們剩下的那些親人都能過得好一些,僅此而已。
他們所求的都是最平凡、最卑微的東西啊,他們又有什麼錯呢?
夷阿豸茫然地著蔚藍的天空,著被渲染得幾近明的白云。
他記得家鄉的天空遠比眼前的更加湛藍遼闊,記得茂盛的草原上牛羊群。
只是他已經十幾年沒有回去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的家鄉,他為之奉獻出了生命的親人,究竟還記不記得他……
“你是怎麼查到我的?”夷阿豸問穆清葭道,“我自認這三年來藏得很好,從未出過馬腳。為什麼你這次突然就殺到了徐記果煎鋪子,為什麼會知道是我?”
他愣了一下:“難道……是顧簪煙那兒出了問題?是供出了我嗎?”
還沒來得及想明白的一切在這一刻像是散落的珠子一樣被串聯起來的。
夷阿豸恍然地自語道:“怪不得我們已經許久沒有得到的消息了,怪不得我們安在京城中的那些暗樁被毀了個干凈……原來已經落網了,叛變了,原來是你們將藏起來了!”
“的確已經了階下囚,只不過究竟有沒有將你供出來,這一點我并不知曉。”穆清葭漠然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三年來,你在特地為我準備那份加了生芭蕉子的蓮子藕時就該知道,早晚有一天我會弄清楚這一切的。”
“三年,你覺得太早?可在我看來,直到今天才抓住你,已經晚了太多了!”
穆清葭最初確實想不明白這個藏在徐記果煎鋪子里要暗害的人會是誰。
就同楚云遏說過的那樣,周瑾寒在京城中樹敵太多,為他的王妃,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要羅列出想害的人的名單,那可實在是一項不小的工程。
只是后來出了散草一事后,不由又聯想到了這三年買回來的蓮子藕。
用這兩樣東西來害,都是為了讓的寒加重,最終因氣兩虧而亡。
那麼要做這件事,一來得對的況了解得很清楚,知道的寒十分嚴重,才能保證這個方法有效;二來,既是選擇了用這種慢法子,要麼是他們對的仇恨不深,只是為了讓多吃點苦頭,要麼就是他們不得已,不能一下子殺死。
這樣一想,就能排除很多人了。
首先要布下這麼大的一張網,查明這麼多信息,非實力雄厚者不能夠。其次,如果是周瑾寒的死敵遷怒于,那必然要殺而后快,哪兒能費這個心跟慢慢磨?
宮里的人要殺多的是暗法子,犯不上利用一間小小的果煎鋪子;
司空鶴既言明了最初看中的就是的能力,又已經往種下雙生蠱,還讓太醫院改掉了送給的補藥,沒有再來徐記果煎鋪子里一手的理由。
思來想去,排除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唯一可能就只有簪煙了。
只能是這個藏在徐記的人,所做的事都是為了幫助簪煙。
而這也與后來給自己下散草的做法殊途同歸。
那麼既然想明白了這一點,再結合簪煙與那位“閆先生”的關系,也就不難猜出藏在徐記里的是什麼人了。
最初和覃榆懷疑是鋪子里的伙計,可生芭蕉子是與蓮子碎一樣被烘烤過的,伙計顯然不可能做到這樣,只能是在廚房里的人才行。
也就是說,徐記果煎鋪子的廚房里,有一個點心師傅,也是大通安在大鄴京城的一個暗樁。
“你知道我今日來之前,最擔心的是什麼嗎?”穆清葭道,“不是你的地位在你們這批大通細里有多重要,也不是我面對你可能有幾勝算。我最擔心的,是你不過一個謹慎膽小的鼠輩,在我來抓你之前,你就已經跑了。”
“所以我其實還得謝你的這份自大。若非你因自大和心存僥幸而留了下來,我今日就得撲一場空。”
夷阿豸冷笑了聲。
“可惜啊,即使你今天抓了我,即使你們已經控制了顧簪煙,你——穆清葭,還有那位權勢滔天的曜王,你們也回不到從前了。”
夷阿豸眉目鷙地盯著穆清葭,笑起來:“你們倆上可是背負著上一代的仇恨啊,你的祖——唔!”
锃亮的寒一閃。
穆清葭手中劍柄一旋,珠飛濺的同時,一截舌頭從夷阿豸的里掉了出來。
夷阿豸未盡的話語永遠截斷在了嚨里。
穆清葭面無表收劍歸鞘,看著跟前地面上的人死魚一般大睜著雙眼瞪著他,含著一嚨的,模糊地發著一串雜音。
他應該又是在罵娘吧?
只是將死之人口中的話,除非是自己想聽的,否則穆清葭半點注意都懶得分給他。
只對后的使揮了兩下手指,涼聲道:“將他帶回去,給長公主好生看押。他日同大通國談判之時,還得將他們這一批人當做籌碼帶到大通那位無德無能的皇帝跟前去。”
“哦對了——”穆清葭轉回,補充道,“別忘了將他上文了‘彎刀落月’——不,‘彎刀落弦月’刺青的皮割下來,興許還能當做禮送給旁人。”
夷阿豸聽了穆清葭的話,發了狂一樣甩著頭嘶吼起來。
沫從嚨里噴到了臉上,濺進他的眼睛里混眼淚中,像是流著淚的惡鬼。
穆清葭的語調轉得和了許多,嘆聲道:“都是一群早在三十年前就該消失的人,上留著相似的刺青,只會辱沒了‘夷阿’這個姓氏。相信遠在大通的另外一批刺了‘滿月’的人,會很激我們替他們除去了心頭大患吧?”
話盡,沒再多看悲憤到形容癲狂的老者一眼,轉走向了前頭的鋪面。
這世上人人都有苦衷,可并不代表有了苦衷,犯下的罪行就能得到原諒。
不是以德報怨的圣母,到了傷害的大鄴百姓們也都不是。
后廚的另外兩個點心師傅和那個跑去躲風頭的小伙計此刻也都被捆在了鋪子里。他們是親眼見到了穆清葭與夷阿豸的打斗,又從滿的夷阿豸邊被一路拖到前面鋪子來的,好死不死,正好還聽見了穆清葭說夷阿豸同那通敵叛國的流云榭有關。
誰能想到呢?天天跟他們待在一起的這個寡言的“老豸”,竟然是潛伏在他們大鄴京城里的細?
這可是整整三年啊!
窩藏敵國細的罪名一旦落下,他們腦袋搬家都是輕的了!
三人哭無淚,臉比死了三天的尸還白。
尤其是后門影一閃,那個戴著銀白鬼面的黑袍人帶著一腥味走進來了。徐記的一票人被嚇得一激靈,膽子小的已經當場暈了。
“大人。”其中一個使詢問道,“這些人該如何置?”
穆清葭冷眼朝這群鵪鶉似的人一掃。
正想回答,大門卻在這時被人拍響了。
“有人嗎?我是來取糕點的。”清脆的聲喊道。
眾使戒備地拔劍抵到了門口,其中幾個還用劍指住了試圖發聲求救的徐記眾人,威脅他們都老實閉。
穆清葭收角,悄聲湊到窗前,用劍鞘稍稍打開了一道朝外頭去。
大門口,一輛馬車正在階下等候。提著籃子的那年輕姑娘抬手又往門板上敲了兩記,有些不解地加大了聲音:“有人在嗎?我是曜王府的,約好來取今天的糕點的。”
“快開門。”語氣加重了些,說道:“咱們王爺和王妃說不準今天就要進京,要是誤了王妃的吃食,以后你們徐記果煎鋪子可做不咱們王府的生意了!”
穆清葭面沉郁地看著一墻之隔的這個人,黑袍遮掩下的手握了拳。
的眼中流出深刻的哀切來。
因為門外的人,是覃桑。
猜你喜歡
-
完結758 章

慕紅裳
個性活潑的女大學生謝家琪抹黑下樓扔個垃圾,不小心跌下了樓,再睜開眼,她發現自己變成了右相府的嫡小姐謝淑柔;榮康郡王正妃顧儀蘭絕望自裁,一睜眼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四歲,一切都可以重頭再來。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與安國公家的小姑娘穆紅裳沒關係,紅裳怎樣都想不明白,她的人生怎地就從此天翻地覆……
123.8萬字8 6379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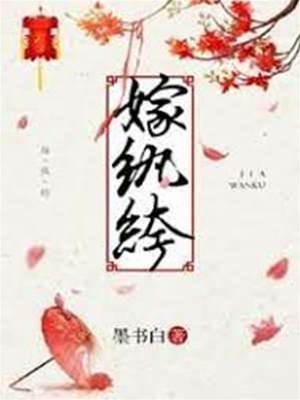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287 -
完結283 章

代嫁太子妃
簡介: 一朝穿越,她成了出身名門的官家小姐,青梅繞竹馬,卻是三人成行……陰差陽錯,定親時她的心上人卻成了未來姐夫,姐姐對幾番起落的夫家不屑一顧。她滿懷期待代姐出嫁,不但沒得到他的憐惜,反而使自己陷入一次更甚一次的屈辱之中。他肆意的把她踩在腳下,做歌姬,當舞姬,毀容,甚至親手把她送上別人的床榻……
23.2萬字8 10713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1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