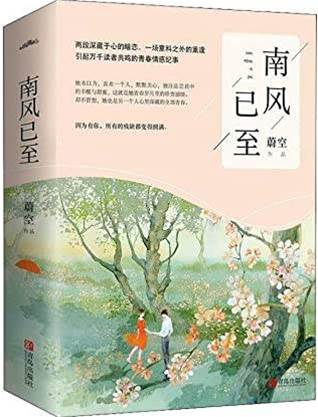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哄好了沒》 第112 章 我現在被你治得,跟條狗一樣
“你就會哄我。”盛意了胳膊,把陳最腦袋從肩膀上抖了下來。
“你看我承認了,你也不信。”陳最從後麵抱著,把往觀影沙發上推。
盛意被他抱得,迫不得已跟著他的步伐坐到沙發上:
“也不是不信,就是覺得當時你在學校,也不缺孩子陪著,不太像一直想著我..那什麽的那種。”
陳最摁著遙控選電影,不知道看什麽,他一直按著鍵,重重地“哦”了一聲。
“所以當時進你樓裏,被你調戲,你是故意的?”
來他家沒多久就因為,去他樓裏找吃的。
“你對別的人也這樣?”
他那時又混又壞,像條沒經過馴服的惡犬,揪著的睡問是不是沒穿。
當時盛意剛寄人籬下,膽子小,忌憚他,隻小聲罵了他一句,然後回去自己哭了好久。
要是放在現在,高低要扇他一掌。
陳最歎了口氣,搖頭否認:“沒,就看你有覺。”
“哼。”盛意推開他,也不管他手上瞎按到什麽。
手去翻手邊置架的老碟。
“我那不是小時候看我爸搞有影,一直覺得這事兒惡心的,後來看你就在我對麵樓的臺上晾服...”
陳最也有點不好意思,小姑娘那個時候可能不知道有烘幹機,也不知道對麵有人在看,穿著吊帶就去晾自己的服。
陳最看完當天晚上就夢見了:“我就...就那什麽了唄。”
陳最看,捂著笑了笑,又說:“那晚你來我樓裏,怎麽爬進來的,我全看見了,就等你進來逗你玩兒呢。”
所以本就不是什麽湊巧他看不順眼之類的爛借口。
恰好是他早就打定主意了,把接到自己家後就一直在等。
隻不過為什麽要用這種讓人討厭的方式?
盛意不理解,陳最自己都不清楚。
他明明有那麽多讓孩子喜歡,追捧的點,偏偏用了最低級的方式。
事實就是,他本學不會像普通男生追孩子那樣,曖昧,告白,,婚姻。
太慢了,他等不及。
盛意這樣子的溫吞格,一旦他在曖昧過程中讓別人鑽了空子,他才要追悔莫及。
“你那個時候就超級過分的。”盛意想了想,又很生氣:“什麽都來惹我,惹得我生氣了又來哄,好像我就是個玩。”
陳最又重重地歎了口氣,承認:
“年紀小想吸引你注意,不太懂啊。”
他手去抱盛意,兩人推搡間盛意,盛意睡開,他又手進去,啞著嗓子說:
“所以幻想一直是你。視頻是分手那天才導進手機的。”
他笑得壞:“事實證明,也沒導錯,不然這半年我要憋死。”
“好了你可以閉了。”盛意摁住他下的手,角彎著。
以前對陳最的,盛意一直不太確定又奇怪。
這人就背後做這麽多,當麵連一聲“我你”都沒說過。
換其生早就要著他告白了,偏偏盛意就篤定他一定喜歡,所以那句話說不說已經不重要了。
手被摁著,陳最靠在盛意肩上的腦袋用了點力:
“那你呢,第一次見我,怎麽想的?”
“很拽。”盛意眨了眨眼,沒忍住,笑著補了一句:“好做作的。”
穿著運服,頭發比他現在的短發要長點兒,估計是從國外回來沒來得及剪,碎發自然垂在眼角。
不得已看人的時候得微微抬著頭,又因為輕度近視,得瞇著眼。
不知道是不是運服的立廓形把整個人散漫的氣質又襯得有點冷。
但總就是個裝的混球。
尤其是校慶的發言,他校服就套了個外套,拉鏈也沒拉,站在演講臺上說什麽人的天賦是早就定好了的,普通人盡力就行,別為難自己。
實在是太裝,偏偏還沒人敢說他什麽。
“反正就是印象不太好,想看看誰能治你。”盛意撇了撇。
想起那個時候,他是真的很欠揍啊。
“還能有誰治我啊?”陳最拉了拉的睡,將人抱著換了個姿勢,麵對麵瞧著:
“我現在被你治得,跟條狗一樣。”
“什麽像條狗一樣。”盛意紅著臉瞪大眼睛:“你怎麽總是講。”
“又會跪又會。”陳最說的意思就是字麵意思:
“這不就是狗嗎?連寧宇他們都這樣兒形容我了。”
....盛意有時候覺得陳最就這麽直白地讓人沒辦法接話。
真的很想打他啊。
這人一說到什麽話,就總是帶著點兒其他意思。
陳最無所謂地扣著的手,調了燈,指著電視問:“想看哪部?”
被他麵對麵抱著,看電視都得扭頭,看哪部重要嗎?
“行啊,那我隨便放。”陳最將人腦袋摁進懷裏,不懷好意地勾著角,手選了半天才點播放。
下一秒,盛意就聽見自己細碎的聲音在放映室回。
還投屏了整個幕布。
“不是說好了,純聊天嗎,你騙我?”盛意將頭埋進他懷裏,紅著臉不肯抬頭:“我真是信了你的鬼話。”
“就當是我求你,行了吧,求你了寶寶。”陳最拍了拍盛意背上的蝴蝶骨:“快搞我。”
盛意抱著他的脖子搖頭。
陳最也不急,單手把沙發邊的一個巨大的紙箱單手拎到沙發上,聽響聲,裏麵應該是些零零散散的東西。
打開虛掩的蓋子,一件一件地往外拿。
盛意抬頭起來,看他手裏先是著網狀,他認真地看了眼,嘖了聲:
“過時了,太俗了。”
然後是絨絨的尾,他壞笑的眸子裏閃了點兒,故意掃到盛意臉上:
“玩兒嗎乖乖?”
盛意呼吸都變重,抓住他的手:“不玩。”
然後摁停他的作。
陳最語氣哄著解釋:“我也沒做什麽呢寶寶,我就是想和你一起看看,這不都是我們以前買的嗎,很多沒用過,也不知道幹嘛的,怎麽玩。”
盛意立刻反駁:“是你買的,不是u0027我,們u0027,我不知道你買了這麽多這種東西!”
盛意手上力氣不大,他沒幾下就掙了,又扯了一堆七八糟的。
“隨你怎麽說咯,我就是看看,這些都是做什麽的,我又不認識,也沒玩兒過幾樣。”
陳最裏說的冠冕堂皇,挑挑揀揀好半天,盛意一個都沒同意。
他就不太高興了。
從箱底扯了件鏤空又難穿,布料不太多的綢質地的旗袍,用指尖挲了幾下。
這件就他媽很在他的點上了。
之前都玩得是純,這麽直白又的,他沒玩過。
簡直了。
想玩。
陳最慢條斯理地拆著服,怕人跑了,胳膊還錮著盛意。
“你在幹什麽呀?”盛意看陳最半天都沒說什麽話,沉著呼吸抱著,在背後不知道弄些什麽。
陳最已經把手上那點布料理順了,解好,垂在麵前:
“乖乖的,我給你穿,好不好?”
他聲線和得能沁出水。
?
盛意還沒反應過來,就已經到了解扣的步驟。
手不願得推了兩把,被陳最親了幾回,最終還是默聲隨便他怎麽造。
“又上套了吧乖乖。”
陳最認認真真地給扣著服,挑眉一臉得意。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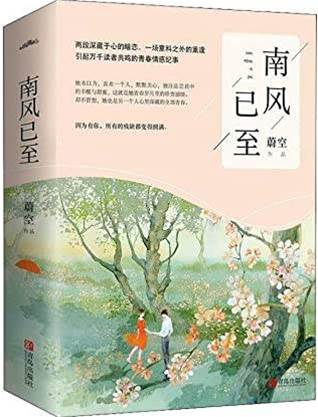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191 -
完結540 章
全球示愛少夫人
“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但愛情免談。” 蘇輕葉爽快答應,“成交。 “ 可他並沒有想到,婚後她對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 “靳先生,我想要離婚。” 男人把她抵在牆角,狠狠咬住她的唇,「想離婚? 不如先生個孩子。 ”
93.6萬字8 294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