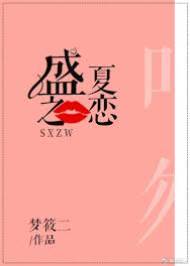《甜誘!傅爺的心尖寵她嬌又撩》 第132章 乖小狗
半月後。
臥室的大床上,宋時漾一手捂著腰,一手可憐兮兮的抹著眼淚,小委屈的撅著:“騙子,我要回棠錦園。”
什麽高冷,明明就是斯文敗類,視頻沒被發現前,他還能裝一裝,現在呢,直接出真麵目,抓著狠...do,怎麽裝可憐哭都沒用,因為他會裝的比更可憐。
想起前幾晚,男人紅著眼眶哼哼唧唧:“姐姐,你就不能疼疼我嗎?求你~”
現在想起來,小都還打。
跪在地毯上的傅祁韞看了眼腕骨上的手表,淩晨兩點,太晚了。
他拿著手裏的藥膏,溫的嗓音輕哄著:“乖乖,先抹藥,明天送你回去好不好?”
宋時漾看著他手腕上的咬痕,瞪他一眼:“現在就要回去!”
“乖,現在太晚了。”
宋時漾哼一聲:“你也知道現在太晚了?”
“老公錯了,乖乖~”傅祁韞向床邊挪近,大掌握住細白的腳踝:“小祖宗,我們先抹藥好不好?”
宋時漾收回腳踝放進被子裏,出手:“給我,我自己會抹。”
“好。”傅祁韞打開藥蓋遞給:“周圍都要抹上,裏麵也要。”
宋時漾頓住作,周圍也就算了,裏麵是什麽意思?
傅祁韞看著泛紅的耳尖,低聲輕笑:“我很樂意為公主效勞。”
宋時漾撇過頭,閉上眼睛,表示默認。
傅祁韞跪坐到床上,藥膏捂熱後一點一點細致微的塗抹著,細白的小輕,菲薄的微微勾起,他帶著點點技巧打圈按。
紅溢出的嚶嚀,宋時漾咬住下,漂亮的桃花眼裏泛起的水。
指尖的藥膏漸漸潤化掉,男人額上青筋湧起,結氣難耐的滾幾下。
他加快抹藥的速度,塗抹好藥膏,起衝進浴室。
聽著浴室裏的水聲,宋時漾漸漸閉上眼,又困又累,打工人白天上班,晚上還要“上班”。
嗚嗚˃̣̣̥᷄⌓˂̣̣̥᷅
傅祁韞出來時,已經睡著了。
十二月的帝都,天已經很冷了,他用半溫的水衝了一會,上還有些涼,他站到空調前全吹暖後才躺上床,有力的臂彎圈住帶進懷裏,聞著上的玫瑰香睡覺。
翌日。
宋時漾醒的時候已經九點多了,旁的男人靠在床頭辦公。
黑發自然垂落著,眉骨優越,高的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眼鏡,菲薄的抿著,下頜線立致,上穿著垂的黑睡袍,鬆鬆垮垮的,約可見的咬痕,鎖骨冷白,妥妥的斯文敗類。
傅祁韞察覺到的視線,低頭繾綣一笑,眉眼溫:“寶寶醒了,早餐想吃什麽?”
宋時漾撇過頭,拒絕的:“想吃棠錦園的早餐。”
傅祁韞放下電腦,躺到旁邊,指尖起一縷卷發把玩:“真想回去嗎寶寶,現在天這麽冷,你腳會涼的。”
自從天冷了,傅祁韞每晚都會幫暖腳,男人上一直都是燙的,被窩裏特別暖和。
“腳涼有暖水袋。”需要好好休息幾天,再這樣下去,腰非得廢掉。
傅祁韞眼見勸不住,隻好點點頭:“多久?”
“這個不確定。”
“好吧。”傅祁韞坐起幫穿服,薄抿著一言不發。
宋時漾強迫自己移開視線,同男人的下場就是廢小腰,畢竟他那張臉裝起可憐來太有殺傷力了。
可到底還是不忍心,電梯裏宋時漾扯著他袖口輕晃:“幹嘛一副天塌的表,我就是回去住幾天,又不是不回來了。”
傅祁韞垂下眉眼,聲音悶悶的:“幾天是多久?”
宋時漾出手:“五天。”
傅祁韞撇過頭:“三天。”不能再多了。
宋時漾收回扯著他袖口的手,紅輕勾:“七天。”
“就五天!”傅祁韞握住的手十指相扣,臉上的神委屈到不行。
“好~”宋時漾踮起腳尖湊到他邊親了親:“好乖的小狗。”
傅祁韞低頭蹭著的頸窩:“那乖小狗可以去找主人嗎?”
宋時漾義正言辭的推開他:“來找我,然後再讓我你主人嗎?”
。您提供大神蘇源的甜!傅爺的心尖寵又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6112 -
連載1087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9萬字8.18 24614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89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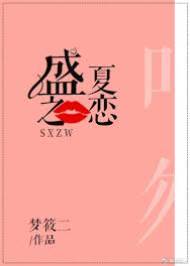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6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