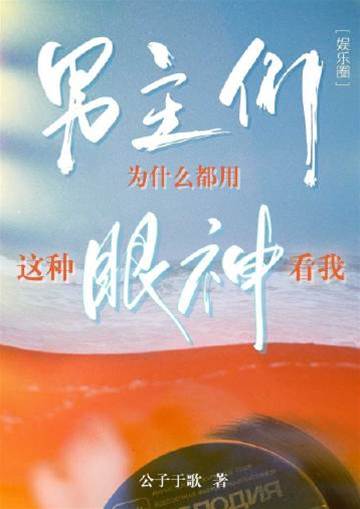《償願》 第61章
我們是夫妻。
這簡簡單單的五個字,像是一顆包含了無數彩帶的水晶球,“嘭”的一聲在祁願的心頭炸開。
繽紛飛揚,悸不息。
忽然想起來十五歲那年,學校裏組織家長會,全班的同學,不是爸爸來就是媽媽來,再不濟也有爺爺,隻有,自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顯得局促又不安。
可就在家長會進行到一半時,程院長和宋瑤都同時趕到了的班級門口。
老師站在講臺上,有些錯愕地看著門外姍姍來遲的兩人,問了聲:“你們是誰的家長?”
一大一小的兩人相視一笑,異口同聲地說:“祁願的。”
永遠都記得那天,程院長為了來參加家長會,穿上的那件他與老伴新婚時穿過的西服,以及宋瑤為了扮,問福利院阿姨借的職業小套裝。
那一刻,差點落下淚來。
家長會結束後,程院長帶著和宋瑤去學校門口的湯店,一個人吃了一碗鴨湯。
隔壁桌恰好有一對年輕夫妻帶著自己年的兒來吃飯,一共三口溫馨和樂,人捧著碗,忙著喂還不會拿筷子的兒,丈夫則在一邊細心地為妻子挑去碗裏的香菜。
說來也是心酸,這些平日生活裏隨可見的溫馨小細節,卻還是深深了祁願。
從年時起,好像就是個很容易為“簡單溫馨”而落淚的人。
記得那天,程院長發現了一直在看那一家三口的視線,過手來了的頭,笑容溫和地對和宋瑤說:“我們瑤瑤和願願,以後都會有家的。”
當時智尚未完全啟蒙的,低下頭攪弄著碗裏的湯,微微落寞地說了句:“不會有了,沒有爸爸媽媽,哪裏來的家呢?”
當時,程院長聽完後,哈哈笑了起來,又了的頭,慈藹地說了聲:“願願長大了也會是媽媽的。”
當時愣了愣,而後才後知後覺的紅了臉。
那個年紀的孩對問題總有著一種害的逃避。
可那也是第一次,忽然想到,自己未來的丈夫會是個什麽樣的人呢?
那時候,也沒有什麽特別心悅的異對象,唯一狂熱喜歡過的,應該就是那個年代,風靡全球的一個華語流行樂的男歌手,但也隻限於對對方音樂天賦與才華的仰慕。
心事泛濫的時期,也曾構想過自己會喜歡什麽樣的男孩子,會和什麽樣的男孩。
但卻從來沒有考慮過婚姻。
因為,在刻板而又古派的思想裏,婚姻是等於家的。
可那時的,對於家這個字,卻是既期盼又畏懼。
期盼那種三餐四季,細水長流式的浪漫與溫馨,但又畏懼生活落於平凡後的瑣碎與爭執,更多的,是覺得自己無法勝任妻子與母親這個角。
甚至到後來,遇到了徐晏清,他在的生命裏幾乎扮演了一個完到極致的伴形象,卻都沒能消除心對婚姻的畏懼。
當年,兩人還在一起時,第一次談及這個問題,就是不歡而散。
當時景園的房子剛買,徐晏清還是以婚前贈送的方式,將房子掛到名下的。
那天他們剛一起去挑選了一圈家居,中午就順便在商場吃了飯,徐晏清坐在對麵,挽起襯衫的扣子,垂著眉眼認真地為剝蝦尾的殼。
兩手托著下,笑嘻嘻地看著他,說了句:“房子都給我了,裝修家居也都是你出錢,將來要是你結婚了,你老婆吃醋怎麽辦呀?”
當時徐晏清剛剝好一顆蝦尾,抬起眉眼看了一眼,挑著眉笑得一臉戲謔:“你有必要吃你自己的醋麽?”
當時愣了愣,才反應過來他說的是什麽意思,當即就有些為難地了手指。
那時候,的確沒考慮過結婚這個問題,連對徐晏清都沒有。
許是的為難太過外,徐晏清也發現了,他將剝好殼的最後一個蝦尾放進的碗裏,摘掉了手上的一次手套,抬起眉眼,神十分認真地看著,問了聲:“你是不想和我結婚麽?”
當時被他問得有些慌,一時間也不敢看他的眼睛,攪著手指,眼神四飄,支支吾吾地說:“不是,我就是覺得……還沒……到這個地步吧,說不定……說不定……”
後半句終究還是沒有勇氣說出口。
可徐晏清的臉當即就沉了下來,問了聲:“說不定什麽?”
那應該是他們在一起那麽久,他第一次用那種神和說話,嚇得立馬就閉不敢說話了。
那頓飯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徐晏清送回學校,從始至終兩人一句話都沒再說。
後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都沒再聯係彼此,還是的舍友發現了反常,暗地問:“祁願,你是不是和你男朋友吵架啦,怎麽這段時間都沒見你出去約會?”
當時還有些委屈,撇著說了聲:“我也不知道,就上次他問我是不是不想和他結婚,我沒答上來,他好像就生氣了,他不找我,我也不敢找他。”
舍友當時眨了眨眼睛,四下看了看,湊過來小心翼翼地問了句:“你是不是……不喜歡他啊,隻是覺得……他有錢?”
當時這種現象在們學校裏很常見,特別還是們這個圈子,漂亮就是孩子最有說服力的武。
看見過被評為“玉掌門人”的學姐,搖曳生姿地走上了校門口的一輛勞斯萊斯,也見過
稚氣未的學妹挽著金主的胳膊混跡各大上層酒會。
當時聽完舍友的猜想,立馬搖了搖頭,否認道:“不是的,我們是真的在往的。”
那時候雖說尚在校園,但已經名氣不小了,與徐晏清的也一直於地下狀態,隻邊幾個比較親近的人知道有男朋友,而知道這個男朋友就是徐晏清的,也隻有宋瑤和林瑜。
舍友當時一臉疑,問:“那你為什麽不回答他?要是有個有錢又賊我的男朋友問我要不要嫁給他,我當場一百八十度瘋狂點頭好嗎?!”
雖然當時討論的話題還正式,還是不忘加了一句:“還帥。”
接收到舍友一記頂級無語的白眼後,才接著說:“我也不是不想嫁給他,而是我本就沒考慮過這個問題,對誰都沒有。”
舍友當時了然的點了點頭,而後又一臉無奈地搖了搖頭,一副恨鐵不鋼的樣子,歎了聲氣,說道:“祁願吶祁願,你長值,不長商吶!你自己想想,如果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在規劃你和他的未來,可他卻忽然來了一句沒想過,你是什麽心?”
眨著眼睛思考了片刻,忽然覺很難過,撇著說了聲:“想哭。”
“那不就得了,就算你現在不想結婚,那你也要告訴他理由呀!或者說對於結婚這個計劃,你覺得什麽時候談才合適啊!他是真的想娶你,而你在結婚的這個問題上,是不是除了他,也沒想過別人?”
最後一句話落耳朵,像是忽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脈,刷的一下子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轉就跑了出去,也不顧舍友在後的呼喚。
那天從學校出來時已經很晚了,但還是打車去了徐晏清的公司。
大冬天的,在他公司門口蹲了一個多小時,才見他神疲憊地從徐氏大廈裏走出來。
記得那天他臉不太好,連小江跟在他後都戰戰兢兢的。
直到小江一眼看見了蹲在路邊花壇旁的,才忽然喊了聲:“小願小姐?”
徐晏清當時也愣了愣,轉頭看過來,臉上的神由最初的黑沉轉為愣怔,而後忽地皺著眉頭大步走過來。
那天走的急,外套都沒穿,差點被凍冰雕。
見他走過來,也緩緩站了起來,但因為蹲太久,都麻了,本想歡快地朝他奔過去的,最後卻像個瘸蛤蟆,跛著腳迎了上去。
接著,不等他斥責的話說出口,就忽地一把抱住了他,將凍得冰涼的小臉在了他膛上,吸了吸鼻子,撒似地說了聲:“你再不出來,我都快要冰雕了。”
徐晏清當時皺著眉看了一眼,最終隻是無奈地歎了口氣,將一雙冰涼的小手揣進了自己的懷裏,問了聲:“怎麽不直接給我打電話?”
故作委屈地撅了撅,嘟囔了聲:“你不是在生氣嘛,我怕你不理我。”
他當時摟著,親了親的發頂,說了聲:“不會,再生氣都不會不理你。”
撅著,氣的哼了一聲:“你就是沒理我!你這幾天一次都沒找我!”
一邊說著,還一邊將揣在他西服外套裏的手,使壞地鑽進了他的襯衫下擺,將冰涼的掌心在了他瘦的腰上。
覺到他被冰到後,下意識的了一下,也跟著咯咯笑了起來,用臉蹭了蹭他的膛,說了句:“懲罰你一下。”
徐晏清也跟著笑了起來,就任由一雙冰疙瘩似的小手在他服作,說道:“不是不理你,我是在想一個問題。”
當時懵了一下,將臉從他口抬了起來,看向他,問了聲:“想什麽呀?”
他垂著眸子看著,湊過來親了親的:“不結婚的話也行,隻不過你就不能平分我的財產了,萬一你哪天遇到更好的人,不想和我在一塊了,從我這裏你也分不走什麽,還白白浪費你這些年的青春。”
說完後,他又溫地親了親的額頭,神鄭重地說:“所以我在想,找個時間把我名下的房產和車產都轉給你,就算離開我,也足夠你好好生活。”
那一刻,忽然了眼眶。
想,哪裏還有人比你更好呢?
見哭了,他心疼地親了親的眼睛:“哭什麽,你記住,我你,但你是自由的。”
可這句話一出,反而哭得更厲害了,嗒嗒地說:“不行,你隻能娶我!我要是不能嫁給你,我該怎麽辦呀!”
他當時笑著親了親臉頰上的淚珠,說了聲:“好。”
從前,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那麽期盼嫁給一個人。
後來,也從來沒想過他們會鬧到那麽難看的地步,之後還能再重逢,更沒想過,有朝一日,他會和說:“祁願,我們是夫妻。”
可終究,一切都還是變了樣。
*
衛生間外,徐晏清依舊保持著雙手撐在頭兩側的作,高大的影幾乎將全部覆蓋。
兩人無言地對視了半晌,在外麵的走廊上有人侃笑著走過時,祁願才忽然如夢初醒,匆匆挪開了視線,兩隻手用力推了一下麵前的人,催促道:“快點,讓開,有人來了。”
徐晏清垂眸看著,勾笑了笑,聽話的鬆開了手,站直了子。
祁願瞥了他一眼,也沒顧及自己上還披著他的大外套,匆匆轉走了出去。
可還沒走出去幾步,就聽後傳來一陣跟上來的腳步聲,而後一件西服外套就該在了的頭上,還沒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一隻大手就忽地從後抱住了的,另一隻抱住了的腰。
接著,視線一陣天旋地轉,驚呼了一聲,整個人就翻了個麵,被扛在了徐晏清的肩上。
腳步微顛,腹部頂在他寬直的肩上,視線裏是是他寬闊直的脊背,心髒在腔撲通撲通直跳。
反應過來後,氣急敗壞地了聲他的名字:“徐晏清!”
扛著他的人回應了:“嗯。”
抬起拳頭捶了一下他的腰:“你放我下來!”
拳頭落在了他腰側,他斜了下子,聲音從前頭傳來:“腎在這,換個地方捶,捶出個好歹來,最後影響的是你自個兒的生活質量。”
這話一出,祁願的臉立刻紅出了天際,又在他腰上狠狠掐了一把。
徐晏清了腰:“嘶。”了一聲,但也沒把人放下來,就這樣給扛了出去。
*
小江原本坐在車裏等的,遠遠的就看見徐晏清扛著祁願從酒店裏走出來,他的西服外套下來,蓋在的頭上,長長的大將裹得嚴嚴實實,隻出一雙穿著高跟鞋的腳。
許多未收到邀請的,聚集在門外,眼看著還沒到活結束的時間,就有人出來了,還是這麽曖昧的姿勢,立馬拿著相機聚集了過去。
長長的紅毯臺階上,他扛著一步步順階而下,隔離帶兩邊,閃燈“哢哢”閃不停。
小江愣了愣,趕忙啟車子,開去了路邊,而後又匆匆下車,為兩人打開了後座的門。
徐晏清走到車旁,彎下腰,先將祁願塞了進去,而後才跟著彎腰坐進了車裏。
車門“嘭”的一聲關上,將後的閃燈,與問詢聲都隔絕在了門外。
祁願這才從他的層層服下掙紮出來,看了眼後視鏡裏還拿著相機對著這邊“哢哢”拍不停的記者。
斜了他一眼:“你等著明天上頭條吧。”
徐晏清也轉頭看了一眼,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樣,撇著角點了點頭:“我不是幾乎每天都在頭條上晃悠嘛!”
“……”
那倒也是,財經頭條上但凡哪天看不見他的影了,那才奇了怪了。
祁願抬起手理了理糟糟的頭發,將他的西服外套和大外一起丟給了他,反譏道:“娛樂頭條!”
反正沒臉,毫不慌。
然而,沒想到的是,他一本正經地點了點頭,說了聲:“嗯,標題我都想好了,徐氏集團CEO深夜扛一不知名星上車。”
“……”
“我覺得這花邊新聞不錯的,畢竟大家懷疑了很多年我的取向,證明一下也好。”
“……”
就淮江四個家族裏的公子爺,除了徐晏清,幾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地傳出過桃緋聞。
從徐晏清從國外回來一直到現在,滿打滿算也有七年,中間除了宣布了個和趙家的婚約,但卻也是一直拖著沒辦婚禮。
且不說淮江這些太子爺們的份,是一個正常的正直氣方剛年紀的男人,也不至於至此,私生活幹淨的有些過分。
於是有不人推測,他是不是對人不興趣,曾經甚至還有人po出了一張他和路闊兩人勾肩搭背從會所出來的照片。
還配了個十分曖昧的標題。
他幾乎黑著臉看完了那個營銷號的所有推測,甚至連“同人”這樣的詞兒都用上了。
後來,第二天,那個營銷號就徹底消失在了大眾的視野,可卻連帶著他一連好幾個星期看見路闊都來氣。
祁願看了旁的人一眼,最終選擇閉,轉頭看向了另一邊窗外,皮子這方麵的功夫,幾年前就說不過他,這幾年下來,依舊沒啥長進。
徐晏清笑著看了一眼,可手機卻在此時忽然響了起來,他拿起來看了一眼,角的笑意瞬間頓住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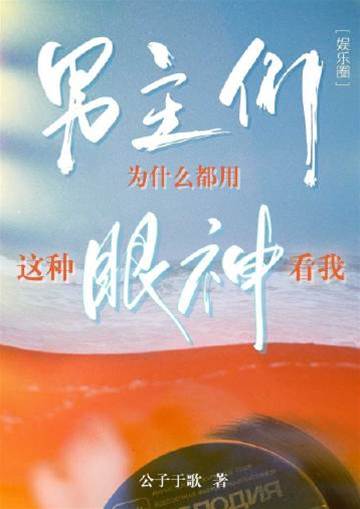
男主們為什麼都用這種眼神看我[娛樂圈]
翟星辰穿進了一篇豪門戀愛綜藝文里,嘉賓配置堪稱戀綜天花板。一號男嘉賓,惡名赫赫,死氣沉沉,所有人都要繞著他走,平生只對金融數據感興趣,偏偏一張臉帥絕人寰,漫不經心地一笑,便能叫人臉紅心跳,行走的衣架子,未來商業帝國掌權人,銀行卡隨便刷的那一…
75.6萬字8 10926 -
完結1165 章

影帝影后今天又撒糖了
蘇夏是娛樂圈衆所周知的頂級流量,更是家喻戶曉衆星捧月的爆劇女王,手握多項含金量極高的獎杯的影後。 出道五年沒有任何的绯聞,唯壹讓衆人驚掉下巴的事情就是被爆出來她竟然是影帝陸景堯的迷妹! 所有人都感歎原來就連影後都在追星。 直到有壹天,蘇夏去參加了壹個綜藝節目,被主持人問到這輩子最幸運的壹件事情是什麽。 她歪了歪腦袋,笑的很甜:“那大概是我和我的愛豆在壹起了吧。” 驚天大瓜頓時震驚了所有的網友。 後來,狗仔拍到了那個禁欲高冷的影帝壹臉寵溺的喂著他的小姑娘吃著冰泣淋。 再後來... 網友冷漠臉:請影帝影後克制壹點,狗糧我實在是撐的吃不下去了!
124.9萬字8 42563 -
完結615 章

替嫁前妻:總裁寵上天
一場為還養育之恩的替嫁,換來的是愛人的憎恨,姐姐的算計,父母的拋棄和陷害。當她涅磐重生再度歸來,卻依舊逃不開命運的輪盤。沈離夏:薄亦琛你為什麼要纏著我?我們已經結束了!他卻大手一攬,直接將她抱進懷里:我們之間,輪不到你來說結束!那你還要怎麼…
108.1萬字8 84898 -
連載774 章
重生六零:我帶著空間打臉暴富
末世滿級異能強者風凌語為救蒼生選擇與喪屍王同歸於盡,一朝重生,攜滿級異能重生於年代孤女身上。 什麼?這個年代食物匱乏,人們縮衣節食,看我滿級空間異能如何瀟灑度日! 什麼?有人想要我性命,看我末世女王如何扭轉乾坤,揪出幕後黑手! 為了安穩度日,風凌語選擇下鄉,誰知竟在這裏遇到那個他! 素手纖纖,攪亂風雲,看末世女王風凌語如何一步步找出真相,攜手愛人和小包子在這個特殊的年代綻放出末世女王的風采!
127.7萬字8.33 84952 -
連載312 章

他比夜色溫柔
渣未婚夫劈腿親妹,葉歲扭頭睡了渣男他舅。秦遲晏掐著她的腰,冷笑,“敢算計我?胸不大心倒是不小!” 葉歲聳肩,“小舅若是看不上我,我換下一個。” 秦遲晏卻緊抓她不放,“你敢!” …… 私情曝光後,所有人搓著手看好戲,等著葉歲被踹。結果,卻等到她被那天之驕子的男人嬌寵上天。葉歲以為和秦遲晏只是逢場作戲,各取所需,卻沒想到早已跌進他織的網中…
53.7萬字8 8837 -
完結412 章

被糙漢大叔掐腰爆寵99次後,我多胎了
【先婚後愛】【甜寵】【閃婚】【團寵】為救母,清潔工溫馨用彩禮十萬把自己嫁給一個陌生男人,當天領證了。他是堂堂總裁,卻扮醜扮窮,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就來領證。都說防火防盜防閨蜜,可她天天就防他。“喂!女人,吃了臭豆腐必須刷牙!”“喂!女人,馬桶用了要消毒呀!”有人說,總裁大人一表人才,不近女色,是南城所有女人的夢中情人。而她說,他粗狂醜陋,又窮又悶騷直到真相大白……天,溫馨,你家老公的胡子飛了!天,溫馨,你家老公臉上的刀疤移位了!天,溫馨你家老公開的竟然是邁巴赫!天,你家老公不是助理,他才是總裁!溫馨看著人群中簇擁的俊美男人,攥緊拳頭……
76.6萬字8.18 232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