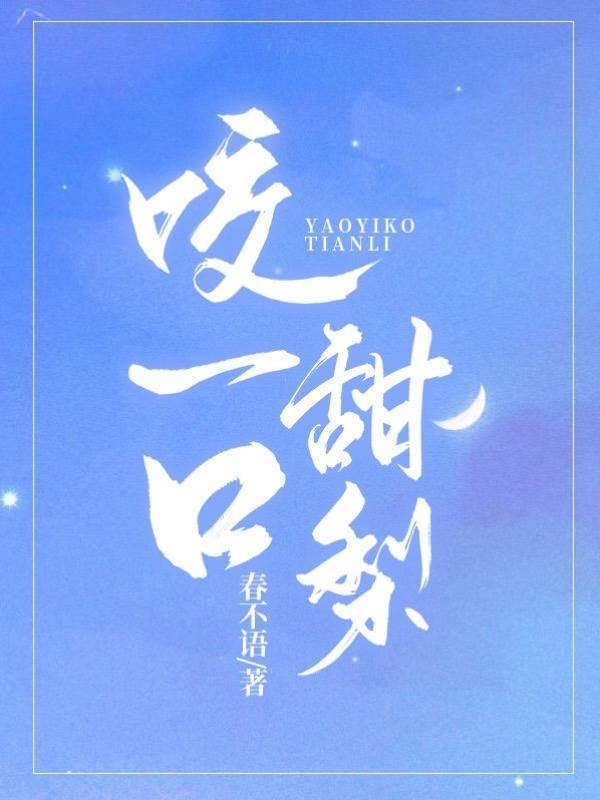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慣寵溫軟》 第151章 明示他
直到天快亮的時候,聞彥川才把溫漫哄睡著。
蜷在聞彥川的懷里,一雙手抓著他腰間的布料,使勁地往他上。
聞彥川稍一子,溫漫就睜開眼哼唧著要上來,屋空調的氣溫偏高,聞彥川脖頸上都滲出一層細汗。
他就那麼一下下地拍著的后背,像從前哄小喬睡時一樣安著溫漫。
海藻般的長卷發散著,聞彥川在指尖捻著,又將手穿到發間,著每一縷發都從指間穿過。
溫漫擁著他,將整個人都在他的前,聞彥川抱住的肩膀,灼熱的吻落在肩頭,只是將扣在懷里,聽著勻稱的呼吸。
聞彥川難得陪著睡個一天懶覺,再次醒來時,早已是華燈初上。
溫漫睡了一整天,渾酸痛的要命。抓著聞彥川的手臂不肯松,一直抱在懷里。
沉穩,有力,給足了安全。
浴室里的水聲嘩嘩作響,聞彥川站在臺,將窗戶拉開一條隙,手搭在窗口,兩指夾著燃了一半的香煙。
臺水晶花瓶中的戴安娜開的艷麗,秋風吹過,花瓣細微地劃過聞彥川挽起的襯衫袖口上,沾染了一玫瑰香。
聞彥川面平常,一手舉著電話,語氣淡淡:“去問一下當天頒獎典禮的地址,找管理員備案要下當天的監控視頻,直接拿去告。”
電話那頭的秦晝一頓,沒有多問,只回了一句:“還用手下留嗎?”
聞彥川捻了香煙,將窗戶重新拉上,隔絕了風聲,周圍都靜謐下來。
“留什麼?”
聞彥川說:“打司錘死他。”
后的浴室響起一陣窸窣聲,在門被拉開的那一瞬間,聞彥川結束了通話。
溫漫只裹著一件浴巾走出來,連發頂的頭發都未沾。
走到聞彥川后環抱住他,輕聲詢問:“在做什麼?”
聞彥川點了點一旁的戴安娜:“玫瑰養的不錯。”
溫漫著他的背脊,語氣里撒意味十足:“你把我養的也不錯。”
聞彥川回過神抱住的腰,輕笑出聲。他一頓,低頭了溫漫的頭發:“沒洗?”
“手沾不了水。”
溫漫抬起手在聞彥川面前展示著手上纏繞著的紗布,又順著他的肩頭攀上去,著他的背。
聞彥川單手勾著的腰,迫使踮起腳來對著自己,幾乎要將整個人抱起。
他挲著下頜的,像是逗小狗:“暗示我?”
溫漫著他,湊近他,微微啟,包裹住他的耳垂。
呼吸熱灑,呼出氣音:“在明示你。”
客廳一片昏暗,只有浴室的燈明亮照映,過那層玻璃,在地板上留下斑斑影。
浴巾落地,曼妙都顯在影之下。
聞彥川看著地上的影子,凹凸有致,長發也隨著作微微飄。
他勾著的腰,呼吸沉重。
沒有了任何阻擋,他糲的指尖劃過細/,雙眸也在一瞬間到灼熱。
他子擋住了,將隔絕在窗前。子半彎一個弧度,還在輕/咬著的肩。
“不怕被看到?”
聞彥川單手將一整個托起掛在上,另一只手則是在山水中作畫,描繪的濃墨重彩。
攀著他的肩,任由他抱著自己走進影中。
……
小寧在接到秦晝的電話時,外面的天已經完全黑了。
秦晝問了電影頒獎典禮的地址,小寧照答,說完了才想起來問:“要地址做什麼?”
秦晝實話實說:“老板要拿當晚的監控視頻告溫小姐的前男友。”
小寧‘哦’了一聲,又補了一句:“在會展正門停車場側面的巷子口,旁邊有棵大槐樹,應該正對著路口監控,別找錯了。”
秦晝默然,默默記下了地址后又問:“那天發生了什麼?”
小寧回憶著當晚的形,嘆一句。
“那真是一個,無比兇險又值得紀念的夜晚啊。”
燒烤店門外的大棚遮傘下擺著幾張小餐桌,紅的塑料板凳腳下還殘缺著幾個碎渣,周圍滿是嘈雜聲,一旁的紅塑料桶上扎滿了木簽。
小寧坐在桌子前,面前擺著幾個鐵盤,一手還拿著玻璃瓶的北冰洋大快朵頤。
“那天晚上,江瑾突然找了過來,我還在車上等著溫姐,誰知電話里突然傳來劇烈的嘶吼聲——”
小寧掐著嗓子,學著溫漫當時的語氣:“滾開!別我!”
秦晝坐在的對面,一深灰筆西裝與眼下的景象格格不,他端坐在紅的塑料登上著背脊,手里還拿著一杯咖啡。
他點頭,隨聲附和:“嗯,你繼續說。”
后桌的食客時不時投來打量的目,轉頭時里還嘟囔著:“誰吃燒烤喝咖啡啊,真裝x!”
小寧擼著串兒,芝麻辣椒蹭了一臉,講的繪聲繪:“我當時立馬拉開車門往回跑!你知道那段路離巷子有多遠嗎?還好我平時跟在溫姐邊力好,這要換一個人,還真不一定跑的那麼快!”
小寧說完,還肯定自己似的點了下頭,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也沒停。
“我當時一到場,江瑾那孫子正捂著腦袋呢,我都嚇壞了!你不知道,溫姐當時手里拿著獎杯,純玻璃啊,那得多厚重?一下就砸過去了!我以為給江瑾開瓢了!”
秦晝聽到這的時候,眉頭微微一皺。
他大概想得到當時的況。
小寧一手拿著串,像是想起了什麼,仰頭大口大口地灌著北冰洋。
玻璃瓶空了,反手握住瓶子,對著秦晝指了過去。
作太快,秦晝一怔,猛地子向后仰。塑料凳哪來的背靠,秦晝的子向后栽去,險些摔倒。
小寧連忙擺了擺手:“別怕,我只是示范給你看。”
秦晝頓了頓,表有些一言難盡:“可以理解。”
小寧點頭,換了個方向指著手里的玻璃瓶:“我上前趕拉著溫姐要跑,江瑾還想跟著我們,我當時就這樣,我就這麼指著他。”
小寧一頓,轉頭又對著燒烤店屋里喊了一句:“老板!再來二十串牛油!”
說完,又正起來:“我說你別過來啊!我們的人都在后面!你敢來我就喊人了!”
學完這一切,小寧才放下瓶子,對著秦晝抬了抬下:“怎麼樣,是不是很英勇,很值得紀念?”
秦晝抿,目在眼前空的鐵盤中掃了一眼。
他頷首,對小寧給予了肯定。
“對于你那天晚上的表現,組織對你表示肯定,但對于你今晚的飯量,組織對你表示震驚。”
秦晝看了一眼小寧,言又止。
“這件事你做的不錯,我可以向聞總請示找你們公司的老何提議給你升職加薪,總不至于讓你吃不飽飯。”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3162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6179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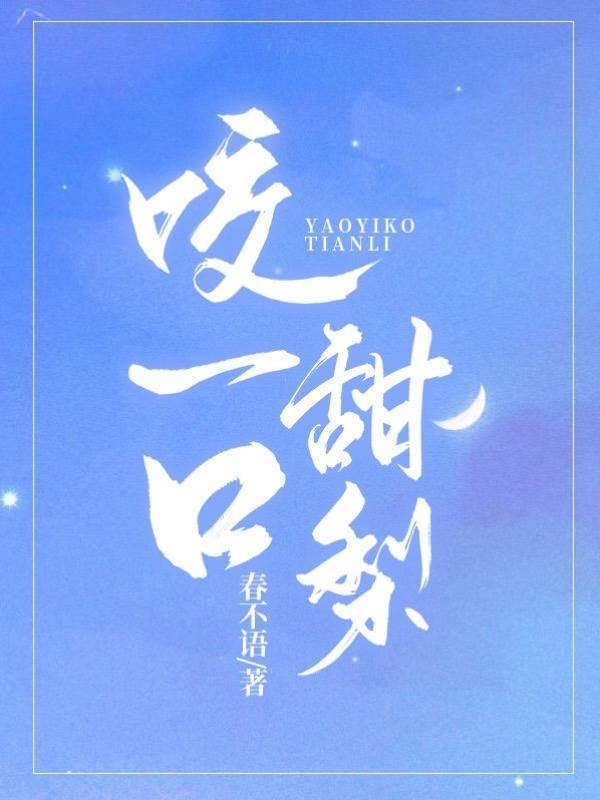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