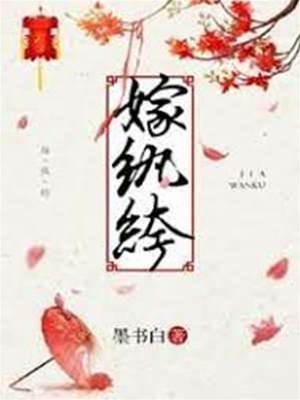《金吾不禁,長夜未明》 第81章 第 81 章
三人如愿進了城。
張行簡沒有鬧騰, 楊肅和沈青梧扮夫妻,三人用假的份進城。
原本沈青梧和楊肅都做好準備,隨時準備被發現, 準備開打。但是城門前的軍士稀稀拉拉, 查得并不嚴謹。
張行簡與他們打聽,含笑著:“上個月我剛來過這里, 那時候守城的有十來人,怎麼今天各位爺, 只出了四五個人?”
沈青梧心想:他上個月怎麼可能出東京?
張月鹿的,騙人的鬼。
那守城兵被調來看城門,心不太好,回答得很嘲諷:“有門路的都去結上峰, 去干油水大的事了。誰來守城?”
張行簡裝著天真:“但我最近聽說,帝被刺,朝廷把東京都封了,什麼張家沈家都封了起來……說是沈家出了什麼刺客,向天下通緝……”
他說這話時,目頓了頓。
同時,那在前面在一起的楊肅二人,也站在“通緝令”前, 著通緝令上所畫的子畫像。
楊肅震驚:“這是……沈青梧?”
他看自己旁那個穿上裝后段風流窈窕的子, 再看看通緝令上那個被畫的五大三的“沈青梧”。
繪圖的人明明知道沈青梧是子。
繪圖的人卻想象不出來子怎麼能在千軍萬馬中刺殺帝。
于是, 結果是——通緝令上的沈青梧,滿面橫,眼神兇悍, 鼻都更像威武不屈的男兒郎, 而非子相, 更和真正的沈青梧模樣相去甚遠。
楊肅放下心:按照這通緝令抓人,那恐怕對方十年也找不到人。
楊肅奇怪:“縱使繪圖的人不認識沈青梧,難道朝廷中認識沈青梧的人也沒有嗎?還有沈家……”
沈青梧:“也許他們都瞧不上沈青梧,本沒正眼看過沈青梧。在他們眼中,沈青梧是什麼妖魔鬼怪的樣子,也無所謂。”
張行簡已經打聽完自己想知道的訊息,走到他二人后,聽到沈青梧的評價。
張行簡溫和笑一笑:“朝廷不是誰的一言堂。有人想找出沈青梧,有人想先救帝,有人不想找出沈青梧。這就是造如今結果的原因。”
楊肅詫異,扭頭看他:“朝廷不是你……不是張三郎說了算嗎?”
張行簡:“他不是不在嗎?而且,朝廷上下憑什麼完全聽張月鹿的呢?他只是宰相,連帝的話,都不能讓人完全信服。”
楊肅:“無論如何,帝恐怕活不咯。”
他語氣開懷。
只要帝死,他們這趟任務就完了!
張行簡平靜:“不一定。我方才打聽到,四方有些本事的大夫、醫者,都被兵們押往東京,為帝看傷。守城士兵們惶惶不安,出一個訊息——要麼,帝已死,但被人封了消息;要麼,帝還未死,尚有一口氣在,等著被救。
“看這城下兵寥寥,全去押送大夫的跡象……我認為后者的可能更大。”
楊肅和沈青梧對視一眼。
不能讓大夫們去東京。
沈青梧問張行簡:“我們不是來看大夫嗎?這城中最厲害的大夫,是誰啊?”
張行簡:“容我問一問。”
沈青梧和楊肅二人去跟百姓打聽消息,主要是楊肅問,沈青梧聽;張行簡去找他的當鋪,拿最新的消息。
半個時辰后,三人站在一家“明善堂”前,門口“神醫在世”的牌匾已被摘掉,堂里堂外排滿隊,皆是找大夫看病的人。
他們在人群中聽百姓抱怨:原來的神醫被兵們帶走了,現在治病的人是神醫的兒子。神醫兒子遠不如神醫,但是神醫兒子去府求了好多次,說他爹年紀大了,經不得奔波,
被府打了出來。
百姓們的討論聲很小,生怕被府巡邏人聽到。
但話里話外,不滿緒分外真實。
有人說:“那個皇帝從他執政開始,就沒做過一件好事,我家莊稼還被征走,要給他蓋別院……干什麼要救他?
“我看那個刺客,殺得好!”
也有人擔憂:“話不能這麼說,這皇帝這麼年輕就死了,誰當皇帝啊?聽說他們這一代皇室,都沒幾個苗子……這要是隨便弄一個皇帝,還不如現在的,怎麼辦?”
“要是再回到帝姬霍朝綱的時候,也不好啊。”
有人問:“聽他們說帝姬霍朝綱,但是帝姬做了什麼事,怎麼霍的,也沒人知道啊。反正我們家在前年的時候還能吃口飯,現在家里一堆病人,看個病還得千里迢迢來這里……過兩天,估計排隊都等不到大夫。”
在這排隊的,皆是病人、病人家屬,說到傷心,各個掩袖垂淚,哽咽連連。
有人道:“聽說帝姬從益州開始分了大周,不知道南邊會不會好一些啊?”
“別做夢了!重兵把守,還要渡河呢……誰敢去南邊呢?”
“那、那我也想試一試!這皇帝要是不死,活過來了,不知道又會想出什麼主意折騰我們……”
“哎,可我那在縣衙當雜役的表舅說,搞不好咱們要跟南邊打仗啊。”
于是所有人一同發愁,所有人唉聲嘆氣。
沈青梧三人沉默地聽著,并未說話。
有府巡邏人過來,走到“明善堂”前,說閑話的百姓們連忙閉。這些兵在堂前巡邏一圈,進去堂,等在外的百姓們長脖子,聽到里面兵的厲喝聲:
“明天收拾收拾,一塊準備去東京吧。”
等在外的人面面相覷,開始發愁神醫兒子若也走了,誰給他們看病呢?
大約帝的命,與他們的命,標清價值,全然不同吧。
到中午時,沈青梧三人終于踏進了“明善堂”。
楊肅熱笑,摟著沈青梧肩:“大夫,快幫我夫人看看病。我們到找不到大夫,全靠你了。”
那堂前大夫是一個中年國字臉男人,下一圈包養得油的胡須。大夫眼角下垂,看著十分沒神。
他沒打采地招呼沈青梧坐下,搭脈前,他嘟囔一句:“找不到大夫是正常的。一個個都要從咱們城外那條道上進東京,再厲害的大夫,也都在府那里咯。你們想見到,也難。”
楊肅驚訝,做出為難狀:“就是說,城里其實有很多大夫,但我們見不到?幸好還有您……”
大夫白他一眼:“明天我也不一定在了!我爹被兵帶走,要去東京。我想了想,我也跟著一起去,照顧我爹吧。我爹那麼大年紀,哪里經得起這種折騰?”
楊肅:“從南往北的大夫,都要經過這里啊……”
他看了張行簡一眼。
張行簡選擇的城鎮,位置實在太巧妙了。
大夫看他們三人一眼,尤其是楊肅看張行簡的那一眼復雜緒。
大夫:“……”
他眼角了。
行醫多年,看多了奇怪的病人們,這家的奇葩關系,他在三人進來時就覺得微妙了。
年輕漂亮的夫人與俊俏笑的年輕郎君,看起來十分和諧養眼,恩非常。然而,這位夫君待自家夫人是熱了,夫人的態度卻是冷冷淡淡的,甚至沒有多看自己夫君一眼。
毫無婦人該有的規矩。
從進門一刻起,楊肅像個殷勤小婦,攙扶著沈青梧。楊肅拉凳子還要灰,跟大夫搭話,給大夫倒茶。這般忙活,換來的,是他夫人一言不發,冷眼旁觀。
這家婦人真是……目無尊卑,不將自己夫君放在眼中!
可若是再看一看他們后那個賬房先生……大夫目收,略微迷惘。
一文士袍,形修長,斯文而雅致。最絕的……是那張臉。
賬房先生從進門開始,并沒說什麼話,卻目若有若無地追隨著夫人;夫人沒說話,不看任何人;只有丈夫一人忙活。
大夫手搭在沈青梧脈搏上,心驚了一驚:該不會是這家夫人和賬房先生搞出了什麼事,丈夫忍辱負重,太自家夫人,出門來帶夫人看病吧?
再聯系楊肅說到找大夫,這夫人看著面還算正常……大夫手抖一下。
他默想:不會是鬧出孩子,想要流了吧?
他這是正經醫館,不做這種事!
大夫心中有了猜測,便直接去探查沈青梧是否懷孕。
大夫將脈搏撥了又撥,奇怪的:“咦?”
張行簡此時開口:“大夫,的病很嚴重?”
大夫胡須:“是平脈啊……我再看看。”
三人并不知道,平脈的意思,是并未懷孕。
三人目盯著大夫。
大夫被他們看得有點心慌:“這、這……小娘子,你莫非很久前過重傷,你這脈象顯示,你很難有孕啊……”
沈青梧一怔。
楊肅和張行簡皆一怔。
這大夫在說什麼?為什麼在看沈青梧有無孕狀?
楊肅甚至還多看了張行簡一眼。
張行簡:“……”
大夫看他們表各異,便估計自己說到痛了。
人家,哪有不想要孩子的?
大夫聲安這個態度冷漠的娘子:“娘子放心,你這時間久了,經過我好好調養,也是有可能懷子的。我可能醫不到位,但是只要我們從東京回來,我爹幫你調養……”
沈青梧:“你等等。誰說我要生子?”
大夫愣住。
楊肅在此時,不敢看沈青梧發青的臉,他小聲又艱難地提醒:“大夫,我夫人是上有些傷……我們想讓你看看傷,不是來求子的。”
大夫:“……”
張行簡在后微笑。
他明明沒有笑出聲,但沈青梧仿佛有背后靈一樣,立刻目兇,扭頭瞪他。
不能生子的事被大夫說破,還被楊肅和張行簡聽到。沈青梧約覺得這不是什麼好事,這是一件短,會讓人同或讓人放棄……不想讓任何關心的人知道。
張行簡盯著眼睛,看到那幾分迷惘與怒意。
張行簡目慢慢溫。
張行簡輕聲:“夫人與爺在這邊看病,我去買點兒東西。”
楊肅低著頭不敢看沈青梧:“哦哦哦。”
那大夫也覺得尷尬。
大夫覺得尷尬的同時,在看到張行簡和沈青梧的眉來眼去后,更堅定這家夫人爬墻了。
大夫鎮定:“……哦,看傷啊,我方才看錯方向了,咳咳。但是你們雖然年輕,卻也到了生孩子的年齡,讓我爹幫你們調養……”
楊肅怕這大夫再說下去,沈青梧砸了這醫館。
楊肅快哭了:“您快看上的傷吧。我們不著急要孩子,真的!”
大夫:“知道,知道。”
這大夫看沈青梧的傷,一點點把脈,面漸漸凝重。他詫異看眼這位娘子,不知道這位娘子怎麼心肺上了那麼多損傷,還能坐在這里。
這要是尋常人,早該死了啊。
大夫來藥,自己一邊診脈,一邊說一種藥材名。
張行簡重新回來時,正見這位中年大夫著汗,
很為難地說:“以我的水平,只能開這點兒藥,你們先吃著。等我爹回來了,讓我爹再幫你重新開藥。”
楊肅:“若是我們等不到你爹回來呢?”
大夫狠狠瞪他一眼。
然而醫者父母心。
大夫道:“你們要是等不到我爹,就一直吃著我開的這副藥吧。吃個一年,中間不要怒,不要做劇烈運……一年也能養好了。”
沈青梧皺眉。
一年?
絕無可能有時間休息一年。
楊肅以同樣的想法和大夫爭論,說自己妻子活潑好,不可能不做劇烈運。楊肅問能不能加重藥量,短療養時間……
大夫氣怒:“你當我這是買賣麼?還能討價還價?”
楊肅賠笑:“您試試嘛!”
沈青梧百無聊賴地站起來,袖子垂下,等著楊肅和大夫討論出結果出來。反正,要一年不武,沒有人會同意的。
張行簡在后輕輕了腰。
沈青梧冷著臉回頭。
他低垂著眼,袖子抬起,掀起來,讓看他藏在袖中的東西。
沈青梧眼睛被日照得瞇了一下。
看到他從袖中取出一細長玉簪,靠著袖子的遮掩,不讓旁人看到,只讓看到了。
張行簡微笑:“剛剛在街上看到的,覺得有些意思,送給你,要不要?”
沈青梧心中一。
卻拒絕:“不要。”
張行簡輕笑:“真的不要?算作方才惹你生氣,給你的一個小補償禮,也不要嗎?”
沈青梧眼波晃一下。
生氣是因為自己的難堪面被張行簡知道,并不清楚張行簡和楊肅早就知道,生悶氣的原因和張行簡并無關系。張行簡卻退出醫館,給買發簪,逗開心……
他素白的手握著簪子輕晃,給展示玉簪上方的小月亮。月亮下垂著流蘇,簪上刻著樹枝藤蔓。
這簪子非常有巧思。
沈青梧心了。
盯著月亮下晃的流蘇:“月亮?你有私心吧?”
張行簡冤:“又不是我自己雕刻的,我怎麼有私心?恰巧在路邊攤看到了,正是緣分。好不好看?”
好看,是十分好看的。
張行簡的眼,從來不會出錯。這玉簪不會如他的玉佩那樣名貴,玉簪更像一種逗人開心的玩意兒……不值什麼錢,但很有趣。
沈青梧看上的,就要得到。
果斷:“多錢?我要了。”
張行簡挑眉。
抬頭,與他一同靠著墻說悄悄話:“我不會白收你的禮。我直接花錢買!”
張行簡不聲:“那我的路費,是不是也得給?”
沈青梧咬牙:“給!”
張行簡眼波華瀲滟,笑未笑。
他的眼睛漂亮十分,勾人時有如桃花噙水。
這讓沈青梧如臨大敵。
厲聲斥他:“注意你的份!”
張行簡一怔,目閃爍。
他想到如今和楊肅是夫妻,他只是賬房先生罷了。
但是……賬房先生也很有趣啊。
他收了笑,一本正經:“那請問夫人付多錢,買在下的簪子?”
他一聲“夫人”,讓沈青梧心弦一。
沈青梧怔住。
張行簡認真:“如今的住宿,不是在野間宿,就是靠在下洗碗洗盤子賺錢。在下記得,夫人無分文,可憐得很啊。”
為了不打擾楊肅和大夫爭吵的興趣,兩個人躲在墻說話。
從張行簡展示簪子開始
,二人便越靠越近,那大夫偶爾抬頭,看到一叢蘭花相擋,貌娘子與小白臉賬房先生的臉都快上了。
大夫看一眼楊肅。
傻乎乎的丈夫還在為了一點藥和自己據理力爭!
這傻丈夫再不回頭,那兩個人都快親上了。
在大夫惆悵的腹誹下,沈青梧的耳朵正一點點紅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758 章

慕紅裳
個性活潑的女大學生謝家琪抹黑下樓扔個垃圾,不小心跌下了樓,再睜開眼,她發現自己變成了右相府的嫡小姐謝淑柔;榮康郡王正妃顧儀蘭絕望自裁,一睜眼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四歲,一切都可以重頭再來。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與安國公家的小姑娘穆紅裳沒關係,紅裳怎樣都想不明白,她的人生怎地就從此天翻地覆……
123.8萬字8 6383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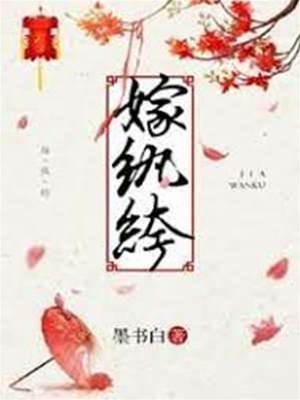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287 -
完結283 章

代嫁太子妃
簡介: 一朝穿越,她成了出身名門的官家小姐,青梅繞竹馬,卻是三人成行……陰差陽錯,定親時她的心上人卻成了未來姐夫,姐姐對幾番起落的夫家不屑一顧。她滿懷期待代姐出嫁,不但沒得到他的憐惜,反而使自己陷入一次更甚一次的屈辱之中。他肆意的把她踩在腳下,做歌姬,當舞姬,毀容,甚至親手把她送上別人的床榻……
23.2萬字8 10713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1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