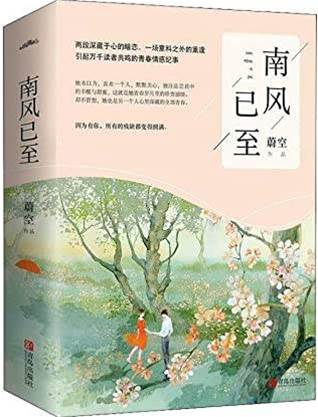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春夜纏吻》 第5頁
江檀記得很清楚,1月20日。
默默算了下日子,剛好,滿打滿算,一個月。
一個月...也夠了。
鬼使神差的,江檀起,推開臺的門,站在了周應淮側。
他在打一個國電話,法語流利,說不出的聽。
很多人都說,法語是浪漫的語言。
而周應淮,他不屬於浪漫,他是理本。
只不過是皮囊太迷,才會人不知如何是好。
周應淮掛斷電話,轉過時,看見江檀站在自己後。
他抬手,著江檀被風吹得發涼的臉,「站在這裡幹什麼?」
「看你。」
「然後?」
江檀扣住周應淮的手,踮起腳,親他的角。
「然後親你。」
純又溫。
而周應淮只是片刻的怔愣,便反扣住江檀的脖頸反客為主,和侵略如有象,慾沾染其間,難以離。
江檀卻突然推開他。
眼眶是潤的,在皎皎的夜中,波粼粼的一雙眼睛。
突然喊他的名字,「周應淮。」
「在的。」
「今年夏天遇見你,我很開心。」的聲音很輕很輕,在夜寂寥中,莫名人心口發。
「...」
周應淮看著,自己都沒有察覺,皺了皺眉。
「我知道,你給我捷徑,我陪著你,是很公平。」
江檀眨眨眼,笑得更加真切,只是聲音有些抖:「但是我不能做小三。」
「...」
「你要是結婚,我們就得分開。」
周應淮看著佯裝鎮定,卻已經紅的眼睛,剛剛的慾念散的一乾二淨。
他走向江檀,指腹輕輕過的眼尾,姿態放低,哄著:「你今天不是和我說,你想吃糖葫蘆?給你買回來了,買了一堆。」
他指了指那一整袋子的糖葫蘆。
江檀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很輕易的被扯開了話題,先是笑,之後眼淚掉下來,「那你不回我消息....」
倘若是從前,在未遇見江檀之前,周應淮自己都不會相信,他會那麼認真的去哄一個人。
他子冷漠,難以共,除了利益,不為任何人容。那些年,外界傳聞他不近是真的,但不是因為其他,只是因為,他嫌麻煩。
為了片刻的歡愉,和一個人產生關係,真是麻煩的要死。
他又實在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可是這一刻,他看著江檀沾染在自己指腹的眼淚,卻覺指腹那塊有些異樣。
他尚未來得及細想,本心已經迫使他開口,說道:「檀檀,你知道的,一般除了正事,我都是不回的。但是...你如果很難過,下次你給我發這些,我儘量都回你。」
字斟句酌,用詞嚴謹。
江檀看著周應淮步步退讓的姿態。
聽見心裡有個聲音,在說:江檀,你究竟還要什麼呢?這還不夠嗎?你未免太貪心了。
這世間的事,最怕的就是不知分寸,越界的盼。
江檀咬著糖葫蘆,選擇收回越界的步伐。
下雪這天周應淮難得休息,抱著江檀睡在床上,表很安適。
那天晚上吃過糖葫蘆之後,周應淮就讓人將江檀的東西都搬到了主臥。
周應淮說,冬天快到了,你手腳冰冷,我抱著你睡。
實在是很溫的話。
要不是有了孟彥西的提前點醒,江檀只怕是會不管不顧的陷進去。
說來,那天的糖葫蘆也實在是不算好吃。是人非,十二中門口的糖葫蘆,也早就不是江檀記憶中的味道。
江檀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那天會給周應淮發了這麼一條簡訊。
如今細細想來,大約是想要一份偏。
周應淮的偏。
多可笑啊,他連都沒有,更何況是偏。
江檀確認,只有自己見過周應淮這個樣子,認真的看著周應淮沉睡的臉。
他的睫很長,眼尾的弧度偏深,鼻樑高,薄,皮好得不像話。
江檀和周應淮之間的關係,讓不敢去他的臉,只是乖巧的端詳著。
外人喊一聲朋友,不至於就不知深淺的這麼以為了。
江檀從來不是周應淮的朋友。
直到鄭珩的電話打進來,攪了周應淮的睡眠。
鄭珩說:「應淮,帶著你的江檀出來打麻將吧!」
周應淮剛睡醒,眼神難得的,甚至能人生出關於溫的錯覺。
他看著江檀那雙乖的眼睛,著的頭髮,說:「知道了。」
江檀出門時,選了一件紅的大。
皮白,紅襯得異常明艷人,了些仙氣飄飄的覺,多了些勾人心魄的。
周應淮看著半晌,淡淡的說了句:「這件不好看,換一件。」
江檀沒多想,愣了愣說好,轉就要去換,被周應淮住。
周應淮說:「算了,我去給你找。」
江檀對於周應淮的審,還是有很高的期待的,以至於後者拿著一件鵝黃的厚重棉襖出來的時候,江檀角搐。
「你...給我找的?」
「怎麼?不好看嗎?」周應淮一本正經:「年紀輕輕的小姑娘,穿這個剛好。」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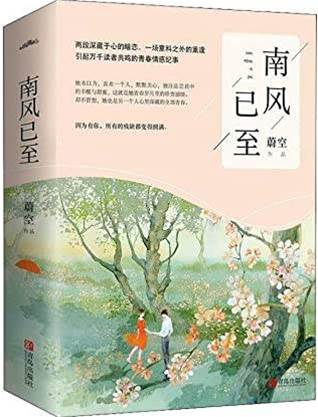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192 -
完結540 章
全球示愛少夫人
“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但愛情免談。” 蘇輕葉爽快答應,“成交。 “ 可他並沒有想到,婚後她對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 “靳先生,我想要離婚。” 男人把她抵在牆角,狠狠咬住她的唇,「想離婚? 不如先生個孩子。 ”
93.6萬字8 295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