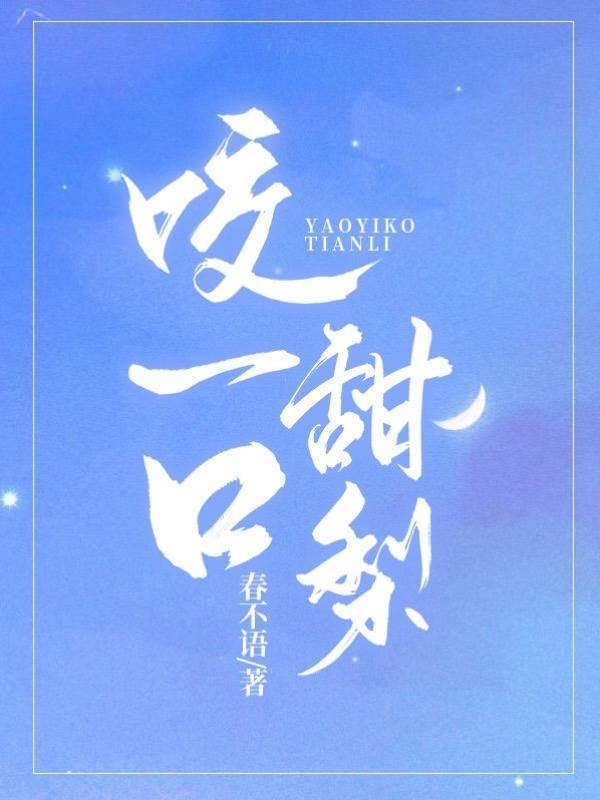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誘他撩他!禁欲大佬失控破戒》 第126章 短暫而又無比熱烈的戀愛
“翹翹,今天也在二樓食堂吃啊?”
“嗯,這里的飯還香的,而且營養搭配很均衡。”
“你真是太自律了!”
林連翹端著自己的飯盒去舞蹈團二樓專門為這些舞者們設立的食堂吃飯,認識的同事和打招呼,無一不羨慕的自律。
林連翹每天早中晚都在食堂吃飯,空閑時間要麼就是回自己的宿舍休息,沒出過舞蹈團。
每天拼了命的練舞,本就超越不人的進度如今將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這些人就算是想嫉妒,卻是騎馬也追不上的進度。
林連翹自己卷自己,們卻不想讓自己那麼累,于是們和林連翹和解了,自然也能和睦相。
被季聿白無視了將近一個星期,林連翹心早已絕,從格灣安區搬出來到宿舍之后,的手機再也沒有開過機,所有心神全都投進練舞之中。
效果顯著,就連于團長也夸贊的勤勞。
只是的能有些跟不上自己的訓練,林連翹又給自己安排了能訓練,吃的東西就要增加,食堂做的最好,控制住口腹之,也能把食堂做的菜都吃個。
這天林連翹照例去食堂吃飯,然后去做一個半小時有氧加無氧。
這些日子被季聿白寵壞了,林連翹單獨一個人吃食堂,總會想起季聿白。
他口味不刁,什麼都能吃,林連翹到現在都還記得季聿白第一次吃臭豆腐時滿臉便,一副,‘現在立刻馬上給我準備垃圾桶讓我把里東西吐出來不然我一定結果了你’的表。
看著他那副模樣都能捧腹大笑多吃半碗飯。
季聿白總會等笑完了,再把自己過的苦給也嘗一遍,出其不意喂一口帶了香菜的臭豆腐。
臭豆腐很好吃,那一片香菜差點沒要的命。
“啪嗒”
勺子里的牛跌進澄澈的湯里,濺起湯,林連翹低下頭,眼淚猝不及防地滴在餐桌上。
真是沒骨氣。
還是很想他。
林連翹了眼淚,勉強吃完了飯,去健房鍛煉。
……
舞蹈團外,和林連翹打過招呼的男男們結伴出去吃飯。
門口停著一輛邁赫,警衛員怎麼趕都趕不走,只能黑著臉站在那兒瞪車里的人。
那些舞者們一出來,當然也看到了這一輛矚目的豪車。
們每次出來都能看到它。
“又來了啊,這是誰家的家屬啊?這麼好,天天車接車送的。”
“不知道,你們要過去看看嗎?”
一行人大膽地走過去,想看看這是誰家的男朋友或者家人,竟然每天都來車接車送。
剛剛靠近,車窗降了下來。
煙味沖天。
眾人熏得往后退。
從里面探出一只蘊含著無窮力量的手臂,在車窗上。
接著,駕駛座上男人英俊卻郁的臉了出來。
有人驚呼,“你是……那次在堯城和林連翹在一起的男人?”
都是一個舞蹈團的人,之前在堯城巡演,季聿白千里追妻,有人看到們在酒店樓下親昵,自然也見過季聿白。
結伴相行的人立刻驚嘆起來,“林連翹的男朋友?”
“不會吧?林連翹最近都在舞蹈團一直都沒出來過!”
聽到這句話的季聿白沉晦暗的目終于轉,落在那些人上。
“林連翹……”他嗓音沙啞到了極點,仿佛久未睡好的窮兇熬夜分子,“一直都在舞蹈團里?”
“是啊。”
“前幾天就搬到舞蹈團了,聽說是為了過幾天的大演,單獨一個人的軸呢。”
“你不是的男朋友嗎?沒告訴你?”
“也是,要是告訴你了,你何必天天來這兒等?你是不是和林連翹吵架了啊?”
季聿白罕見的沉默,斂下的眸子里盛滿了翳。
怪不得他怎麼找人都找不著。
他給打電話不接,發信息也不回,讓晉津言,唐晝,薛文明,薛茉等等所有人都試了給打電話,林連翹卻好似人間蒸發了一樣,誰的消息都不答。
擱他這兒鬧失蹤……
他在舞蹈團前等了四天都不見林連翹出來。
他以為自己找錯了地方。
原來,從格灣安區搬出去之后就住進了舞蹈團。
季聿白滿腔怒火,想立刻把給揪出來,質問為什麼。
可手才剛剛落在車門鎖上,卻又生生停住。
質問完了之后呢?如果林連翹問他,他失蹤的那一個星期是為了什麼,他又該如何回答?
以后又要怎麼面對?
季聿白整個腦袋尚沒有完全理出一個正確的答案,邁步往舞蹈團方向走的腳就如扎了一樣,怎麼都不了。
他現在應該離開,離林連翹越遠越好,以后再也不和有任何瓜葛。
可他不想走。
想見。
發瘋一樣地想見。
……
林連翹鍛煉完之后,洗了一個澡,這才回宿舍休息。
舞者練舞的時間并不松散,中央舞蹈團的舞者練舞時間要求更是嚴苛。
不過林連翹自己加練,沒有人覺得會懶,所以林連翹在宿舍睡了一個小時的午覺之后,神抖擻到舞蹈室,也沒人覺得不對。
今天要和幾個舞者一起排練群舞《雨霖鈴》
林連翹是領舞,這個舞也是過幾天大演時會演出的曲目。
黑的舞服在一眾白之中格外顯得亮眼,加強能之后,作愈發的韌有力。
“這次排練得不錯,咱們再走兩遍,連翹,注意想象自己現在就在舞臺,臉上的表做好,我們拍一個練舞室版的,回頭做專訪時用。”
林連翹點點頭,調整了一下緒,待音樂重新響起,臉上的表便富了許多。
巧笑兮的左右顧盼,宛如采蓮娘,隔江著郎。
練舞室外,專注跳舞的林連翹并沒有注意到,窗戶旁站著左思右想的男人。
他的目仿佛黏在了林連翹上。
看著踮腳起舞,纖細韌的腰肢與每一,恰到好的搖擺。
輕歌曼舞,人間絕。
整個世界只剩下。
季聿白的目越來越深邃,越來越晦暗,里面藏著的緒比驚濤還要翻涌,比暴雨還要狂。
握的雙拳沒有松開,季聿白沉默地看著連續跳了好幾遍,笑盈盈混在人群里拿起自己的水壺,角勾起與旁人說笑。
會發一樣,無時無刻吸引注意。
似有所覺,林連翹扭頭看向窗外。
卻見那里一片空,并沒有多余的人。
排練其他舞的人來這里的舞蹈室竄門,看到林連翹便對說,“連翹,你男朋友這些天都在外面等你你知道不?”
正在休息喝水的林連翹微愣。
“你說什麼?”
“你不知道嗎?”那人驚訝了,“從你搬去宿舍之后,咱們舞蹈團外,一直都有一輛邁赫在門口,我們還想著是哪家的家屬這麼好,天天車接車送風雨無阻的。”
“沒想到是你男朋友啊,你這些天都在閉關,沒告訴你男朋友嗎?讓他一直在那兒等。”
林連翹攥手中的水杯,立刻跑了出去。
不停歇地跑到了門口,四張。
炎炎夏日,公路被炙烤的都出現了宛如水面一樣的波紋,零星幾輛車子駛過,不論哪一輛,都不是悉的。
這里沒人,空樹蔭遮掩的地方,連一輛車都沒停。
不知是跑得太快被太曬太狠而劇烈跳,還是因為不敢置信他來了而發狂律的心臟在這一刻驟然平靜下來。
苦笑一聲,原地站了片刻,就聽警衛員說,“小姑娘!你男朋友剛走沒多久!”
林連翹呆呆地過去,“他才走?”
“是啊。”警衛員很是不高興地說,“他每次就停在那兒,一待就是倆小時,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小姑娘,男朋友吵了架你哄哄他就好了,男人就這臭脾氣,犟著不如著來。”
林連翹抿著沒有說話。
那警衛員嘆氣,又道,“以前看他來送你,都高興的,直看著你走進去沒了蹤影才走,現在又在這兒天天等你,顯然是想服。”
林連翹看了一眼警衛員,問道,“真是這樣嗎?”
警衛員是四十多歲的大叔,聞言眼睛一瞪,家鄉話都飆出來了,“可不是咋滴!男人都這樣!和朋友吵架,心里已經后悔,但就是拉不下臉道歉!”
林連翹眼里多了點神采。
“去打個電話問問吧,說不定他立刻就給你道歉了呢。”
林連翹了舞,立刻撒丫子就往回跑。
回了宿舍。
把手機開機,焦急地等待了一會兒,開機畫過去,手機屏幕亮起。
大幾千的手機在亮后沒多久,竟然直接卡殼了。
不知多的電話,信息一腦的全部都沖了進來,差點把手機給沖卡。
好半天,叮叮咚咚的聲音才結束。
林連翹點開未接來電。
十分之九都是季聿白打來的。
剩下的是宜瑛,莊如真,薛茉,薛文明,唐晝等等人打來的。
林連翹那原本已經干涸的枯木在看到這些未接來電時,仿佛遭逢一場春雨,重新長出綠的枝椏,心臟撲通撲通跳。
抖著手再去看信息。
季聿白的那一欄后面標紅了不信息。
【你去哪了?】
【林連翹,你手機沒電了?】
【睡醒給我回電話。】
……
【林連翹!你如果再不接我電話,等我找到你一定弄死你!】
【你他媽還能飛出京城往外跑嗎?別讓我抓到你。】
……
【細妹,別玩了,趕回來。】
【你去港城找林阿公了?】
……
【我投降,細妹,別折磨我,給我回信息。】
【不需要你搬出去,想在格灣安區住多久都隨你。】
【有事面談,別再玩失蹤那套了。】
……
【林連翹,你心真狠。】
林連翹看完信息,心一陣陣痛。
又不扯起一個無力的笑。
心狠嗎?
要是心狠,絕不會只躲在這兒四天。
留在空全都是和季聿白回憶的格灣安區,幾乎整夜失眠,沒日沒夜都在盯著手機看他是否回消息。
季聿白冷了將近一個星期。
明明是他突然變臉把拋下,任由五臟俱焚,焦慮不安,眨眼間,在他眼中卻是狠心了。
林連翹沉默的把其他信息看完。
薛茉:【翹翹妹妹,你去哪里啦?我給你打電話你也沒接,看到我的消息記得給我回復哦,我有點擔心你的安危。】
宜瑛:【死妮子!干嘛不接電話!】
【手機沒電了記得充電,我有好多話還沒跟你說呢!】
【?林連翹,你已經和我失聯一天了你知道嗎?再不回復我要報警了!】
【翹翹你到底去哪了?別讓我擔心!】
【我這幾天休息,已經買機票回國了。】
【該死的林連翹,我已經準備坐飛機了,明天早上就到京市,你要是敢不來接我你死定了!】
宜瑛的最后一條消息斷在這里。
要坐很久的飛機,明天就到京市。
林連翹心中涌現陣陣暖流,連忙開始回宜瑛的信息。
【我沒事,最近在閉關練舞,剛剛看到你的消息,對不起,讓你擔心了qaq】
【明天早上準時到機場去接你,到時候任君罰,對不起!】
發完這些,林連翹突然又掃到一條短信。
那個陌生手機號,讓到無比惡心的人。
季畫生。
又來給發信息。
林連翹無意點開,可短信容是直接出現在屏幕的。
【你真不想知道季聿白的母親為什麼死的嗎?那個,足以讓你顛覆整個人的三觀。】
林連翹看著那一行字,只覺潘多拉魔盒距離越來越進。
沉默了許久。
季聿白一直追求他母親死亡的真相。
如果能從季畫生的里知道,幫季聿白查清楚他母親死亡的真相,也算是把欠他的都還清了吧……
將們兩人短暫而又無比熱烈的,就此畫上句號。
比限定時間來得更早的結束。
林連翹出手,按著字母,打開了那咫尺之遙的魔盒。
【我想知道。】
【今天下午五點,我在畫室等你,地址你知道的。】
林連翹眼睫抖,眼底沒有半分畏懼。
季畫生是京市小有名氣的畫家,畫風詭譎,黑灰白紅四種被他運用的淋漓盡致,吸引了不喜歡暗黑系畫風之人的喜。
他的畫室也連接著他的畫廊。
“這些都是我以前畫的,現在看來,以前還是太過稚,什麼都不懂,只覺得全世界都是灰暗的。”
季畫生親自領著林連翹參觀自己的畫廊,彎笑著,那笑容總是帶著。
“不過現在我的畫風改變了許多,就像是上次我送你的那幅畫,是不是很明亮?”
林連翹點點頭,“是。”
“你喜歡就好。”
林連翹看向他,問,“你要怎麼才愿意告訴我季聿白母親死去的真相?”
季畫生依舊帶著笑,“這麼迫不及待嗎?”
林連翹沒有接話,意思很明顯。
“好吧,那我們上樓,非常謝你愿意做我的私人模特。”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2944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5200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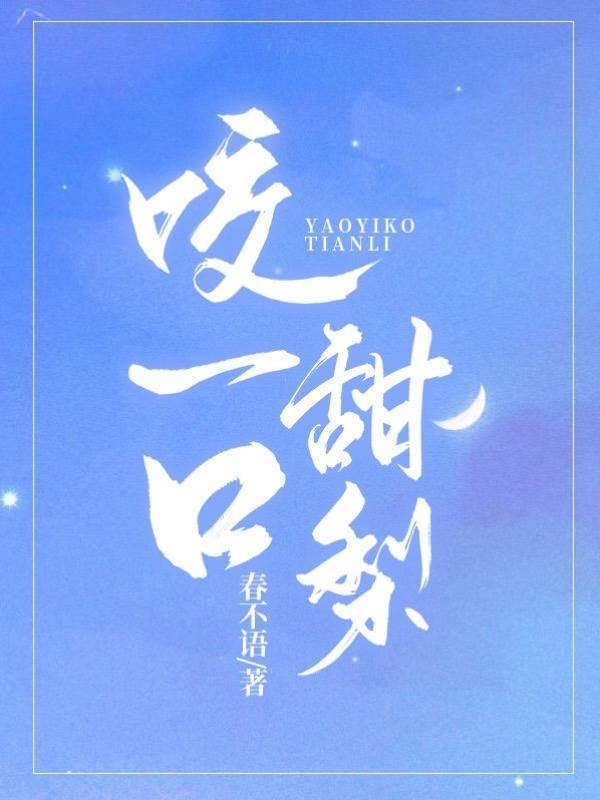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