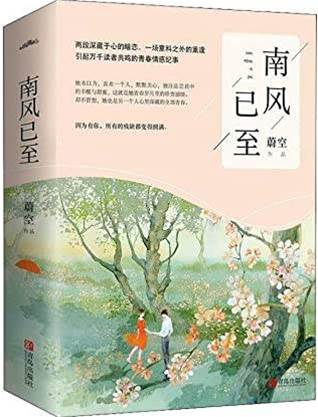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心儀》 第108頁
手就被陳燦猛的甩開。
陳燦把手一下就從他兜里出來,并且迅速且敏捷的跳離了他半米遠。
周放震驚了。
甚至懷疑之前走不穩路全他媽是裝的。
周放順著陳燦的視線往前看。
隔著池水能看見長輩在前庭忙碌的影。
他臉一下就黑下來,看向陳燦,冷聲道:“你搞什麼?”
陳燦是條件反手跳開,見他生氣了,又連忙靠回來。
這幾天顧著想他和想一些七八糟的事,完全沒想過這一茬。
在紀、外婆、還有顧姨姨周叔叔心里,不就把他們倆當親兄妹一樣。
這、這這大過年的,又這樣毫無征兆。
小心翼翼的對周放說:“我不是…就、我們、我們就這麼牽著進去,不太好……”
察覺到周放的臉更臭了,連忙解釋:“我不是說我們在一起不好,只是,還是慢慢來,這樣嚇到紀了,不好……”
周放的眼越來越涼,陳燦解釋的聲音也越來越小。
到后來也是覺得自己沒理,昨晚哭著鬧著確認關系的是,今早甩開他手的也是,說著說著聲音幾乎小到沒有了。
“我和你在一起,明正大,有什麼好躲的。”
說完他拽回的手,就要過橋進前庭。
“話——話不是這麼說”
陳燦怕他發火不敢過分掙扎,只能拖著步子,試圖在言語上勸回他,“你瞧你說的,這、這不是躲,只是暫時給個緩沖——唉——你別走那麼快,我——”
眼見著離前廳越來越近,陳燦連假笑都笑不出來了。
“你不是認真的吧,哥,這可不是小事。”
周放停下腳步,他下頜線繃著,渾的氣場都散發著不爽,看上去隨時要發怒。
他咬牙切齒:“你最好配合一點,別我進去親你。”
說完他拽著進了前廳。
陳燦是一個踉蹌絆進來的,他們剛進前廳時,實在沒有一曖昧的氣氛。
反倒像是周放把拎著甩進來一樣。
顧月都差點要出聲教訓周放。
直到看見他們牽在一起的手。
還有陳燦在滿屋子長輩的注視下逐漸紅的臉。
萬籟俱寂中,周放牽著施施然落座。
陳燦認命的扯出一笑,“紀、外婆、顧姨姨、周叔叔新年好。”
聲音還算平靜,就是手心細細的發著。
過了兩秒。
周放老大爺一樣的屈指敲了敲桌面,“都說話啊,人都被你們嚇到了。”
紀年臉上洋溢著笑,皺紋折的整張臉都是,又好似想到了什麼,表努力嚴肅下來,指著周放罵道:“禽!”
周放:“……”
顧月剛想說你什麼姨就媽得了,聞言立馬轉了口氣,指責道:“嘖,禽,虧你下了的手。”
周放:“……”
陳燦:“不是的,是……”
紀年打斷了的話:“嘖嘖嘖!今天真高興,周放你去后院酒窖里頭拿上幾瓶酒來,拿最里頭的!”
“燦燦,等會吃完飯你來紀屋,我有件嫁妝,太合適你了……”
顧月也湊近,“唉你這戒指誰送的,哎呦,好丑……”
陳燦一一應著,百忙之中還關切的看了一眼周放。
周放冷笑一聲。
心想,不用管我,你們開心就好。
-
吃完飯后。
他們去了前廳喝茶。
留下陳燦和劉邀月一起收拾正廳,陳燦把碗筷壘好,端去廚房。
“外婆,”輕喊了一聲,劉邀月回頭。
劉邀月年時也是高門大戶的小姐,之后后來家道中落,才有世周家養長大。
舉手投足間都是歲月沉淀后的風雅。
劉邀月笑了笑,是典型的江南人,皺紋和白發也掩蓋不住的貌,笑的時候格外溫:“怎麼?”
陳燦抿了抿,沒好意思說話,劉邀月了然笑笑。
和紀年從小一塊長大,后來兩人的丈夫相繼離世后,就一直在這諾大的驟園里頭相伴著生活。
才算是從小看著周放長大的。
對于周放,對于周家,再放心不過了。
拍了拍陳燦的手,“阿放這孩子,外婆放心。”
-
這頭回廊。
周放慢悠悠推著紀年。
紀年意有所指的說:“我覺得吧,我還能活多年的。”
“是。”
紀年見他不接茬,又裝模作樣的嘆了聲氣:“唉,燦燦這丫頭,我總覺才那麼點大,才十來歲。”
周放:“……您想說什麼?”
紀年輕咳了一聲:“我覺得你最好不要太早當一個畜生。”
周放笑了。
敢這老太太還能換位思考的。
之前他沒追上的時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要抱曾孫子。
張口閉口就是一句“你要等我死了再生?”
現下追上了。
又突然站到方那邊去了,了方的,覺得自己的孫兒太小可不能這麼早被這男的禍害了。
又說自己還能活多年的。
紀年見他不回話。
又想起陳燦昨晚被灌的醉醺醺的和今早的表現。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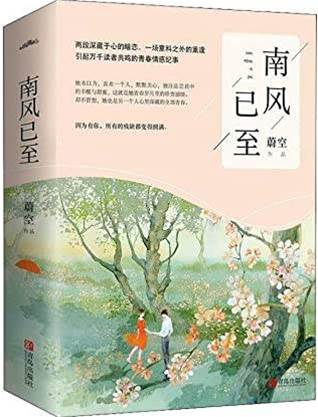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192 -
完結540 章
全球示愛少夫人
“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但愛情免談。” 蘇輕葉爽快答應,“成交。 “ 可他並沒有想到,婚後她對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 “靳先生,我想要離婚。” 男人把她抵在牆角,狠狠咬住她的唇,「想離婚? 不如先生個孩子。 ”
93.6萬字8 295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