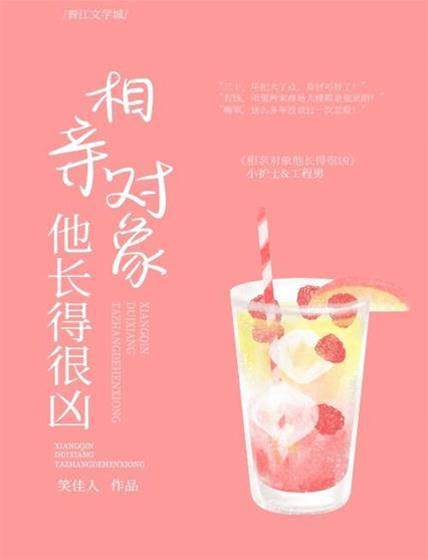《穿成反派的炮灰前妻》 第六十九章
慕行風本就帶著病態蒼白的臉,在這一瞬間似乎又白了幾分,但他只道了句:「在山上跟著我這麼多年,醫還是個半吊子。別說話了,保存力。」
他上前一步,竹節般修長的手指搭上衛的腕兒。
衛臉灰暗:「我的,我知道……」
「孩子還在。」慕行風應著那微弱的脈搏,面上浮起喜悅神。
衛原本毫無生氣的眼眸里似乎一下子有了亮,不過很快又暗淡下去了。
韓君燁聽到這句也愣愣看著衛的肚子。
林初大喜過,之前聽到趙婆子那般說,又見衛出嚴重,真以為孩子已經沒了。
慕行風看向燕明戈:「用力穩住心脈,我來施針。」
葛洄把從馬車裡帶過來的藥箱放到了旁邊的紅漆木桌上,慕行風打開藥箱,取出裝銀針的針盒,又人備了筆墨,筆走龍蛇寫下一張藥方:「讓廚房把葯煎出來!」
林初接過方子,雖然不喜慕行風,但這關係到衛的命,林初當即拿著藥方就準備往外跑。
卻聽衛道:「等等。」
林初朝著床榻看去,只見衛臉蒼白,卻是罕見的倔強決絕。
看著慕行風:「我不用你救。」
「阿,別鬧。」慕行風面薄怒。
燕明戈也攏著眉心看著衛。
衛眼神放得很空,像是早已看這一場人世:「不是鬧……我不願欠你。」
慕行風目死死絞著衛的視線,不願欠他,是想就此跟他再無瓜葛嗎?
他勉強出一抹笑:「阿,哪怕是為了孩子……讓我先給你施針好不好?等你好了,你說什麼我都認了。」
他這一生,清貴高傲,從來沒在任何人面前說過一句話,唯有在面前,才放下所有驕傲。
「孩子……」衛著小腹,緩緩閉上眼:「就當我欠這孩子一條命,黃泉路我陪走便是。」
「師姐!你別衝!」林初真怕衛一心尋死,語無倫次道:「你不要他救,我們找別的大夫好不好!不管怎麼樣,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衛虛弱搖搖頭:「這孩子命苦,投胎到了我肚子里,幾近波折,已經傷了本,哪怕能出生,將來也得病痛折磨,一輩子泡在藥罐子里,與其讓來人世遭這一趟罪……我願跟一起去了。這世上……我已沒有什麼可留的。」
「我說了,我能救!」慕行風看著衛,一字一頓道:「我不會讓這孩子有事,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
衛似乎想說什麼,小腹那裡的痛意卻猛然變得劇烈起來,五指用力抓了下的床褥,手背青筋綳起,五也痛的扭曲。
「阿!」慕行風心魂震,他一把起銀針盒踉蹌著撲到床前,一邊哆哆嗦嗦取出銀針一邊沖著燕明戈大吼:「愣著做什麼,快些給輸送力!」
衛痛得冷汗連連,頭髮都被汗水沾凌在臉上,仍斷斷續續道:「慕……慕行風,我不欠……不欠你……」
慕行風只覺得一分一秒對他而言都是煎熬,他猩紅著眼道:「衛,如果你說這些扎我心窩子的話,能讓你痛快些,那你便繼續說。」
幾枚銀針扎在衛上幾大,腹部的劇痛緩和了些,卻依然呼吸都極其艱難。
林初幫忙扶起衛,燕明戈坐到後輸送力,很快眉頭就皺了起來:「一心求死,力輸過去,那邊沒有接引,真氣全都散了。」
林初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哽咽道:「師姐!你當真就要這樣舍下我們嗎!」
慕行風著銀針的手抑制不住的發抖,他那雙素來淡漠的眼中,終於出現了名為潰敗絕的東西:「衛,你不欠我,是我欠了你!是我欠了你!讓我救你,從此我們兩不相欠,再無瓜葛……」
最後八個字,他嗓音低啞得厲害。
衛艱難笑了兩聲:「你救我,只是想要我腹中這個孩子罷。」
慕行風只覺得渾的都朝著自己頭部涌去,腔的怒火讓他恨不能將手邊一切能砸的都砸個碎,他咬牙切齒道:「如果可以,我真想把它摔一堆沫讓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為了它!」
衛緩緩道:「那你立誓,絕不認我腹中這個孩子,將來也不許見它!」
林初怔住了,萬萬沒想到,衛此番,只為了讓慕行風立下這樣一個誓言。
都說為母則強,衛知道自己有孕一事被慕行風知曉,他必定不會罷休,借著這個機會讓慕行風立下誓言,哪怕以後孩子出生,慕行風也沒了再找上門來的理由。
慕行風死死盯著衛,氣得渾直哆嗦,又撕心裂肺的咳嗽起來,咳到後面,只覺嗓子眼兒竄上一腥甜,他咳出一口痰來。
「主子!」葛洄憂心喚了一聲,想上前卻又被慕行風一個眼神制止。
慕行風用袖子去邊的跡,看著衛,出一個苦而自嘲的笑來:「你長大了,也越來越聰明了……如果,這是你所願,那我全你。」
慕行風豎起三手指,視線依然死死盯著衛蒼白而虛弱的臉龐,沙啞開口:「我慕行風在此發誓,今生,不得認衛之為慕氏脈。」
話落,屋子裡陷一種可怕的沉寂,他看著衛,眉眼間的笑卻溫一如當初,「好了,先治傷。別怕,我扎針不疼。」
衛別過臉,眼角一行清淚還是涌了出來。
年時,一度害怕扎針,有幾次大病需要扎銀針時,他都是用這樣溫的語氣哄。
往事已殤,如今再想起來,只是徒增傷。
林初看得鼻子一酸,捧著藥方跑出了房門。在大門口見宋拓,把藥方塞給宋拓:「去藥鋪把這些葯都抓回來!」
宋拓騎馬去藥房,總比跑過去要快。
宋拓先前就派人去請大夫了,只是郎中遲遲還沒來。他知道此事刻不容緩,應了聲是,拿了藥方就往外走。
他在門口跟袁三拎著大夫趕回來的袁三了個正著。
袁三著氣,顯然是一路狂奔回來的,他跟宋拓不錯,當即問了句:「二小姐怎麼樣了?」
從他當年隨燕明戈上山,他了衛第一聲二小姐,到如今,他依然用二小姐稱呼衛。
「慕公子正在裡面診脈,開了方子讓廚房那邊先煎藥,我正準備去藥鋪抓藥。」宋拓拱了拱手,旁邊的侍衛牽著一匹馬過來,他接過韁繩,翻上馬就往藥鋪奔去。
這一路被袁三放在馬背上顛得七葷八素的郎中挎著藥箱,嘟噥道:「你們府上都請到大夫了,還這麼折騰我這把老骨頭。」
袁三沒有回話,整個人力靠在了院牆上,汗水大顆大顆從他額角落,顯然是累的不輕,只是他眼神中帶著一種人心驚的沉寂。
慕行風在啊。
郎中見袁三不說話也不進府,以為是府上有了一個大夫,用不著他了,心中憤懣,甩袖就要往回走。
袁三一把拉住郎中的后領,分毫不理會郎中的鬼,只道了句「得罪」,拎著人直接進了府。
林初乾眼淚,正準備去房間里看看有什麼能幫得上忙的地方,就見袁三扯著一個郎中的領把人給提了進來。
「嫂嫂,聽說這是一直為二小姐看診的大夫,留下他,約莫能用的上。」袁三把郎中往林初跟前一放。
林初自然認得這郎中,知道有這郎中在,衛自然也多了一層保障,只是袁三這「請人」的方式一貫的野蠻。
「辛苦袁兄弟了,那邊偏廳備了茶水,袁兄弟先過去坐坐。」林初先對袁三說了這番話,才有些愧疚的對郎中道:「許郎中莫要見怪,實在是府上人命關天,我夫君的這位兄弟才這般魯莽請您過來。」
「燕夫人哪裡話。」郎中對著林初這個都尉夫人自然是半分脾氣不敢有的,他不是第一次來給衛看診了,隨口問道:「是那位夫人了胎氣嗎?」
燕明戈他們在用力幫衛療傷,林初不好這個時候領著郎中進去打擾,又不能落了這郎中的臉面。
想起荊禾之前為了保護自己了不輕的傷,適逢府上此刻作,必然還沒理傷口,當即帶著郎中去了荊禾的房間。
荊禾四肢都有很深的劃痕,因為來不及請大夫,只灑了金瘡葯簡單包紮。
郎中給荊禾把了脈,又開了方子,囑咐了一些養傷期間要忌口的東西,林初都一一記下了,向郎中道了謝,又人領著郎中去偏廳用些茶點。
見到林初平安無事,荊禾一顆心才放下了,只是神間不免自責:「都是奴婢保護夫人不利,才讓夫人陷了陷境。」
這話讓林初又是愧疚又是心疼,道:「若不是你,說不定我現在早命喪黃泉了,莫要再說這些話,你好好養傷。」
「都是些皮傷,過幾天就好了。」荊禾道,想起之前刺客闖進來外面混戰一片的場景,重傷彈不得,想出去幫忙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神愈發愧疚,「衛姑娘傷勢怎麼樣?」
「大夫正在醫治,師姐福大,肯定會沒事的。」話雖這般說,可林初心中還是格外不安。
。
猜你喜歡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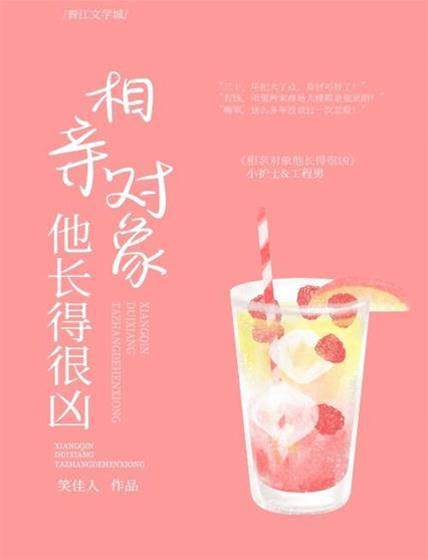
相親對象他長得很兇
江桃皮膚白皙、面相甜美,護士工作穩定,親友們熱衷為她做媒。 護士長也為她介紹了一位。 「三十,年紀大了點,身材可好了」 「有錢,市裡兩家商場大樓都是他家的」 「嘴笨,這麼多年沒談過一次戀愛」 很快,江桃
20.8萬字8.57 43712 -
完結320 章

奸臣的話癆婢女
裴沅禎是個大奸臣,玩弄權術、心狠手辣,手上沾了無數人命,連龍椅上的小皇帝都被他擺佈於股掌之間。 朝堂上下,無一不談“裴”色變、諱莫如深。 沈梔梔是剛賣進裴府的燒火丫頭,原本只想搞點錢以後贖身嫁個老實人。 某日,裴沅禎心情不好,伺候的婢女們個個戰戰兢兢不敢靠近。 負責膳食的婆子慌忙之下逮住沈梔梔,哄道:“丫頭,這頓飯你若是能伺候大人舒舒服服地用了,回頭管家賞你二兩銀子。” 沈梔梔眼睛一亮,奔着賞銀就進去了。 她看着端坐在太師椅上面色陰沉的男人,小聲道:“大人,吃飯啦,今晚有桂花魚哦。” 裴沅禎摩挲玉扳指的動作停下,冷冷掀眼。 沈梔梔脖頸一縮,想了想,鼓起勇氣勸道: “大人莫生氣,氣出病來無人替;你若氣死誰如意,況且傷身又費力;拍桌打凳發脾氣,有理反倒變沒理;人生在世不容易,作踐自己多可惜......大人,該吃晚飯啦。” 裴沅禎:“..........” 此時門外,管家、婆子、婢女驚恐地跪了一地。 紛紛預測,這丫頭恐怕要血濺當場。 卻不想,沈梔梔不僅沒血濺當場,反而從個燒火丫頭扶搖直上成了裴奸臣的心尖尖。. 他一生銜悲茹恨,自甘沉淪。後來,她陪他走過泥濘黑夜,萬千風雪。 裴沅禎才明白,世上並非只有仇與恨,還有一種,是煙火人間。 小劇場: 近日,朝堂文武百官們發現首輔大人越來越陰晴不定了,衆人膽戰心驚。 有人私下打聽,才得知原委。 據說——是因爲府上丟了個小丫鬟。 文武百官們:??? 城門牆角,裴沅禎騎在馬上,目光凜冽地盯着膽大包天的女人。 剛贖身出來沒兩天的沈梔梔:QAQ 我想回去嫁個老實人來着。
50萬字8.18 45003 -
完結99 章

天鵝頸
南城歌劇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舞臺上的今兮吸引—— 女生腰肢纖細,身材曲線窈窕,聚光燈照在她的臉上,眼波流轉之間,瀲灩生姿。 她美到連身上穿着的一襲紅裙都黯然失色。 容貌無法複製,但穿着可以,於是有人問今兮,那天的裙子是在哪裏買的。 今兮搖頭:“抱歉,我不知道。” 她轉身離開,到家後,看着垃圾桶裏被撕碎的裙子,以及始作俑者。 今兮:“你賠我裙子。” 話音落下,賀司珩俯身過來,聲線沉沉:“你的裙子不都是我買的?” 她笑:“也都是你撕壞的。” —— 賀司珩清心寡慾,沒什麼想要的,遇到今兮後,他想做兩件事—— 1.看她臉紅。 2.讓她眼紅。 到後來,他抱着她,吻過她雪白的天鵝頸,看她臉紅又眼紅,他終於還是得償所願。
31.2萬字8.18 28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