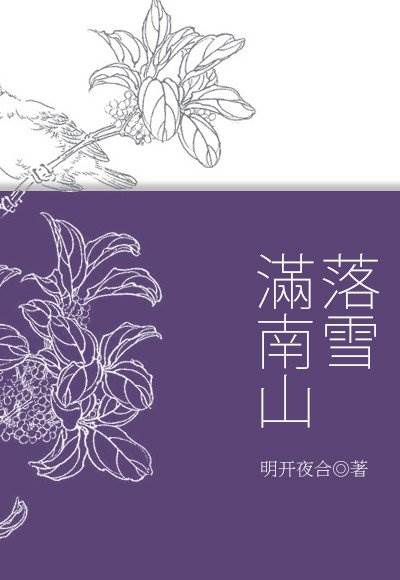《所謂愛情,是你》 第二十六章 她說最後一年
早上八點,咖啡店的老闆六月的媽咪顧亦安的姐姐沈清和開門準備營業時才發現咖啡館竟已經提前開張了,三個客人各占著一張桌子,等著各自清晨的第一杯熱飲。櫃檯後顧亦安圍著圍忙著煮咖啡。
顧亦安聽見有腳步聲,以為是新的客人,一句「請問」還沒問出口就發現來人是老闆娘,快他一步地,六月蹭一下從櫃檯后跳出去,跳到媽咪的懷抱里當一個乖寶寶。
「早啊,姐姐。」
「早。」沈清和看了眼時間確定了不是自己來晚了,「今天怎麼這麼早?」
「提前醒了,就過來嘍。」說個端著咖啡往各個桌子送,路過沈清和的時候還不忘驕傲地說一句,「裡面給你留了一杯,雙份糖呢。」
沈清和甜食,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顧亦安才能拿棒棒糖使喚六月,屢試不爽。
送完咖啡再回到櫃檯后,空間雖不大但站兩個人還是綽綽有餘的,顧亦安放下托盤與沈清和一起品嘗早晨的第一杯咖啡,「我說姐姐,你是不是要考慮考慮提前一下營業時間呢?」
沈清和不理,端著咖啡坐在椅子上,眼睛看著面前的一排書,想著今天要看哪一本,挑好了才順著顧亦安的話瞧一眼引進門的顧客,清冷的聲音帶著幾分倦懶,「不。」
說罷打開書沉浸其中,至於客人,有顧亦安在就無需費心。如此說來,對於這個店還真是不上心啊,似乎開店只是一個消遣,打發時間的工罷了。有沒有客人是次要,客人滿不滿意是更次要,唯有自己開不開心是主要。想來,若沒有六月和顧亦安這兩個鎮店之寶怕是倒閉千百次了。
招待好客人後,顧亦安才有些時間找個椅子坐下,端著咖啡看那個抱著貓看書的人。
已經忘了什麼時候認得這個姐姐,興許是來到這個城市為顧亦安的時候,又興許再晚一些,是這個咖啡館營業的時候。
不論怎樣,算來也有三年了吧。算來六月也快三歲了呢。太久了,一不小心曾經的人離開了那麼久。
旁邊的柜子里拿出畫本,已經記不清是放在這的第幾個畫本,太多了,數不清。拿出筆朝著姐姐沈清和比量一番,不是第一次畫卻是第一次覺這麼強烈想為畫一張像,許是怕了哪一天夢了現實,分別也沒有可以懷念的件。
還未落筆就聽見姐姐清冷的聲音,「把六月也畫上。」
「好,收到。」
「等會寄出去。」
「不寫點東西嗎?」
「不。」
能說一個字就不說兩個字的方便省事,然而時倒流四年也是說笑鬧的,活潑得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只可惜他錯過了那時的。
他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隻言片語的流言是關於關於顧家的爺。
顧家的爺,除去雷打不的林衍,見得了的只有兩個,一個亦初一個亦安,若非他同父異母的哥哥顧亦初意外去世,怕也不到他顧亦安來補這個缺。想到他的到來建立在姐姐死去的上就難以心安,有時候想想,自己這樣每天出現在面前莫不是最大的殘忍。
好在人會死去而不會。
一幅畫結束,白的紙黑的線簡簡單單又格外用心,也不給姐姐檢查直接折好塞進信封里,填上地址。這國的信件一旦開始就是三年。顧亦安看著手中的信,竟有些羨慕收信的人,不知道明年今日是否也能收到這樣一封來自人的信。
驀然間又想起那個夢,夢裡時月安歌混淆在一起,分不清楚。
顧亦安說,「我做了一個夢。」
「嗯。」清冷的聲音只一個字,表示在聽在等,無事不起早,這可是他顧亦安的風格。
每個人都有一個無法直面的人和一段無法直面的往事,於顧亦安而言。所有的無法直面都與安歌有關。端著咖啡往姐姐面前走一步,醞釀一會還是不能夠直接說出,所幸折中找個引子,「我夢見姐姐不要我了。」
沈清和聞言,頭也不抬一遍翻著書一遍順著貓兒六月的,「那定是你做了對不住我的事。」
「哎,」顧亦安搖搖頭,表示姐姐就是姐姐啊,連個安的話都不會說,點點頭表示承認,「夢裡六月因為我了重傷,你帶著六月離開,再也沒回來……」
「嗯。」
沒什麼反應的回應,看不出是安還是嘲笑,或許都是又或許都不是。說出來也無非找個釋放的出口,沉默一會,直奔主題——
「我夢見……回來了,一直在我邊,換了個份換了個樣子——就在我邊。」
「喜歡?」
「嗯?」突然地被問住,「我當然……」恍然中看著姐姐沈清和平靜的目,他似是明白了,這個不是安歌而是——
時月。
喜歡?
不!或許……
不知道……
如此當真是被問住了,對面沈清和還在等著回復,看著顧亦安垂眸陷思考的樣子淡淡一笑,好奇是什麼樣的孩能降得住顧亦安。
良久,顧亦安笑著搖頭,抬眸眼中儘是無奈,「算不上吧。」
「嗯,好吧。」聳聳肩表示中立態度,接著看書,不時抬眸看一眼顧亦安,看他的舉棋不定。
「每一次接近都會讓我想起安歌,很清晰,不論是夢裡還是……現實。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是回來了,可是……不是。」一杯咖啡涼彷彿寓意著什麼回不來的事和人,一口喝盡帶著苦味的咖啡,喝到最後也沒嘗出一點兒甜,放下杯子的瞬間才想起來兩份糖全給了姐姐。
沈清和聽著顧亦安的回答,難得一見的模樣。怎麼?真的心?突然間想起些什麼,手從書架中出一份文檔資料,昨晚林衍送來請翻譯的一份學申請書。說是翻譯實則借的口來勸說顧亦安順從顧家的安排,出國留學再接顧家企業。
申請書遞給顧亦安,什麼也不說以他的英文水平看一份表格還是沒問題的,顧家的門一旦踏進就別想著全而退,或傷痕纍纍如,或心疲憊如他。
「林衍拿來的?」他就知道林衍來找姐姐不會有什麼好事。
沈清和輕輕點頭,知道顧亦安抵顧家更是不喜林衍這個名義上的大哥。
可是林衍又做錯了什麼呢?
無非錯在被顧家看中了才華收做養子,明面上的風實際上難不是與他一樣被被囚著束縛著,都是不由己,或許正是因為這點太像,他才不喜這個大哥。
照鏡子似的看到另一個自己,痛苦掙扎之中若是不說倒還可以忍,一旦被破被坦白,就無法再欺騙著自己繼續承。某種意義上,他是他的鏡子,他亦是他的鏡子。
顧亦安隨意翻看兩眼便扔在桌上,他知道會有這麼一天,只是不知道會這麼快到來。從安然變顧亦安的第一天就與所謂的親生父親訂了君子之約,他給他四年的自由,他還他餘生的唯命是從。
為什麼會是在這個時候呢?
突然又回到那個夢,恍然間有些明白夢裡一遍遍掙扎著要帶夢中人離開,或許是夢比現實早一步想起四年之約,那夢裡要帶走的是誰呢?
安歌?或許……
時月。
時月啊時月,我該怎麼面對你。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會不會還怪我對你瞞份?你會不會釋懷?會不會寫信給我?
「什麼時候開學?」
「來年九月。」
「嗯。」還有一年的時間,不長不短足夠上一個人也足夠捨棄一個人。想到要分離眼前就莫名浮現出一雙蒙著水霧的眼睛,夢裡夢外都甩不開的眼睛,幾乎夢魘一般,「姐姐,你說會不會……」會不會夢是真的?們當真是一個人?「我總覺得還在,尤其是遇見這個姑娘以後……」
「當然在。」沈清和出手指著顧亦安的心口,「一直在這。」
「嗯。」顧亦安捂著心口,彷彿什麼珍寶似的小心翼翼呵護。
許久許久,沈清和開口,聲音有些空遠,不知是說給他聽還是說給自己,「這對活著的人會不會太殘忍……」聲音越來越小,直到陷自己的回憶。
顧亦安不知想起了什麼,無非顧家的爺曾經的人,昔人已故空餘,新人在側不知味。
果然,死亡是對活人最大的考驗。
兩人各懷心事各想著舊人新人,咖啡館里呆上一天,平平淡淡尋尋常常,一個照顧客人忙前忙后,一個收收賬款從容不迫。進進出出許多人,來了再走,恰如人生,遇見又分離。
若真的要找出一些不同尋常的事,那就要走進人群中去,聽他們說,看他們笑。歷史總是相似,相似的故事相似的,卻又細緻到極點的各自彩。
顧亦安忙中閑品一杯咖啡,看人看故事,做個旁觀者是他的好之一,看客人的形,看客人的表,印象深刻的便畫在本子上,時不時地張出來。畫家長得,畫像畫得妙倒也沒有人來爭一個肖像私權。
除去有靈的,不定時還依據心把自己上架出售,定時定量出售自己的現場畫像。
想來這也是咖啡館吸引客人的一個原因所在,尤其是孩們和們,多次推開咖啡館的門只為看一眼小黑板上有沒有寫著「今天服務生心好,出售畫像兩張」或是「今天老闆開心,出售畫像三張」之類的話。
掙扎幾次,顧亦安拿出手機,看一眼再放進兜,每日的問候已經延遲了許久許久,還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拿著筆在一屋顧客以為自己要了筆下的幸運兒時,顧亦安畫了一雙眼睛,想要接著畫出臉甚至是髮型,卻發現怎麼落筆都不對。
一張畫只一雙眼睛,張在塗牆上,顧客中有人猜測是老闆娘沈清和,有人猜測是服務生顧亦安。
然而究竟主人究竟是誰,連作畫者也說不清。
猜你喜歡
-
連載81 章

后婚寵主義
【久別重逢|先婚后愛】文案如下:十年前,他是校草加學霸,她是寄宿他家三年之久的借宿生。十年后再見面,她沒成想,他就是那個傳聞中最為難搞的——甲方爸爸。“好巧啊,銘呈哥。”“能把‘哥’那個字,去了嗎?嚴格意義上,你不是我的妹妹。”“……”她知…
35.1萬字8 6862 -
完結824 章

被奶奶按頭結婚?爺他一秒淪陷了
【甜寵+雙潔+隱婚+寵妻狂魔】禁欲高冷不近女色的商爺被自家老太太按頭結婚,娶的是自己看著長大的小不點。他一直以長輩自居,從未將小不點當成女人看。丟下一紙離婚協議之后,他立刻就后悔了,尤其看到她的身邊桃花不斷。商爺人前高貴驕矜,生人勿進,背地里默默掐人桃花,一朵又一朵。終于有一天某大總裁忍無可忍拍案而起,撲通一聲跪在搓衣板上,可憐兮兮的撒嬌:“老婆,跟我回家好不好……”
149.1萬字8 164368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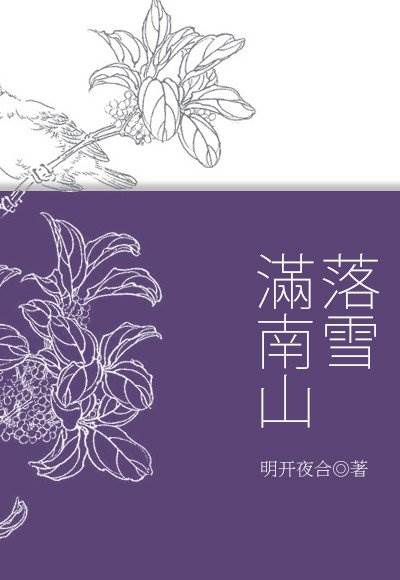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300 -
完結309 章

水洗情書
遲宴澤猖狂,酷帥,耀眼,是北清大出了名的浪蕩公子哥。身邊永遠花團錦簇,燈紅酒綠。 周檸琅清冷,懂事,沉默,一直墨守成規,在校園裏每次遇見他,她都竭力將十六歲開始就懷有的滾燙情愫藏於心底。 他身邊來來去去不同女生的時候,她在圖書館跟實驗室埋頭學習。 一個雨天,校園咖啡廳裏,她穿杏仁白裙子,揹着雙肩書包,捧着書本,正要裝作不經意的路過。 留意到周檸琅清麗卓然,遲宴澤的朋友說:“這女生一看就特別乖。” 遲宴澤佻薄的撩了撩眼皮,壞得不行的道:“爺就喜歡乖的。” 一次大學聚會上,早就瞞着所有人在一起的他們偷偷約出來,在無人角落,他痞氣的熱吻她耳廓,她着急要去跟室友見面,心如撞鹿。 他薄脣輕勾,嗓音含混道:“再讓爺親會兒就讓你走。” * 狂戀如同一場熱帶颶風,來得快,也去得快。 大學畢業後,逃一樣離開的周檸琅沒想到會在自己上班的醫院碰見遲宴澤。 久別重逢,他站在春日陽光裏,睨她的繾綣眼神裏有她這些年來一直住在那裏的影子。 “周檸琅,把老子睡了,不給老子名分是不是?”身爲天之驕子的他捻滅手裏的煙,又頹又喪的跟她認敗。 “周檸琅,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他求她一樣,卑微到極點的要跟她複合。 後來,一起去當初她年少時求願暗戀有回聲的佛寺內焚香還願。 暗戀他許久的周檸琅見他不凡的眉眼,在金瓦紅牆的經殿外終於安寧寂靜,不似年少時那般暴戾猖狂。 她心裏知道,她的暗戀真的改變了他。 山清海晏,同袍同澤,是周檸琅的遲宴澤。
48.5萬字8.18 118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