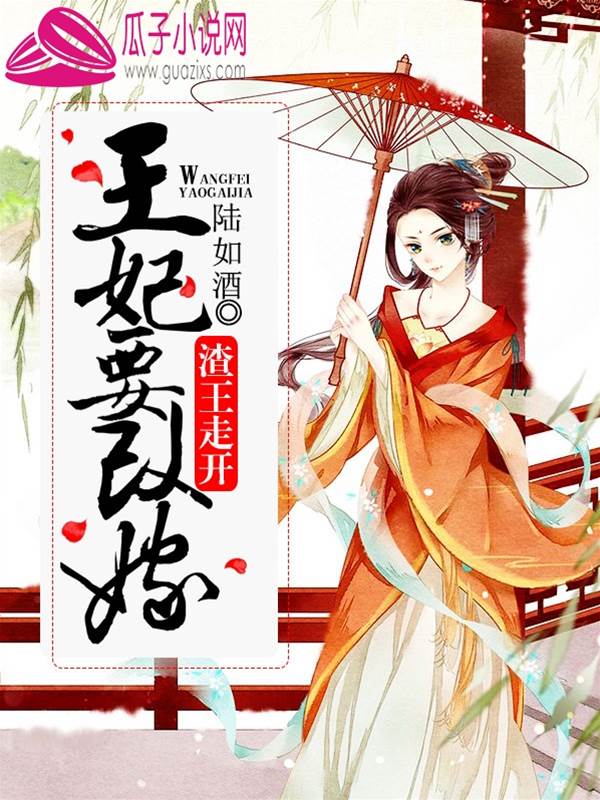《籠中雀她渣了瘋批皇帝》 第2卷 第六十章 要他的東宮,也要他的良媛
接著便是連續三日的扣宮門,百分為兩派,一派是太子黨,堅持國本不能,太子不能易;一派是燕王黨,力陳天降異象,皇命若移,不得復久。
兩派便在宣室外爭了個你死我活,聲謾罵,甚至大打出手。
許鶴儀連續數日進宮,子不住,再去未央宮時,便攜了姜姒隨車侍奉。若許鶴儀進了宣室,姜姒便避于車。若他出了大殿,姜姒便盡心照顧。
這一日,許鶴儀依舊去了未央宮,百尚在爭執不休,有的已經中了暑氣被侍匆匆抬了下去。其余大多吏因僵持時間已久,心疲憊,因而盤坐于宣室外,吃了侍端來的飯食與水,繼續斗一般,聚訟紛紜,相持不下,難解難分。
姜姒端坐于王青蓋車中,車設有短案,案上嵌有爐子,拿火折子點著,就能煨上藥。
因不知何時能回東宮,怕誤了喝藥的時辰,因而便帶了藥來。
簾子挑開,有人上了馬車。姜姒盈盈端了藥罐,文火煨上湯藥,宛然笑道,“殿下,就快好了。”
來人坐到面前,搖著折扇意味深長笑道,“姜良媛。”
姜姒陡然抬起頭,手中的作一時停頓下來。“燕王殿下上錯馬車了。”
許之洐角上揚,滿是譏誚,“未央宮外這王青蓋車一共兩駕,本王子康健,又不需飲什麼藥,自然是上錯了。”
姜姒面沉靜,“殿下既然知道上錯了車,便自行下車吧。”
“嗯。”許之洐應了一聲。
姜姒正奇怪他應得如此痛快,誰知車外已有人聞聲揚鞭馬,馬車晃了一下,轱轆轱轆便駛了出去。
姜姒驚愕地看著他,“這是太子殿下的馬車!”
許之洐笑道,“自然。”
姜姒心口發,若是許鶴儀出了宣室,沒有及時飲下湯藥,只怕要加重病,因而趕忙掀開車簾喊道,“將軍快停下!太子殿下還等著用藥!”
許之洐的神瞬間便晦暗了幾分,一雙幽深的眸子若有所思地打量著,“你真是鐵石心腸。”
這話又從何說起。
馬車越來越快,在長長的甬道上疾馳。
姜姒面發白,握了藥罐,“殿下要去哪里?”
“自然是燕王府。”
姜姒呼吸一凝,別開臉,眉梢蹙。絕不要隨他回燕王府,可伯嬴也決計不會停下車來的,這樣想著,姜姒抱起了藥罐,趁許之洐不備,掀開簾子便要往下跳去。
伯嬴已一把將拽回,勒住了馬,馬車便堪堪停在了甬道中央。
“良媛請回吧。”伯嬴冷冷地掀開簾子,請進車。
姜姒不得已,抱著藥罐坐回了馬車。抬起眸子見許之洐坐在那里,臉鐵青。
“你真是連命也不要了。”許之洐譏諷道。
“殿下一定要太子退位麼?”
“唔,”許之洐一笑,眼眸卻深不見底,“是呀!”
他又說,“我不但要他的東宮,還要他的良媛。”
“你......”姜姒不曾想到,自己嫁給許鶴儀,竟促使了許之洐取而代之的計劃。一時愕住,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你可有乖乖聽話,守好自己的子?”他抬起的下,仔細打量著那一雙人的桃花眸。
姜姒臉一白,“殿下若說完了,便放我下去。太子殿下該喝藥了,若是誤了時辰,你我都擔待不起。”
“做了良媛,當真不一樣了。”他似笑非笑地看著,眼里沒有半分笑意,“任憑你是中宮皇后,也不過是我的奴罷了。”
話音還未落,他隔著案幾扣住的后頸,俯便重重地吻了上去。
掙扎幾下,又急又怒,已是一掌扇了過去,“殿下請自重。”
下手倒是狠,許之洐的臉頰漸漸發紅,他瞇起了眸子瞧,眼神非常復雜。
就連姜姒自己也僵住了,被他制日久,沒想到自己竟然敢打他,因而一時也手足無措起來,朱微微翕,卻并沒有說話。
兩個人一時僵在那里。
姜姒低垂著眼,咬著,紅了眼眶,“我要去送藥了,他一定等急了。”
許之洐的地抿了一條線,他幽黑的眼眸漸冷,淡漠道,“我不許你走,你能走出去?”
那一雙眸子水盈盈,凄聲問道,“殿下到底要怎樣?”
“跪下求我。”他垂眸冷冷掃過,終究還是要跪下。
姜姒呼吸一凝,神立時黯然了下來,心里一時間五味雜陳,令郁郁不過氣來。終極心一橫,抱著藥罐便跪了下去,“求燕王殿下放我出去。”
“主人。”他毫無地肅聲命道。
“絕不!”死死地瞪著許之洐,抓藥罐的手已是骨節發白,著的倔強。
“你若不從,便將你,從這王青蓋車里扔出去,那些迂腐老臣也都看看你這放的樣子!”他已然了怒,冰冷的聲音里暗藏暴怒,仿佛一把尖銳的冰刀,寸寸割人骨,令人膽戰心慌。
他話音不過是甫落下來,手便將的領口扯下肩膀。那凝脂似的肩頭似刻意削的一般,沒有一多余的。一時暴在空氣里,開始輕輕發起抖來。
姜姒脊背一涼,噙著淚仰頭看他,他的神冰涼,沒有半分愫。除了放走這樣的話,他慣是說到做到,不曾有假。
姜姒慢慢地低下了頭,忽而笑道,“殿下當真是‘一言九鼎’。”
許之洐又一次反悔了。
他自己答應過,他不再是的主人,也不必再做他的奴。他們已是山高水遠,互不相欠。
“是你自己不識抬舉。”他猛地扣住的頸,一點點收力道,迫使高高揚起臉,正對上他的眼睛。那只手分外有力,隔著的皮,似是要將的骨頭碾斷一般。
“你只知關心許鶴儀是否用藥,可曾問過我的傷如何了?”
姜姒便用一種極平和的眼神看著他,眸子里的逐漸地黯淡了下去,眼角淚點點,片刻便順著臉頰滾落下來。
閉上眼睛不再去看他,依言低聲道,“主人。”
“這乾朝的天下,終將是我的。”他肆意張揚,笑起來十分恣意。“跟著我,不虧。”
他說著話,已經挑開簾子下了馬車,淡淡吩咐道,“送回去吧。”
伯嬴聞言便調轉了馬頭,打馬朝來路駛去。
隔著簾子,姜姒能見許之洐負手立在未央宮長長的甬道中,他搖著折扇,那頎長的子在這高高長長的甬道中漸漸遠去。
他這樣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850 章
貴女謀嫁
穿越成本該重生的侯府嫡女,還附贈前世記憶,顧月華很不淡定的接受了,只不過還不等她好好適應這個身份,便有各種各樣的跳樑小醜接踵而至. 先是前世裡害的本尊一家枉死的太子殿下指著她的鼻子大罵賤人,卻被她一個茶壺砸過去給砸暈了. 後有同宗堂姐妹上前來找茬,被她優雅的用三寸不爛之舌給氣暈過去了. 從此,溫良賢淑的古家二小姐,便被灌上了潑婦一詞. 好吧,潑婦就潑婦,名聲值幾個錢?好好保護姐姐家人,努力化掉前世整個家族的災難,覓得一個如意郎君纔是真本事,她在意那麼多做什麼? 但是這每日裡無事獻殷勤的某皇子,總是圍著她大轉是怎麼一回事?
221.5萬字8 62478 -
完結341 章

青珂浮屠
許青珂為了報仇,穿了官服爬上權位成了弄臣。 諸國爭亂起,國內國外權貴者都先奔著名聲來挑釁——聽說貴國許探花長得十分好看? 于是他們都來了,然后他們都彎了。 狗哥:那沒有的,我后來把自己掰直了,因小許許女裝更好看。 【小劇場】 姜信:下毒火燒暗殺我多少回?我只想跟你結盟,為啥不信我? 許青珂:你知道太多了。 姜信:最上乘的謀略不是殺人滅口,而是將對方變成自己人。 許青珂:太麻煩。 姜信:不麻煩,我跟元寶已經在你房間門外了。 金元寶:汪汪! 起初,他只是想結盟,后來,他想跟她成為自己人,再后來....不說了,準備嫁妝入贅去! 金元寶:我的原主人臉皮很厚,因為天天帶著人~皮面具,有時候還戴兩層,我覺得他有病,對了,我叫金元寶,是一條狗,我只為自己代言。
93.6萬字8 7028 -
完結886 章

農家小寡婦
張秀娥穿越了,成了個克夫的小寡婦。人都說寡婦門前是非多。她想說,她的是非格外多。最要命的是,她克死的那病癆鬼,竟然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了!聶遠喬:聽說你昨天洗衣服的時候,和李二眉目情了。聶遠喬:打水的時候王三是不是多看了你幾眼?聶遠喬:聽說許員外家的獨子相中你了!張秀娥:滾!我不是你媳婦!
160.9萬字8 44939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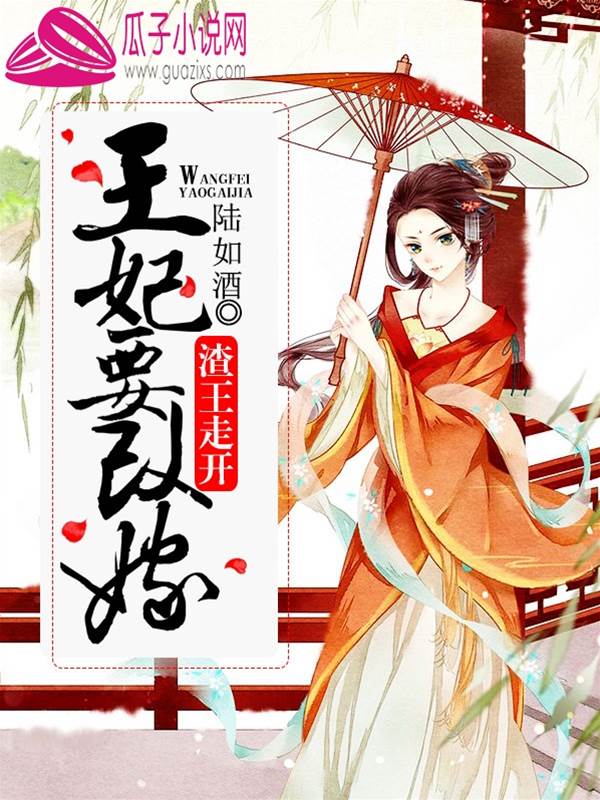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